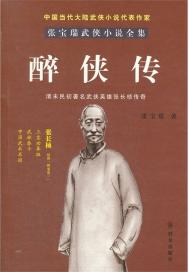谁养育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精气神
揣着录取通知书,我去华东师大报到。那时的中文系就在进入大门不远处的右侧。我看到了宽阔的绿得耀眼的草地,看到了有着罗马式意蕴的文史楼。巨大的巍巍然的圆形庭柱展示了当年的“大夏大学”的不凡气度。我有了找不到北的感觉,于是就向迎面走来的一位老者问路。她很瘦小,清秀的脸上架着一副细细金丝边的眼镜。她和蔼地微笑着,开口回答我时让我惊异地发现,她的声音竟然极其清纯娇嫩。不久我知道,我进校第一天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是亲历过五四文学革命的、曾经在那时的“文明戏”《孔雀东南飞》中扮演催人泪下的刘兰芝的,后来成为《诗经》研究专家的学界著名教授程俊英先生,她那时大约不过五十来岁。
程先生给我们上课时间我们道,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首诗吗?知道它是一首爱情诗吗?知道它只有一句诗句吗?知道它的作者应该是一位佚名的女性吗?我们屏息静听了。然后程先生就用她那如同小女孩般的嗓音向我们朗诵道:
“候……人……兮……”
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否受到过震撼,但是,许多年后,当我提升了自己的文学鉴赏的品位,当我读懂了北岛的那首只有一个字的——“网”——的名诗《生活》,当我自己也站在华东师大的讲台上面对学生时,我才明白了我们的程俊英先生,是以怎样的扎实的功力和对文学本题的准确透视,充填着我们的精气神,把我们引入了文学的殿堂。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位程俊英先生,在她进入耄耋之年,高龄抵达九十之时,竟然还与后生蒋丽萍女士合作,捧出了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处女作《女生妇人》,完成了她的作家梦!
程俊英先生的文学经历在华东师大的老一辈先生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中文系的许杰先生,早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就因其大量的创作实绩而被文学史家议评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徐中玉先生,八十年代后期出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七十多岁的他腰板笔直、步履坚挺地带领着上海的作家群体大步走过了建设世纪之交新文学的那一段路程,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热情率直的批评风格,赢得了上海作家们的真诚的尊重和拥戴。而教育系有一位专攻教育理论的老先生,名沈百英,在他九十多岁时竟发表了一篇儿童文学,题名是《七个矮小子》,一举击败众多竞争者,荣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那篇获奖的作品,后来被多种儿童文学教材选用,几乎成了“儿童故事”这一创作体裁的样本。
出色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宽泛的、久远的、甚至是终身的。记得钱谷融先生当时教我们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时候他才四十多岁,刚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不久,风华正茂。他到我们的大教室里来上课,常常是西装革履,气宇轩昂,让我们一百多个十八九岁的傻妞呆小子们眼前蓦地一亮。他的西服是正规的套装:深色,笔挺,内里有马夹,露出鲜亮的领带和雪白的衬衣领子——在以“穿着草鞋进课堂”为革命榜样的当时,即便是装束,他也是够另类的。他极富口才,给我们分析曹禺剧作《雷雨》时,不由得我们不信服他对人物性格之复杂性的论述,尽管那时尊奉的“文学概论”告诉我们的并不是那样的道理。四十多岁时的钱先生嗓音响亮,讲课属于激情派,每每讲热了,就会先是脱下外套来,接着卸除紧身马夹,最后干脆扯去领带,于是我们就在一个洁白衬衣的滔滔不绝的老师那里,领受到了一种在那时极为珍稀的无拘无束的独特风采。
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召开的“华东师大作家群文化现象研讨会上”发过一个言,称我们学校以丽娃河为中心,辐射组建了东西两大片样式各异的教学楼群,再加上参差揉合其间的水杉林、银杏角、樱花丛、荷莲池等“师大十景”,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气场”,地灵人杰,所以才一轮又一轮地造就出了这么一个“华东师大作家群”。我发这个言有点妖里妖气的,本意自然仅只是逗个乐子,活跃点会场气氛。但是,在华东师大的建校数十年的历史上,我们的确惊异地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走出校门的沙叶新、戴厚英、鲁光,七十年代跃上文坛的王小鹰、赵丽宏、沈善增,还有在八九十年代里有所建树的格非、陈丹燕、孙颙等等这么多的作家,这不能不说是教界、学界或者说是文坛的一大奇观。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原因固然复杂,但我以为,由供职于华东师大的一大批文学功底极其扎实、毕生投入于文学研究乃至于终身都保持着文学创作之欲之激情的先辈老师们所组建而成的文化“气场”,即当下通用说法的“人文氛围”,正是从精神的深处丰富了、潜移默化了、融合打造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而使其中的一部分不懈坚持者结成了一枚又一枚的硕果。
是身正学高、才华斐然的老师们,孕育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精气神。
王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