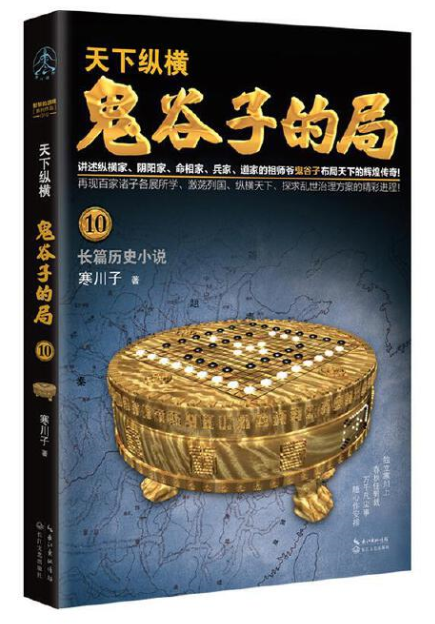——纪念《中国烹饪》创刊十周年
饮食也是文化,对这种观点我很赞同。我们中国人在吃上向来讲究,这种观点无疑更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地位,增加我们的自豪感。联系到我自己,可就败兴了。我的朋友“自吃成材”成了美食家,烹饪能手,如汪曾祺,如陆文夫。我非常高兴,可我自己怎么总跳不出爆肚豆汁卤煮火烧的水平。在吃的领域,平生就出过一回风头,那是在欧洲。有天到某国的乡间去参观希特勒留下的集中营,恰好附近有个“中华料理”,中午我们就去那里吃饭。老板是欧洲人,为了证明货真价实,除了室内尽量挂些中国字画外,还特地养了条地道的北京叭儿狗,那狗每过两三分钟就叫唤一次,确是北京口音。陪同的朋友告诉老板我是中国人,他非常兴奋,说要作几个拿手菜请我品尝,不一会儿就端来了菠萝炖牛舌、咖哩烤肉等好几种菜。吃完后有个朋友问我:“哪一样最像中国的?”我说“只有这狗的叫声。”没想这话叫老板听到了,有点不快地问我:“如果我做的不对,请你说这舌头该怎样做?”我告诉他作舌头不能放菠萝,洗净下锅先不放盐,只用花椒、大料、茴香、葱、姜、蒜白煮,然后……说到这他求我停一停,回柜取来纸笔,要翻译重头再说一遍,他一一记下,一边记一边冲我道谢,最后说什么也不肯收我们饭钱,并说作为讲课费还太少了点。我问他在哪里学来这样的中国烹饪手艺?他说他在越南住过两年,向那里的厨师请教过。我才知道和汪曾棋一样,他也是自学成材。从此我在该地名声大振,不断有女士向我请教中国的烹饪秘诀,诸如包饺子拌豆腐,都曾无私地给予传授。不过好景不长,期满回国,又恢复炊事上的无作为状态,遂再无问津者。但我对吃还是关心的,闲时还对食事作些思索。
我想,若把饮食纳入文化范畴,它可能是最容易从事又最难取得成就的一个项目。说容易,容易到几乎不用学,小孩掌握的头一门生活技能就是吃奶。形容一个人无能,最常用的话是“你就会吃!”说难,简直难于上青天,从参与活动总人数和领袖人物的数目比例看,这个领域成功机遇最小。你看么,全国从事表演行业的不过几万人,名演员却够三位数;耍笔杆的也不过万把人,全国作协的会员已超过三千;研究原子能的人尽管更少,我们也还知道钱学森、钱三强一长列名单。全国十一亿张嘴天天吃饭,著名的美食家,烹饪家能数出几个来?
毛病出在哪儿呢?这可以从体育方面得到点启示。健康人都会走路和蹦跳,会走路和蹦跳并不就是竞走健将舞蹈明星。走路与蹦跳是动物本能,个个能作;竞走和舞蹈是人类创造,不学不行。竞走和舞蹈是人类对走路、蹦跳作了观察、体验、认识、思考、改造、提高等等功夫之后,依据科学原理,按照明确目标创造出来的技艺,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出现的东西,当然属于文化范畴。吃饭的人虽多,但大多仍停留在本能状态,不进入思维创作境界,就很难吃出名堂来。这种情况也是饮食的双重功能造成的。饮食不像绘画,人人都知道画只是给人看的,看画是为了解闷,不是为了看画上的包子馒头来解馋解饱。饮食则不然,它有两套作用,既能解饥活命又供艺术欣赏。不过人总要先吃饱肚子,然后才有闲心去考究食品的色、香、味、形。这两项功能有先后主次之分,不能平等并列。旧中国几千年来,多数人都还揎不圆肚子,能有几个人去研究饮食艺术?虽说这样,但是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历史长,文化传统悠久深厚。从绝对的质与量来说,我们仍是“饮食大国”。中国烹饪闻名世界,遍布五大洲各个角落的“中华料理”,也算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作的一份贡献。
现在人们说“饮食文化”、“烹饪艺术”,既是“文化艺术”,当然像其它文艺门类一样有阶级、民族、地区之差;文野、雅俗、高低之分,也有各种流派的争鸣,各种风格的斗胜。但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特征还在“可饮宜食”。不管什么“文化”,首先得好吃。塑料苹果玻璃葡萄做得再漂亮再乱真,也只是工艺美术的杰作,不能算作饮食文化成果。有了这个概念,我们才可以在千姿百态的饮食文化面前找出共同性,约定一些基本的、通用的规范,便于饮食文化的品评,也适于错误观念的矫正。比如,人们在夸奖食品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如果以“吃字当头”的原则来衡量,这轻重先后的次序就未必适当。一个菜要是吃着叫人恶心,不管怎么好看如何好闻,也不能算是好菜。近来有的饭店,菜肴质量平平,却在雕刻、配色、摆盘花上大费功夫,我就怀疑是受了“色香味”次序排列法的影响。这倒也罢了,更有甚者是把挖掘传统和卖假古董混为一谈,一面上菜,一面解说:“这个菜唐明皇吃过了”;“那个汤明太祖命名”,客人感到自己像小娃娃似地被人哄着玩。说它好吃对不起良心;说不好吃,连皇上都说好,你怎么不识货?有次陪日本朋友去一家饭馆,桌上放了陈皮梅、玫瑰枣、几碟压桌小吃,服务员居然说这是战国时期某名人的家宴传统,那朋友冲我作了鬼脸,用日语说:“贵国在几千年前就有陈皮梅吗?”说完哈哈大笑。若明确食品评议应当先比好吃,后论好看,这类笑话可能会少些。
其实,饮食文化是最讲实效的文化,不能靠哗众取宠,而要看真招子。真招子不一定非上名贵菜肴,祖传绝技,只要普通中见出众,一般中显特殊就是好活儿。记得战争年代,我在沂蒙山区,端午节那天恰好有任务,日夜行军一百几十里,走得肚皮空空,口干舌燥,到了宿营地,各班领到的都是煎饼、猪肉和韭菜。别的班全吃猪肉炒韭菜就煎饼,我们班长把瘦肉和韭菜剁成馅包在煎饼里,肥肉炼油炸成春卷似的煎饼盒儿,引起全团羡慕。这位班长就算得是位美食家,其创造性与成就未见得比条件具备时做一碗狮子头差。只有平庸的厨师,没有下等的菜肴。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