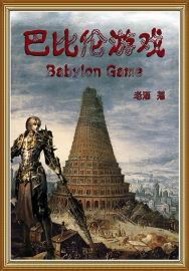她把这些都剪下来,连同刊登廊桥的那期,他的文章,两张照片,还有他的信,都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中。他把信封放在梳妆台抽屉的内衣下面,这里理查德是决不会看的地方。她像一个远方的观察者年复一年跟踪观察罗伯特·金凯,眼看他渐渐老起来。
那笑容宛在,就是那修长,肌肉结实的身材也依然如故。但是她看得出他眼角的纹路,那健壮的双肩微微前俯,脸颊逐渐陷进去。她能看得出来,她曾经仔细研究过他的身体,比她一生中对任何事物都仔细,比对自己的身体还仔细。他逐渐变老反而使她更加强烈地渴望要他,假如可能的话,她猜想——不,她确知——他是单身。事实的确如此。
在烛光中,她在餐桌上仔细看那些剪报。他从遥远的地方看着她。她从一九六七年的一期中找出一张特殊的照片。他在东非的一条河边正对摄像机,而且是近镜头,蹲在那里好像正准备拍摄什么。
她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时还看得出他脖子里的银项链上系着一个小小的圆牌。迈可离家上大学去了,当理查德和卡洛琳去睡觉之后,她把迈可少年时集邮用的高度放大镜拿出来放到照片上。
天哪。以后所有他的照片上都有这个小圆牌挂在银项链上。
一九七五年之后她再也没在杂志上看见过他。他的署名也不见了。她每一期都找遍了,可是找不到。他那年该是六十二岁。
理查德一九七九年去世,葬礼完毕,孩子们都各自回到自己家里以后,她想起给罗伯特·金凯打电话。他应该是六十六岁,她五十九岁。尽管已经失去了十四年,还来得及。她集中思考了一星期,最后从他的信头上找到了电话号码,拨了号。
电话铃响时她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她听到有人拿起话筒,差点儿又把电话挂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麦克格雷格尔保险公司。”弗朗西丝卡心沉下去了,不过还能恢复得过来问那女秘书她拨的号码对不对,就是这个号码。她谢谢她,挂了电话。
下一步,她试着打华盛顿贝灵汉的电话问讯处。登记名单上没有。她试打西雅图,也没有。然后是贝灵汉和西雅图的商会办公室。她请他们查一查本市指南,他们查了,也没这个人。她想他哪儿都可能去的。
她想起杂志来,他曾说过可以通过那里打听。接待员很有礼貌,但是新人,得找另外一个人来回答她的要求。弗朗西丝卡的电话转了三次才跟一位在杂志工作过二十年的编辑通上话她问罗伯特·金凯的下落。
那编辑当然记得他。“要找到他在哪里吗,呃?他真是个该死的摄影师,请原谅我的语言。他的脾气可不好,不是坏的意思,就是非常固执,他追求为艺术而艺术,这不大合我们读者的口味,我们的读者要好看的,显示摄影技巧的照片,但是不要太野的。”
我们常说金凯有点怪,在他为我们做的工作之外,没有人熟悉他。但是他是好样的。我们可以把他派到任何地方,他一定出活儿,尽管多数情况下他都不同意我们的编辑决策。至于他的下落,我一边讲话一边在翻他的档案。他于一九七五年离开我们杂志,地址电话是……他念的内容和弗朗西丝卡已经知道的一样。在此之后,她停止了搜寻,主要是害怕可能发现的情况。
她听其自然,允许自己越来越多地想罗伯特·金凯。她还能开车,每年有几次到得梅因去,在他曾带她去的那家饭店吃午餐。有一次,她买回来一个皮面白纸本,于是开始用整齐的手写体在这些白纸上记下她同他恋爱的详情的对他的思念。一共写了三大本她才感到完成任务。
温特塞特在前进。有一个艺术协会,成员多数是女性,要重新装修那些桥的议论也进行了几年了。有些有兴趣的年轻人在山上盖房子。风气有所开放,长头发不再惹人注目了,不过男人穿凉鞋的还是少见,诗人也很少。
除了几个女友外,她完全退出了社交。人们谈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谈到常看见她站在罗斯曼桥边,有时在杉树桥边。他们常说人老了常常变得古怪。也就满足于这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