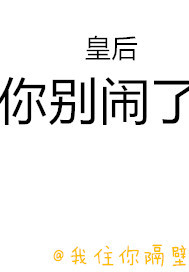翌日清晨,昭德宫,院里院外哭成一片。
“皇上,昭德宫的娘娘殁了。”高力士轻轻走进御书房,略带哭腔的说。
“你说什么?”唐玄宗听到噩耗后,震惊的打翻了最爱的砚台,跌坐在龙椅上,久久无法平复,“什么时候的事情?”
“听昭德宫的奴才们回话说娘娘自昨日睡去便再没醒过来。”高力士擦着眼泪回道。
唐玄宗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喃喃自语,“朕知道了,你下去吧,朕想静一静,哎,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
“娘娘早登极乐,走得很平静没什么痛苦,皇上别太难过。”高力士担忧的劝了一句顺从的向外走去。
“等等!”高力士正欲告退,却被唐玄宗叫住,“力士,为朕重新磨砚。”
随着高力士手腕旋转,纹理奇异的端砚中顿时出现一片墨海。
唐玄宗捻起一直上好的狼毫笔奋笔疾书,力透纸背,洋洋洒洒了在圣旨上写了几句,失落的说,“力士,拿去昭德宫宣了吧。朕知她淡泊名利要的不是这些,如今也只有靠这点微不足道的封赏让朕安心些,后事就由你同太子安排吧。”
“娘娘泉下有知,自会为皇上的一片诚挚感动。”
宫中无秘密,不出一个时辰,皇甫德仪殁了的消息已传遍后宫,有人喜有人忧,不管安于什么心思不约而同地来到昭德宫与皇甫德仪见上最后一面。棺椁中的皇甫德仪的妆容早已拾掇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脂粉,面色如生,神态安详,黄金制成的呈圆环状的金钏一圈一圈缠在她白皙的腕上闪闪发光,明晃晃的昭示着她死后的辉煌。
“我的好姐姐,你怎么这般狠心,妹妹还没有见你一面你便这么走了!”宫中有些位分低的嫔妃还未踏进昭德宫已泪如雨下的哭泣,进了正殿竟直直的扑到棺椁上大哭起来,表现得情真意切、姐妹情深。
望着屋中各怀居心的人兔死狐悲的哭泣声,茯苓心里一阵难过,在宫中共同生活多年的人,哪怕有深沉大恨,人已死了,又何必冷血得令人咋舌,装模作样的演戏。她顿觉得所谓的后事只是一出闹剧,心里有股种想将那些作秀的人统统赶出去的冲动。
倒是皇甫德仪的几个宫女真性情,虽然并未嚎啕大哭,隐忍悲伤忙着接待前来吊唁的人,神色间却难掩悲怆之情,尤其是那名叫炽情的宫女,眉眼间忽闪着一种绝望的刚毅,自始至终一滴泪都没掉,甚至努力维持着脸上的笑意,不让隐在心中的悲伤露出来。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平静了这一片混乱的景象。
“圣旨到——”高力士手托圣旨走了进来,所有的人都跪倒在明黄色的圣旨之下。
“妃皇甫氏昔承明命,虔恭中馈,秉性柔嘉,持躬淑慎。于宫尽事,克尽敬慎,敬上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平和,椒庭之礼教维娴,堪为六宫典范,实能赞襄内政。以昭贤德之范,及尸柩在堂,特追封淑妃。魂而有灵,嘉其宠荣!”
太子及众人跪在地上静听着圣旨的宣读,脸上悲怆无半分欣喜,待高力士宣读完圣旨,双手恭敬的接过圣旨谢恩,叩头时眼中泪花涌动滴落在地板上。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而已。
“太子殿下,皇上命老奴协助您办理淑妃娘娘的后事。还请太子及各位皇子节哀顺变,注意身体。” 高力士低语道。
太子李瑛抬眼坚定的望着他说,“谢高总管提醒,淑妃娘娘后事还要麻烦您老多多提点,娘娘对我恩重如山,本太子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一道圣旨,将屋中的气氛带的有些僵持尴尬,鸦雀无声的,许久,才有人反应过来,迸发出此起彼伏的哭丧声。
淑妃娘娘虽然在生前曾交待后事一切从简,却由于皇上追封和太子坚持大办而办得盛世浩大,规模远远超过她生前任何的封赏典礼。太子殿下不仅招来九九八十一名得道高僧手持法华经为其超度三日,还在宫外护城河里放了数百盏莲花灯祈祷她早登极乐,皇上也下旨宫中皆穿素服,全国上下三日不得开宴为淑妃娘娘放孔明灯祈福。
这三天宫中哀乐不断,凄凄哀哀,吊丧的大臣络绎不绝。今日午时乃是风水术士占卜出来最利于下葬的日子,淑妃的灵魂喧嚣三日之后终于要归于清净。巳时三刻,浩浩荡荡的送葬人群跟在棺椁的后面,又有大队的御林军护送,一步步踏入长安郊外的陵墓。
不管是否有心送行,送葬的队伍绵延几里。打头的是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紧接着是嫔妃同公主们,宫女随行侍候,最后是送葬的臣子。
茯苓同太华公主走在最中间,天气虽然晴朗,她却不由的觉得浑身一阵阵凉意,摇摇晃晃的跟着送葬部队步步前进。心里却暗暗替淑妃娘娘不值,她临死还在挂念皇上,而在皇上的心中,死后的殊荣便能弥补生前的错待,从办丧事到出殡竟全没出席。
“孝昌姐姐,我好怕,时至今日我才发现原来死亡离我们如此的近,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我也像淑仪娘娘这般突然死掉了?”太华公主被死亡的阴霾冲击了,偷偷扯着茯苓的衣服隐忧的问。
茯苓被她扯得回了神,表面上还是装着一副平静的模样安慰道,“别胡思乱想。”
随行片刻后,脚步停止了,一座不甚宽广的墓地出现在众人眼前。淑妃的棺椁慢慢落了下来,太子殿下走上前操持着最后的祭奠仪式。
“娘娘,等等奴婢,奴婢来陪您了。”突然,送葬队伍里跑出一个人高喊着直冲冲的撞在厚重的棺椁上,速度之快就连护送的御林军都猝不及防。那名女子顿时撞到头破血流。太子李瑛离得最近连忙上前查看,奈何她伤的太重只留下一句‘奴婢愿为娘娘殉葬’便香消玉殒了。
“是炽情!”茯苓呼吸一紧,凄寒之意从心底升起,忍不住闭上了眼睛。好一个贞烈忠心的女子,怪不得她之前一滴眼泪也没掉,原来是打定主意操持完丧葬后为主子殉葬。
“太子殿下,此女冲撞棺椁脑浆迸裂乃是横死,更何况此处乃是风水眼,若是将这名女子同时葬入墓穴不禁会破坏风水,怕还会与淑妃娘娘争夺地气。因此这名女子万万不得殉葬!”风水术士盯着死状惨烈的尸体微微皱眉,不认同的说。
“依大师的意思该如何处理?”鄂王李瑶呆呆的望着地上那滩殷红的血,心有不忍的问。
风水术士固守己见,“此女出身低贱,可另行安葬。淑仪娘娘的下葬仪式不能耽误,请太子已大事为重。”
“太子殿下,就依大师的意思吧。”高力士烦躁的定论。
茯苓心里冷笑,赫然出列,言简意赅的说,“太子殿下,炽情乃是淑妃娘娘的贴身宫女,侍奉娘娘一直虔诚恪己。君子有成人之美,太子殿下一向仁德,何不成全其美意?”
太子李瑛本就有此意,碍于术士的话陷入两难难以抉择,“孝昌妹妹说得极是,只是此事关乎淑妃娘娘身后福泽……”
彤玉冲了出来,跪在队首苦苦哀求,头叩在石子上顿时青了一大片,“奴婢求太子殿下成全炽情姐姐一片忠心,奴婢虽死无憾。”
高力士倒是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也没有,目光突然锐利起来,怒目骂道,“大胆奴婢,阻挠淑妃娘娘下葬,若耽误了吉时乃是当诛九族的大大罪,你有几条命能担待!”
“太子殿下,这般贞烈的女子自愿与淑仪娘娘殉葬,其情可嘉,赤胆忠心一片,若因她出身寒微而强行扭其心意,实在是让人不敢苟同。军旅之人多是出身草莽,若让天下人知晓皇族如此小觑出身寒微之人,天下之人又怎能心甘情愿为大唐尽忠卖命?”一名年约四十身着丧服的男子从队伍中走出,没有任何闪躲地迎上众人的目光,振振有词。
“毗伽可汗说得极是!”太子李瑛回头问身边的风水术士,“以大师所见可还有别的办法?”
“命虽是天生,却也可以人为改命。若是此女能得到皇上御笔亲封收为义女,命格自然便能高贵起来,届时母女相依不仅与风水有利还能达成其为淑妃娘娘殉葬的心愿。”风水术士撸着胡须回答。
太子当机立断叫来随行的杨琦吩咐道,“杨统领,你选上一匹骏马速去皇宫将此事禀报皇上,请示皇上的意思再快马加鞭赶回。”
“太子,皇上身体违和,你又何必为了这般小事去麻烦皇上。”高力士劝阻道。
“高爹爹,父皇最欣赏贞烈的女子,若是今日之事不禀报父皇,他日追究起来咱们都承担不了,您说是不是?”太华公主轻盈的走了出来,亲昵同高力士撒娇求情。高力士虽然不情愿,却不好说什么,只得由他们去了。
茯苓这才看向立在一旁的中年男子,此人生得虎背熊腰,满脸的络腮胡子间难掩豪爽之气。正待她打量他的时候,中年男子也好奇的打量着她们,她随即对他淡淡一笑,拉着太华公主退回到队列中去。
眼看日已将午,下葬的吉时就要到了,还迟迟未见杨琦回来,众人不禁小声嘀咕起来,顿时惹得一阵骚乱。
“圣旨到,太子殿下领旨——”又过了半柱香的功夫,杨琦才姗姗来迟,远远地下马,手持圣旨快步跑到队前疾呼,后面还跟着一队人拉着一副上好的棺椁。
“太子李瑛接旨!”
随行全部人员跪下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宫女炽情侍奉淑妃持躬谨慎,朕怜其一片忠心,特擢封为忠善公主,赐棺椁,准与淑妃母女同葬,钦赐!”
杨琦略带磁性的声音抑扬顿挫的宣过圣旨,交到太子李瑛手上。
“太好了!”太华公主拉起茯苓的手兴奋的说,茯苓红唇微启,无声的冷笑,都说生命无价,死后的殊荣却值得人这般欢腾!
炽情,人如其名,浓烈的情意忠于一人,归于平静。入葬虽然出乎预料多了些小插曲,结局还算差强人意,在一番繁琐的祭祀祈福之后,顺利将淑妃同忠善公主葬入墓穴之中。
晚膳后,茯苓回想起日间的一幕幕唏嘘不已,无法入眠。她披上外衣,推开窗户看天上的那轮明月。月色正浓,月色如斯,晕染了她心头的一点惶惑。人生代代无穷尽,明月年年望相似。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春尽红颜老,缓落人亡两不知。
门外,一个婀娜身影移了进来,“姐姐也没有睡意吧!”
“太华妹妹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茯苓欠了欠身,给她让了些位置。
太华唉声叹气,“傍晚高爹爹派人通知我,毗伽可汗已与父皇商量联姻之事,以冲喜为由要与大唐公主联姻。而他提名联姻的公主人选恰好就是在你同我中选一位。”
“毗伽可汗?我刚回宫不久,他又怎会认识我?”茯苓心里一惊,诧异的问。
太华苦涩一笑,“姐姐忘了今日淑妃墓前那名异族男子?前些年这位突厥可汗自愿拜父皇为义子,听闻淑仪娘娘殁了便前来吊唁,这般阴错阳差的选上你我二人。”
“父皇怎么说?”茯苓按捺心中的惶恐,焦急的问。
“还能怎么说?父皇虽然并没立刻答应,但他一向对和亲之事十分赞同,此事怕是已成定局了。”太华公主颓然道。
“妹妹且放宽心,车到山前必有路,再说有你母妃在,一切都会没事的!”茯苓出言劝慰,嘴边逸出一抹勉强的笑意。
两人接着聊了些闲话,直到夜深了,太华公主才起身回长乐宫歇息。和亲消息再度刺激了茯苓柔软的神经,躺下后思前想后,直至五更天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她不禁懊恼起来,还是太过年轻,不懂得收敛锋芒,才惹下这一身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