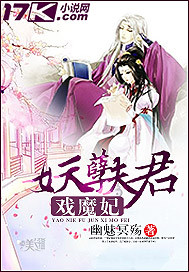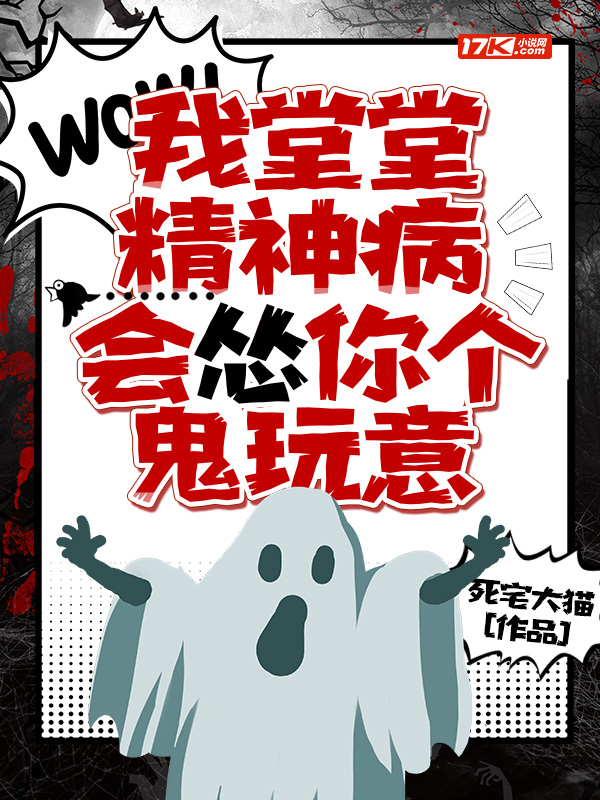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算活不过今日,她在要在死前安排好每一件事,否则就是死也不安心,想到这儿,皇甫德仪微微疲劳的眼眸中逐渐多了几分神采:“炽情,咱们回去。”
皇甫德仪回到昭德宫,茯苓等人从尴尬的境地里解救出来。
“娘娘,您可曾派人通知皇上了?”茯苓忍不住担忧地望向她轻声问。
德仪娘娘隐去眉间沉沉的无奈,难在抑制心头的苦楚,“听侍候皇上的高力士说皇上正忙于政事,外人不得打扰。一会儿本宫再派人去请请看。炽情,去寝殿将本宫的珍藏品拿过来。”
“是。”炽情盈盈一拜柔声答道,旋即进了内室。不一会儿她便托着一个八宝镶珠匣子走了出来。
“这里面都是本宫最爱的东西,本宫用不着了,你们随意挑选一两件留作纪念吧。”皇甫德仪接过匣子轻轻打开后放在几人面前,浅笑道。
茯苓连忙退却,“娘娘这是做什么,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人在日日说恩情,人死恩随人去了。皇宫之人最健忘,本宫送你们礼物只是不想彻底的被遗忘,想让人记住而已,难道你们连本宫这点微薄的要求也要违逆吗?”皇甫德仪轻声责备,语气中七分无奈三分悲切。说罢,轻轻叹息,秋水般的眸子里朦胧出些水雾来。
耳边这声短暂的叹息,让茯苓欲言又止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那恭敬不如从命,万春不客气了。这个玉蒲扇做工精致,玉面上的绘图也很细腻出彩,让娘娘割爱了。”万春公主形状优美的菱唇溢出清越的声音,从匣子里取出一柄精巧的扇子。
随即绮玉姑娘选了一只玉海棠样式的发钗,茯苓也随手捡起一柄由黑漆漆的石头磨成的把玩短剑,谷天祈则选了一管黑玉箫。
“谢德仪娘娘!”得了她的东西,众人齐声谢恩。
见到众人所选的礼物,德仪娘娘嘴边含着一缕暧昧的笑意,意味深长的望了望茯苓又瞟了谷天祈一眼,话中有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孝昌如此玲珑剔透的一个娇媚人同忠义侯站在一起郎才女貌,果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娘娘千万莫说笑,忠义侯的意中人并非孝昌。”茯苓审时度势,似玩笑般的说出这句话,希望这席话昭示自己无心于谷天祈,打消绮玉陡升的敌意。自进宫之后她常被孤立,不知不觉竟练就一副察言观色的好本领。
“喔?那就怪了,这一萧一剑乃是一位高人机缘巧合所赠,箫剑本为一体,经过能工巧匠独具匠心的打造后才成为现在的模样。据说这一萧一剑甚是有灵气,南唐时一对小夫妻因战乱走散,十多年后,正是靠着这一萧一剑相互之间的感应才找到彼此。古时有破镜重圆,岂知这一萧一剑也有异曲同工之效。今日这一萧一剑既已重新选择主人,自然也说明你们缘分不浅吧。”皇甫德仪依旧一脸平静,耐人寻味的笑在她嘴边荡漾开来,宫中之人最善察言观色,她又怎能猜不出几人的心思。
“娘娘误会了,孝昌生性柔弱不喜欢刀剑这种利器,刚刚只是觉得铸剑的材质不寻常,一时好奇便拿了过来。倒是绮玉姑娘英姿飒爽,想必也喜欢刀剑这种玩意,宝剑赠知音,既然箫已被忠义侯挑走,娘娘不如将这柄剑一并赏了给绮玉姑娘吧。”审时度势一番,茯苓马上有了主意,将手中的剑递给绮玉。
“那就依孝昌的意思吧。”皇甫德仪挑眉讶然,随即又在匣子里翻出一支白玉兰发簪顺势插在她的发髻上,退后一两步夸赞道,“这支白玉兰发簪与孝昌你的肤色很配,你看簪上多好看,比本宫当年可美多了。忙了一个早上,你们都回去吧。”
随着三人安静地退下,诺大的庭院人声散尽。
似乎连天公也感应了人心,天刚过午,天空便飘起雪花来,不消一个时辰,昭德宫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了。此时际,忽闻两扇朱红大门吱呀轴转,一片洁白的大地上突然出现几行小巧的脚印。
“惠妃娘娘驾到!”门口守门的太监大声唱和。
紧接着门帘轻掀,一股混着寒气的清冽香气冲了进来。
“妹妹来啦,快坐在炉火边烤烤火,天寒地冻的别生病了。姐姐将手头上这点活计做完便同妹妹详谈。”熟悉的香味传入鼻间,皇甫德仪也不抬头,一边说一边继续穿针引线,护甲划着织锦缎子发生倏倏的响声。
武惠妃冷眼旁观者皇甫德仪做女红,转念曼声道,“姐姐身子不利落,这些刺绣缝补的粗活又何必亲力亲为呢?若是病了又要被人说为了太子装病了。”
“回禀惠妃娘娘,我家主子怕皇上冬日膝盖痛,今日身子刚好些便执意为皇上做一对护膝,奴才们怎么都劝不了。”炽情端着上好的茶水进来,刚好听到她们的对话,不想自家主子如此被惠妃奚落,一边回答一边将茶水递给惠妃。
“姐姐教导奴才的能力就如讨好皇上的心思一般多年如一日从未变过,妹妹自叹不如,可惜皇上对姐姐并无几分挂牵。”武惠妃白了炽情一眼,嘲讽道。
“忙了一下午总算做好了!惠妃妹妹惯会取笑姐姐,论起对皇上的心思,后宫中哪比得上妹妹你呢。”皇甫德仪也不辩解,在做好的护膝上挽了一个结,转而对炽情温柔一笑说,“炽情,你们都下去吧,本宫同惠妃妹妹有些体己话要说。”
炽情等人鱼贯而出,轻轻的掩上门。
“德仪娘娘可以说了!”武惠妃冷冷的开口。
皇甫德仪淡然的眸子里隐隐透出凌人之势,搓着手露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若不是为了搭救太子殿下,姐姐我是宁死不愿说的,还望妹妹知悉一切后不要怪姐姐多事。”
“德仪娘娘就别卖关子了,皇上责罚太子殿下禁闭的处分已经撤除了,你如果不信大可以派人查探。”武惠妃声音里隐隐有一丝不满,恨意无限,“我已设法帮了太子,也到你兑现诺言的时候。我只想知道究竟是哪个挨千刀的害死我的孩子,不管他是何人,本宫一定要他血债血偿。”
“这可惜惠妃妹妹永远无法报这个仇。”皇甫德仪很是笃定,一字一顿的说,“因为杀你孩子的刽子手是皇上。”
“你胡说!”武惠妃玉手一扬,拍桌而起,怒目圆睁。
她到底抛不开对皇上根植于心底的情愫,皇甫德仪心知自己这场赌注赌对了,加大打击力度,又加重语气补了几句,“如果妹妹不信,为何如此动怒?你动怒只是因为这个人你心里早就怀疑过,如今本宫提出来,与你的想法不谋而合,你无法相信而已。”
“你有何证据?”武惠妃颓然坐回座位上,蓦然问。
“妹妹自入宫就盛宠不断,不只是因为妹妹容貌出众,很大一部分在于妹妹同武家、同太平公主之间的渊源。记得当初皇上还未登基,妹妹因父亲早亡一直被养在宫中,与太平公主的交情甚好。皇上靠太平公主才能平反宫廷之乱,自然对太平公主大力引荐的你宠爱有加。那时皇上虽然手执龙印,朝中大权却尽在太平公主的掌控之中,所以皇上登基之后对你更加体贴入微,那些都是为了做给太平公主看的。皇上尽管十分宠你,却不能在那时与你孕育子嗣。故而接二连三的制造事端,造成小皇子因病夭折的假象试图瞒过太平公主及其余党。”皇甫德仪娓娓道出一段辛酸往事。
“我不信,皇上对我情真一片才不会这般残酷的对待我。肯定是你,是你得不到皇上的宠爱故意诋毁皇上,试图离间我与皇上的感情,你好恶毒的用心。”武惠妃执帕的手一直在抖,眼中水波谲诡,恶狠狠的指着皇甫德仪骂道。
“就知道妹妹不信,我这里还保留着丽妃娘娘死前的忏悔书,你自己看看吧。”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丝歉意浮上皇甫德仪的眼眸,随手拿起桌上的信封交给武惠妃。
怀着纠结的心情,武惠妃颤抖着展开泛黄的书信。
“德仪妹妹: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们姐妹怕已阴阳两隔了。姐姐自入宫便与世无争,待人谦卑恭敬温顺,原想就这样了此一生,却不想迫于无奈做下几件丧尽天良的事情。
妹妹素来知道我常常被噩梦惊醒,常常伴有心悸之痛,也全因这件事而起。这十年来我一直难逃良心的谴责,时常梦到惠妃夭折的孩子在我耳边哭泣,厉声向我索命。
我心中有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太震撼也太肮脏,生本洁来还洁去,我不想将这个秘密带到棺材中,故而对妹妹一吐为快。当年皇上为了牵制太平公主的势力,宠爱惠妃。因不想惠妃诞下麟儿为太平公主所用,皇上命我在惠妃诞下皇子后将金针刺在皇子的胸口,这样皇子安然活上半月一月便寿终正寝了,就连御医也诊断不出死因。我如法炮制一连害了惠妃三名皇子,有今日冤魂索命之报应罪有因得。
你我早已身为人母,自然知道丧子之痛对十月怀胎的母亲打击有多大。虽然我不喜欢惠妃,却对她有着深深的愧疚。惠妃虽然飞扬跋扈,却也是无辜的,接二连三的痛失爱子。这些年我们姐妹互相扶持走过来,临终前,我有一件事求妹妹帮忙,请你日后在与惠妃的相处中,体会一下她所经历之苦难,莫与她较一日之长短。信封上所说之事还望妹妹守口如瓶,终生不对第二人言,妹妹若能照拂我那可怜的孩子瑛儿一二,我九泉之下也瞑目了,来世定结草衔环为报。
丽蓉绝笔”
“皇上——”武惠妃面色惨白,往日之事慢慢恢复清明,在脑海里串了起来。她手一抖发黄的信封轻轻的散在地上,丽蓉正是丽妃娘娘的小名,笔迹她也认得正是丽妃的,由不得她不信。
皇甫德仪望着珠翠映衬下的惨白脸庞,柔声道,“皇上那时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迫于无奈之举,还望妹妹宽心。”
“皇上指使丽妃害死本宫的孩子,难怪对我这般好!可笑,可笑啊,难怪皇上立丽妃的儿子李瑛为太子,丽妃是皇上的大功臣帮皇上除掉本宫的孩子。”武惠妃眼中的神色比往日寒上千万分,几近崩溃,一下子扣住皇甫德仪的手,指甲都勒进肉里了。
若能化敌为友更好,皇甫德仪见她如此凄惨,心中也升起一丝恻隐之心,没有挣脱任由她抓着,眼中充满同情的劝慰道,“惠妃妹妹千万莫怪丽妃姐姐,她日夜受良心折磨已故去多时,我劝你还是放下这些恩怨吧。”
“虎毒尚不食子,皇上您真是好狠的心呐。”武惠妃猛地甩开她的手,摇摇晃晃的出去。
雪下得很紧。皇甫德仪望着惠妃踉跄的身影,嘴边扬起一抹得意的笑,轻叹,“丽妃姐姐洞察一切,果有先见之明,预留的信函总算派上了用场,相信惠妃同皇上之间的隔阂再无法解除,惠妃也再难相信他人。”
天地苍茫,她一人茕茕而立。她知道自己成功了,成功的用丧子之痛离间了惠妃同皇上多年来的感情,这场赌注她赢了,却说不出是喜是悲。
牵情惹恨两三番,虽然生命只剩一日,但好戏已经铺垫好,只差日后的引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