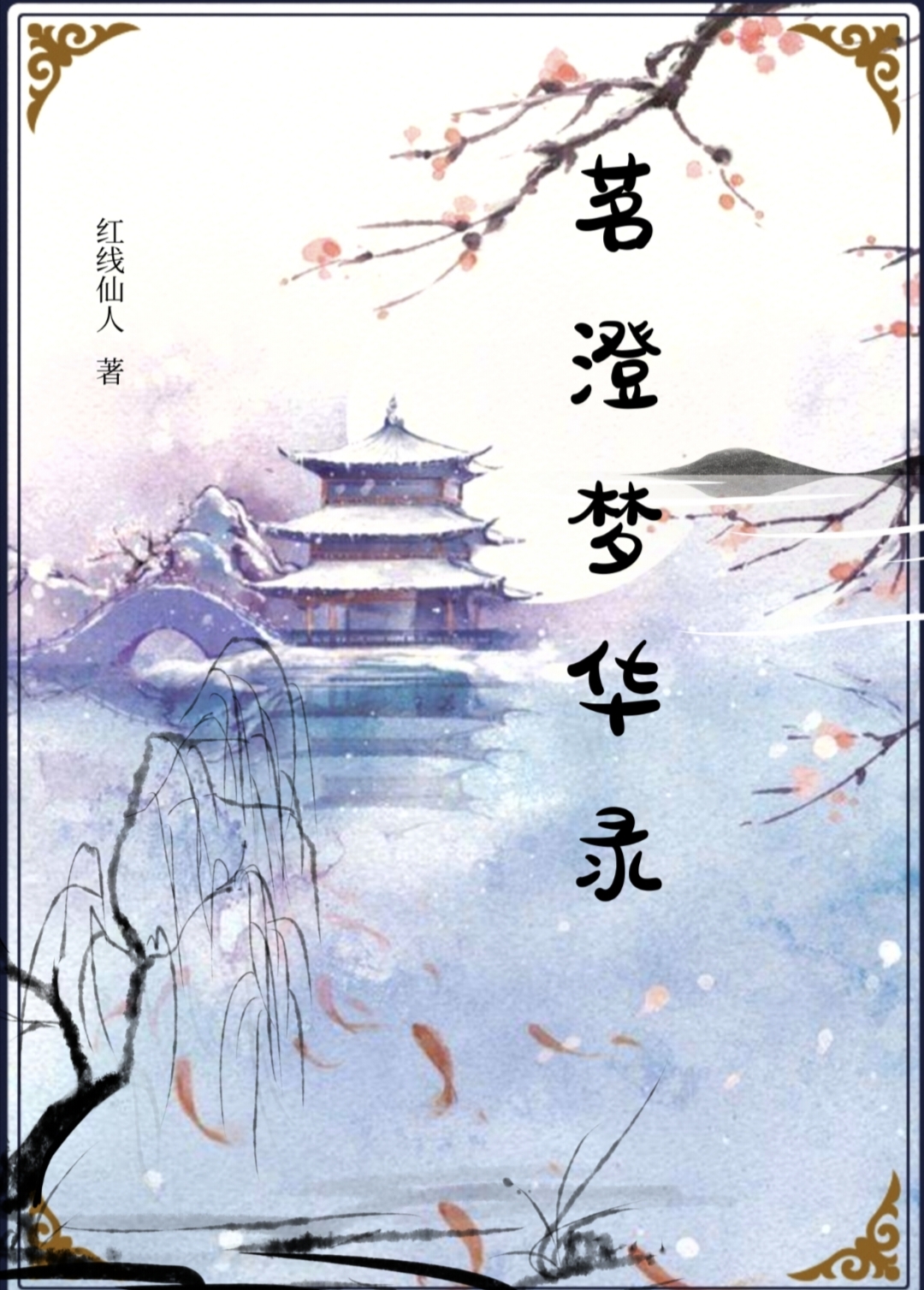范秦苑自从入了清风书院可以说是意气风发,短短半个月已经坐上史令官的位置,而他又通音律便被派到御音司,与其他人一同完善泰山祭祀的乐曲。泰山祭祀是皇帝登基后为求国泰民安而准备的大型祭祀活动,李隆基因蝗灾将泰山祭祀推到明年春季,而现在则是准备阶段,除了礼部外,户部,工部都有参与,清风书院则担负起明理,施礼,德贤,修乐的重任。
“胡闹,此段加入竹笛,轻浮缥缈,音虽空灵但祭祀是与神明的沟通,怎能轻挑。”范秦苑将手中乐谱重掷在案几上,理论着。
坐在一旁的是礼部派来监事王良,他不通音律只是配合御音司按照祭祀顺序准备乐曲,见他急了眼便和声说道:“范大人莫要急,这部分只是衔接而已,总共时长也不过半柱香,以往都是如此。”
“哼,以往?难道前人就没有犯错的时候吗?乐曲主律重要,这连接之处也不能忽视,你且放在这,等我改好了再来取。”范秦苑说完话,便陷入沉思。
王良本想着今日把乐曲带回去,开始准备器具排练,没想到还要再来,有些不乐意,笑着说:“范大人,这段薛总司已经看过了,您只需要加上注释签上名字便可以。”
范秦苑冷言令色道:“胡闹,既然让我负责,我就有权审查修改,既然有不妥怎能随便了事。”他想这样的乐谱虽然也能说得过去,但要签上自己的名字自然就是自己认可的作品,他是断然接受不了如此的瑕疵。
王良见他执迷不悟,心想或许他是新来的人不知道薛林凌的名号,想逞能罢了,“范大人好大的权利,只是薛总司已经首肯过了,你难道还能看出什么不妥来吗?”
范秦苑见他三番五次的搬出薛总司,心中诧异,还是身后的同僚提醒道:“薛总司就是薛林凌,负责御音司和御舞司的总教司。”
薛林凌是太平公主的第二个儿子,从小得父亲言传身教,精通音律古谱,年少时与李隆基同在宫内学习,又因同爱古琴,善编曲,趣味相投成为了知己,李隆基登基后其母想要发动政变他曾苦劝无果,便自愿进入清风书院学习,不理朝政。
在御音司的官员对他还是很佩服的,别看年纪不大,已经是名声在外,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独自一人修复古曲《鄢陵曲》,也是因此才成为清风书院的总教司。
范秦苑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便继续陷入沉思,王良见他置之不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赌气出来拂袖而去。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出半日薛林凌便已得知,不过他到不在意,那段乐曲他也觉得用竹笛不妥,只是并未找到更佳替代,暂且维持原样就好。
“陛下最近甚是疲惫呀。”薛林凌站在厅内,将手中的卷轴递给苏盛,温文尔雅的说,“臣已将《永宁曲谱》修复完成,请陛下过目。”
李隆基摆摆手烦躁的说:“稍后再看吧,朕正有一事烦心,想听听你的意见。”
薛林凌拱手说道:“愿为陛下分忧。”
李隆基命人展开一幅画卷,走下来指点说道:“这幅画是大食国使者送来,说是六月初六会有使团来洛阳朝圣,希望到时能用此仪仗迎接。”
薛林凌走上前仔细观瞧,画上是由十二人组成的仪仗,衣着也是大食国乐师的样子并无奇特,待他细看才明白,原来十二人手中各有一乐器,有的似萧却无孔,有的如蛇盘在手中,有的像月亮中间是一根根丝线。
“这些应该是大食国的乐器,这个与我们的箜篌很是相似,名曰:竖琴。而这个称为胡笳,臣曾在清风书院的聚宝阁中见过,另外这些似有印象,不过还要待臣去查查典籍记录。”听薛林凌这么说李隆基稍有安心,吩咐苏盛赐腰牌准许随时入宫查阅典籍。
“不过,知道名字与能演奏相差甚远,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似乎不太可能。”李隆基消瘦的脸颊上依旧愁云不展。
薛林凌提议道:“陛下为何不贴出皇榜,征选能人贤才呢?”
李隆基当然也想过,只是如此一来大食国使臣必然得知,恐会笑话大唐,他摇摇头说道:“此事不宜张扬。”
薛林凌心领神会,又提议道:“那不如在清风书院之内张贴告示,近半年来清风书院也集贤聚才说不定会有深藏不漏之人。”
这倒是个办法,很快消息便传遍整个书院,这里虽叫书院其实就是朝廷的储备干部培养所,人才济济。
“薛总司,外面有人求见。”侍从回话。
薛林凌正在研读《百乐集》,希望能找到些大食国乐器的蛛丝马迹,他这样已经三日,并且谢绝会客,“何人,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要来烦我。”
“他说他叫范秦苑,是为大食国十二乐器而来。”侍从回话,薛林凌心中甚喜,又觉得这个名字不曾相识却有些熟悉。
“范秦苑?是何人?”薛林凌端起茶杯问道。
侍从想了想回答道:“本月初兵部尚书推荐来了,号称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现为史令官,在咱们御音司负责审查泰山祭祀的副乐部分,前几日与王良大人争执的便是他。”
“哦。”薛林凌饶有兴致的玩弄手中的茶杯,自言自语道:“就是那个号称要修改唤神曲第二篇章的人呀,让他进来吧。”
范秦苑昂首阔步的走了进来,手里面拿着卷轴,身后像是背着一把宝剑,不过用布包着看不出来具体是何物,他脸上似有得意之色,入厅后拱手说道:“臣范秦苑携新谱唤神曲第二章八节,请教薛总司。”
他新谱了曲子?薛林凌有些吃惊,心想唤神曲依祖制谱写,怎能随意修改,真是不自量力,“范大人恐怕要白做功了,唤神曲乃是按史册谱写修缮,就算你的新曲绝妙也难以选用呀。”
范秦苑并不在意,从身后解下布袋,拿出一陌生乐器,淡淡的说:“还请薛总司听过再说。”说罢他独自演奏起来,乐声袅袅,音色浑厚,给人一种大气沉稳的感觉,庄重而又诚恳。
旋律似改非改,唤神曲薛林凌再熟悉不过,主旋律丝毫没有变化,只是辅音去掉了之前的回转和跳动,更符合唤神这庄重的情景。
一曲毕,二人皆不语,不过心思却出奇一致,这样的更改绝对堪称完美,薛林凌心里清楚,他没有拒绝的道理,只是他现在更好奇范秦苑手中的乐器,从外表上看更像是大食国的胡笳。
“范达人手中乐器可是胡笳?”薛林凌直截了当的问道。
“正是,臣前来也为十二乐器图,臣不才,年幼时随父亲周游各国,接触过大食国的乐器,心里喜欢便也学的一二。”范秦苑的眉目间放着光芒,可见他对此胸有成竹。
薛林凌淡淡一笑,同是年少成名,他见过太多夸夸其谈的人,对于范秦苑的一番话,他也是将信将疑,“既然这么说,那就请范大人给在下讲解一番。”
侍从听此话正转身要去取画轴,却听到薛林凌高声说道:“取笔墨纸砚来,范大人边画边讲不是更生动?”
范秦苑心想:看来他是不相信我,怕我对着画卷胡诌。也罢我也不需要那些粗制乱造的东西。
如此,范秦苑一边凭着记忆一边画出十二乐器图,每一个图比画卷上还要详细逼真,而他所讲不止于材质,用法,演奏手法更涉及音色特征,代表作品等。
薛林凌很是震惊,没想到他说的如此详细,只有真正接触过的人才会如此,他向侍从使了个眼色,对方马上明白,将范秦苑所说之话一一记录下来。
本以为一番介绍后,薛林凌会大吃一惊,忙不迭的请他上座,谁知对方居然淡定的请他先回去,稍后再议。
忿忿不平的范秦苑只能先回去,他住在皇甫府,皇甫青岩也算是礼贤下士,每日都会与他们把酒言欢,今日见他郁郁寡欢便与他单开一席,在湖心亭内饮酒。
皇甫青岩将酒杯满上,询问道:“范兄今日为何如此沮丧?”
范秦苑摆手说道:“不提也罢,我本将心为书院,怎知薛总司的心思我摸不透。”
“哦?为何这么说呢?”在皇甫青岩的追问下,他把今日之事说了一遍。
谁知他还没有什么反应,皇甫青岩竟拍案说道:“岂有此理,他怎能如此对待良材,范兄我真为你不值。”
范秦苑听说心中更加愤恨,可是自己人微言轻,又能如何。皇甫青岩仗义的说道:“范兄不必担心,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我就不会置之不理,总有办法能让陛下知道一切皆是范兄功劳。”
听他这么说,范秦苑满是感激,激动的说道:“皇甫兄为我仗义执言,我实在无以回报,唯有以此酒谢之。”
皇甫青岩连忙拦道:“哎,范兄言重了,来我们举杯畅饮。”
话说回来,薛林凌的确带着范秦苑所述,一字不差的回禀李隆基,不过他同时也回禀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并把范秦苑重谱的唤魂曲一并献上。
李隆基得知后很是欣喜,兴奋的问道:“真有如此才人,快传来让朕见见。”
薛林凌拱手说道:“陛下且慢,容臣多说一句,此人虽有大才,不过难免有些心高气傲,臣担心他会顶撞圣驾,所以暂且没动声色。”
李隆基笑了笑,打趣道:“就如当年的你吗?朕记得那时候皇祖母还健在,让你用板笛演奏,没想到你竟然砸了御赐的板笛,说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寻得能配上你的天下无双的板笛,那时候的你才叫心高气傲。”
薛林凌羞涩的笑了笑,惭愧的说:“若不是入了清风书院怎会知道山外有山,自己那时候真是狂妄,现在想来也是可笑。”
李隆基轻叹口气,若有所思的说:“若能回到那时也不为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