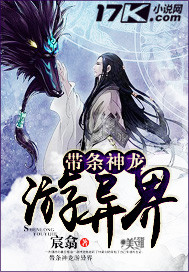母亲时不时的叮一句:别闹了,舒儿,快吃你的早点,都凉了。我这一闹也令各色丫鬟心思活络,边开言细语边摆放收拾,我躺在地板交手抱怀,见素沁已缓缓起身,弄衣还理憋笑意,红了双颦娇艳欲滴,以前不大在意的一对小酒窝陪衬着唇下的美人沟现在看去显得如此美艳不可方物,我不禁看呆了。素沁见我目不转睛的盯着她,脸上不由更红,瞟我一眼后便转身,急匆匆的走进了里屋。
当手不自觉得捂到嘴上时,闻到手上她存留的体香充满了心房,我躺在地板上心也柔软了眉眼也笑了。以前也跟她玩闹,怎么就没感到如今天般如此醉人,血液里慢慢苏醒的躁动让人迷醉。适时母亲看向我,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舒儿该长大了,快点吃早点都凉了。”我以为母亲担心我饿着了,往后我才真的听懂了这句话。
丽萍筹措望着眼前大公子,见他矗立院中向着宁熙堂出神凝视,眼里泛泪光,自不敢出声打扰喊禀报,又不敢起身忘礼数,唯有双手护左膝持跪姿等通令。良久赵忠廷闻得笑声渐止亦回神正容装,感慨起自身与母亲:
相聚容易同乐难,
无力追逝话悲凉。
十月惊天乾坤震,
失亲失势失安良。
家道已是独木难支,十六年前太子之争失去父亲又失去了多少忠良,遗留的暗潮依然涌动令他如履薄冰,一旦当今皇帝不在失去这唯一的有力庇护,若再遭逢浩劫凭己之力绝难善存,他岂能不忧之哀之。“丽萍你起来,给我母亲通禀一声。”赵忠廷转向丽萍作请起手势。
我喝着莲子羹,手抓糕点狼吞虎咽,闹了这些许时候确实有点饿了,刚放下玉碗就看到大哥缓缓走了进来,虽然年岁二十六,却以磨难炼就刚毅沉稳,但眼神却难掩忧色。“儿子给母亲请安,敬请福安。”赵忠廷跪安道。
“忠廷,快起来,这一早过来吃过没有?”母亲每每看到大儿子都不得不强忍怜悯,想到这十六年来这个家一直是他扛着过来的,面对这大儿子虽觉愧疚与痛心,但自从丈夫屈死后早已心如死灰,要不是舒儿刚巧出生只怕也随他而去了。赵忠廷见母亲眼神渐泛空洞,怕她又缅怀过往忙回道:
“儿已经吃过了,
这次来我是有要事相商。”
说完看了看我,显然不想让我听到,这就是我大哥的顾虑想来也是我母亲的顾虑:
沉心事历历锥心,
腥风血雨过一人一重山,
无言相对唯有泪眼四行,
自不想再添愁苦再添人,
身所处已黑暗无边,
自想留此光明照心间。
他们的悉心呵护,
多少年回想起来,
都令我感动不已,
母亲望向我:“亦舒,你回自己屋看诗书或玩都随你,但绝不能离家独自出去。”我应了一声知道了,便起身往外走,一步一回头:
“娘,我就不能听听吗?”
“我真的不能听听?”
“要不让我听听嘛。”
他们绷着脸强忍着不发作,面无表情的四目盯来,我也来个吊眼吐舌作了回敬,才真的走了出去。
多年以后我才从大哥口中得知今天他们之间的对话:大厅上已屏退左右,大哥面色凝重开口道:“母亲,我们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了,皇帝年迈近来病的越来越频繁,已经有一年不问朝政了一直在乾清宫养病,这都是一年前的消息了我最近才探得,儿子没用啊!”说到这眼泪便欲夺眶而出,母亲摆手劝慰:“廷儿,这怪不得你。”自己却也红眼泛泪光。
“十多年了,
我们花钱无数,
却经营的如此凄惨,
可想而知,
我们的对手有多强大了。”
母亲不禁流下了无奈的泪水。
大哥无奈接道:“我们毕竟是十几代的世袭国公,期间拜相封侯能人辈出想不到现今却落得如斯境地…唉!我们是有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可是在政治斗争面前一旦失去均衡,再多的钱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真是兵败如山倒。”
母亲说道:“今天之死局,虽说是你父亲从参与太子党争开始便注定的,却不失为血性男儿,当时你父亲为了天下百姓实施改革,要颠覆到他们的利益,双方都箭在弦上实在是不得不发,怨不得你父亲。”
“儿子不敢,
只是不由感慨而已。”
“母亲知道,
你只是心生惶恐,
不由感慨。”
大哥低头应道:“儿不该惶恐,母亲说的是。”略停顿后,接着道:“母亲,儿子觉得也该让亦舒弟知道了,让他心里扛些事对他也是有好处的。”母亲抬头望着大哥说道:“要是真的能逃的出去自是要让他知道的,但你是知道的,从出事的那一刻起,这十六年来国公府由重兵封锁,再转由暗哨监控明里暗里你知道有多少重吗?
恐怕连家里有几只苍蝇他们都能一清二,你说凭我们能逃的出吗?我们已经是暗无天日,你忍心你弟弟也心坠地狱?”母亲忍不住已泪眼哽咽道:“我们这十六年来,是怎么过来的你难道忘了?因为我们的守护,才不至于心里被黑暗完全淹没,多少让我们心里有点光亮,才不至于让我们了无生趣。如果没机会能逃出生天,我是宁死都不会告诉他的。”大哥更是泪流不止,
母亲接着道:“但你也别以为你弟弟什么都不知道,他心灵透亮着,我们每次谈话不让他听,他就不听更不会偷听,都独自回屋看书,不让他出门他就真的从不走出家门一步,整整十六年啊他只能从书上从窗户上来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知道他爱做梦,他这是在体谅我们。”母亲已泣不成音。
“廷儿,娘是了解你的,
你是个好孩子,
你已心生恐惧,
今天才会完全乱了方寸,
勇敢点孩子,我们不怕。”
大哥不由得已哭出声来满怀歉意的喊了一声:“娘…”
母亲接着道:
“打明天起你给我振作起来,
好了回去休息吧。”
大哥起身擦干了眼泪,便要告辞,忽然醒起还有一事未说,他才真的感到自已经方寸全乱了,
大哥忙说道:“娘,昨天我碰到一怪事还没向你说,昨天我出去碰到了李释,不,应该说是他找的我,丢下了一句三天后寅时开后门谨记,然后转身就走了,要不要照他说的办?”
母亲想了想后问道:
“李释?廖魏袁的人?”
大哥应道:“是,是们我最大的仇家的人。”母亲缓缓道:“现在以我们这般境地却是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你照他的去办,也许他就是我们最后一根稻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