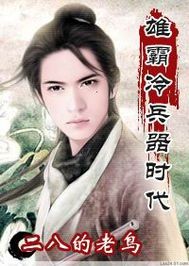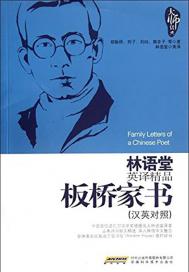浮士奴说:“王,据可靠的消息,南方伐檀等地,人烟荒芜,刁民野众,多有造反生事之人,而 原因多是因天灾瘟疫防控不济而造成多地死伤无数,况且我天宫边界亦有此种情况发生,望王斟酌,以示天下。”
葛朗黑聋看了看这个倔强的老头,又是一通手势的比划,十听户认真的看着记着说着,生怕惹了这个病太岁,童杰转身对旁边的沙华曼珠说:“我们的黑魔图说,大国师,你有什么看法没有?如果有,王请你说一说。”
这老贼沙华曼珠就是个犟眼子,尤其是对浮士奴,好像这俩老头就是一对冤家对头,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斗来斗去,所谓好人坏人都得有,不然这个大黑城早已土崩瓦解,如摧枯拉朽一般,就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沙华曼珠暗道:“怎么着?想着邀功请赏啊?没门儿。你邀了功请了裳,我还往哪里摆,我岂能让你胡作非为,想怎样就怎样?你把我沙华曼珠看的也忒不值一文了,你不是认为那样不对吗?我就偏说它对,跟我对着干,浮士奴,你等下辈子吧。”
于是,沙华曼珠施礼说道:“王,我觉得大梵士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我为何如何说?我是有充分证据的。这事就像是家长里短的小事,难登大雅之堂,是不足以在大殿上议的,可是大家看一看,那浮士奴大梵士为什么还要在大殿上这样说呢?我想,他是有企图的,这样的小事,对王来说,有污蔑王英明神武的嫌疑,王,日理万机,岂能如此不顾国家的利益,而只为自己的私利处心积虑,足最后只是为王徒增烦恼,为大家徒增笑料,为自己徒增一些羞耻罢了。天下谁能匹敌?王者,无可匹敌。”
沙华曼在大殿之上大放厥词,珠满嘴火车,他觉得他这是对葛朗黑聋最直接有效的控制之法,便是在葛朗黑聋的无声世界里,充分发挥他的优势,让他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个真正赤胆忠心之人,于是他扮演了一个表演者,而浮士奴扮演一个说事者。
他们都在为着自己的心中所想而竭尽所能,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彼此都懂得,只有扮好自己的角色,才能让天下太平。
在世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愿意接近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这样的人的人,就成了你的反对者,于是人们就说亲贤臣、远小人和亲小人、远贤臣,结果谁是贤明者,谁是小人就有了界定了,仿佛人君人臣一样,既有明君昏君,也有贤臣佞臣,泾渭分明。
果不其然,沙华曼珠成了黑魔图的座上客,他幸灾乐祸的陪着葛朗黑聋到后殿的鬼名堂逍遥快活去了,而其他的一些人也就作鸟兽散了。
“昏家,早晚大黑城要毁于一旦,他就是始作俑者。”一个将军说道。
浮士奴回头一看,说话者不是别人,正是同僚天玺将军。
浮士奴听了一笑,说:“天玺将军,怎么突然有如此的感慨,莫要他听了去,免得有无妄的祸,以后休再说这样不着边际的话,莫要失了将军的体统。”
天玺将军不服气地说:“那沙华曼珠有个啥子鸟本事,就凭他能变个戏法,糊弄黑魔图,换成是我,我才不上他的当呢。”
浮士奴听了又一笑,说:“你看这日头,快到吃晌午饭的时候了,走,去我家,正好我刚托人从老家带来一些土特产,一起尝尝,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好消息吧,你说呢?”说完,浮士奴哈哈一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天玺将军一看,浮士奴还能笑出声来,更是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说:“老师,你还能笑出来,我真弄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浮士奴一边拽了一下他,一边笑道:“不知道怎么想的,就不要去想了,那你就想着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就行了,这不咋们又到吃饭的时候了?走吧,去我家。”说着,他们师徒二人渐渐远去了。
话说葛朗黑聋,他早已把大殿上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此刻他怀抱媱姨,正在鬼名堂的鬼魔三道中,玩着鬼灵精怪的游戏。
这媱姨天生妩媚,放诞风流,又因吃了燕马峡的瑶草,变化得极妩媚动人,小弛则声色,大纵则淫邪,侍寝承欢,昼夜云雨,葛朗黑聋自然是十分宠爱于她,亲切地称她为媱姨。
媱姨原来并不叫媱姨,她叫勾饶,是天宫城牧竖十二世时期,九星八门中第四上流派的精英先生黄麻的老婆。
说起这一段往事,真是让人感叹,女人因爱慕权势而背叛男人,男人因女人背叛而沦为了阶下囚,而祸起的源头,就是葛朗黑聋在雍己宫大摆宴席,宴请群臣,百官家眷也许可带着,这是十听户特意交代的。
在宴会上,刚开始时,葛朗黑聋只是咧着大嘴笑敬百官酒水,并未十分在意众位官家的眷属。
这时,突然有人提议,以舞助兴。
可是十听户在宴会安排上并没有这一相,这可急坏了易龟,在这关键时刻,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听户大人,这有何难?刚才他们不是都说了吗?以舞助兴,这女人只要脸蛋儿好看,模样儿俊俏,能让魔王高兴,其他人也就是一个陪衬罢了,你看见美,黄麻黄大人的老婆就非常的合乎咋们的要求,你看那模样儿多迷人、多让人想入非非……”
还没等这人把话说完,易龟的脸一耷拉,说:“放肆!那是前城的重臣的家眷,岂能无礼!”
说着,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着黄麻身后望去,不看便罢,一看这小子的口水都流出来了,说道:“美,美,美,真是太美了!你怎么早没有跟我说啊?”那人答道:“听户大人,这不是人家头一次来雍己宫吗?”说完,他看着易龟偷偷地乐,易龟猥琐地骂了一句,转身准备去了。
这时,易龟先来到葛朗黑聋身边,比划了几下手势,他的意思是说,王,为了以舞助兴,我们特意挑选了黄麻黄大人的内眷为大家助助兴,你看行吗?
葛朗黑聋顿时咧嘴大笑,扭头望向正在喝酒的黄麻,与此同时,黄麻突然脸十听户管班的易龟在葛朗黑 聋面前比划来比划去的,偶尔他们还朝着自己点头笑笑,黄麻暗道:“不知道这十听户又在打什么歪主意。”
正在想着,这时易龟绕到黄麻身边,弯腰笑道:“参务大人,卑职与您有一事相商。”
黄麻一扭头看了他一眼,笑说:“易听户,请讲。”
易龟说:“参务大人,刚才大家伙不是说要以舞助兴,可是宫里暂时没有准备,所以,我跟魔王商量了一下,想请贵夫人给大家跳上一曲,不知参务大人意下如何?”说完,易龟扭脸看了勾饶一眼,(当时她还没吃燕马峡瑶草)顿时心生荡漾之情,心猿意马,不知所踪。
易龟见黄麻有些犹豫,便又说道:“参务大人,要不这样,让夫人表态,她若愿意就去,她若不愿意我再去给魔王说,你看怎么样?黄大人,救救急嘛!”说着,黄麻扭头看了勾饶一眼,只见她长长的眉,杏核的眼睛,椭圆形的脸蛋,古铜色的皮肤,看上去,千娇百媚,万种风情。
在来之前,黄麻说了赴宴可以携带家眷的话后就有些后悔了,这本是个招摇的婆子,唯恐自己被当作下贱的人而被遗忘,她害怕遗忘,害怕让她学会了卖弄风情,鼓动风骚,黄麻既爱又恨,说道:“刚才易听户的话,可能你也听到了,你自己拿主意吧?”
只见勾饶那勾人魂魄的眸子先望了易龟一眼,然后又瞧了黄麻一眼,欲说还休的样子,说:“难得魔王有如此的雅兴,难得大家有如此的雅兴,我倒是可以。试一试,只求魔王不笑话就是了。”
易龟听了不禁眉开眼笑,说:“夫人爽快,夫人爽快。”
然后他扭头对黄麻说道:“参务大人,夫人竟是如此重情重义之人,实为大人的福分啊。好,先
这样,我去一下。”说完,他向勾饶笑了一下,便转身离去了。
易龟把商量结果给葛朗黑聋一比划,葛朗黑聋看了大喜。
就这样,勾饶便开始舞动起身子,跳起了《妖娆舞》,一言以蔽之,翩翩起惊鸿,婉婉落游龙,令观者无不如痴如醉,禁不住的摇头叹息,最让人无可不可的是葛朗黑聋,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能让他达到一种如癫如狂的地步的女子,但勾饶做到了"
一曲终了,勾饶收势,谢过便回到原来的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这样傻傻的呆着,楞着,仿佛整个世界的心思都被她的舞勾去了,一去不复返。
这时,易龟突然咳嗽了一声,对葛朗黑聋快速比划道:“王,王,舞结束了!舞结束了!”
葛朗黑聋兴奋地对易龟比划说:“太美了,!太美了!”
与此同时,大家都赞不绝口,对黄麻投去了羡慕的眼神。
大家还接着开怀畅饮,但葛朗黑聋坐不住了,他太想得到这个女人了,这种心情便不自觉地从他的眼神里表现出来了,他总时不时地瞟这个女人,这种不正常的举动被十听户的童杰注意到了,童杰比划说:“王,我有个主意,可以让王彻底拥有这个迷人的女人。”
葛朗黑聋比划说:“快说,什么办法?”
童杰说:“王一会去给黄麻敬酒,以滴酒沾地的罪名治了他,以后的事就看王的了。”
终于,葛朗黑聋如愿以偿;同时黄麻下狱。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存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两相倾轧、欺骗、傲慢、成见……
棉化其人,本是九星八门中第五上流派的精英先生。俗话说,君子有君子的善济,小人有小人的盗道。
棉化假道乱政就是一盗门道。他给葛朗黑聋进贡了四个堪称风华绝代的食花捕藤,沉凫破镜。他(她)们是食花汤婵,叫奴是也;捕藤赜人,汤婵侍女;沉凫亢阳,如宾是也;破镜吏瑕,亢阳表弟。
此时,后殿可谓是乌烟瘴气,妖气冲天,大黑城的气运,仿佛那希拉波利斯的地狱之门,在悄无声息中慢慢地打开了……
回头再说水影,他仔细咀嚼这八句谶语儿,可惜他只道破了六句,前四句:土儿围墙,白刀儿王,休呀休休,娶了个娘,就是城隍囚女四字,末两句:娘盼雉儿,枉断了肠,重点是“枉”字,可以解释为徒然、空、白白地,就是空叹息的样子,这样看来,安娜凶多吉少,至于五六两句:荷花儿开,莲籽儿荡,实在没有头绪,索性就不再去琢磨它了,但又不是说真的不去琢磨,而是说通过自我肯定暗示,让自己不要有过分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个人在路上时,总是这样,当百无聊赖的时候,觉得时间像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慢条斯理的;当心有归属的时候,又觉得时间像是借了得意的春风似的,风风火火的,这就是人的心情好坏,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水影先生到了城隍庙,他突然有了一个灵光乍现,那五六句谶语会不会与奈都有关呢?但是这种想法又一闪而过,没有太在意它。他一边朝着庙门走去,一边有意无意地四下张望,这里哪还有人经过,分明就是天宫城人遗落的地方,偶尔有几个从地里干活的苦力从这儿路过,但他们根本不会在意庙里的事情,虽说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庙,但在人们的心里还是存在一些敬畏之心的,毕竟,这是每一个天宫人曾经心灵寄托的地方。
城隍庙的庙门说是庙门,其实就是有人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一个挡板把它挡在那里了,而门口也只是一个半人多高的洞口,这都是年头久了没人修缮造成的,但是并不妨碍人们从这个口子进出,只要半蹲着一弯腰就轻轻松松地进入城隍庙了。
水影先生在进庙门前,又左右环顾了一下,然后把挡板推到一边去了,一弯腰钻进了庙里,一回手又把挡板照着原来的样子放回到原处,一转身开始打量起眼前的事物,只见东倒西歪的神像也是断臂的神像,摆放香炉的桌上到处都是灰土,往地上一看,在一片狼藉的屋子里面,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垃圾之类的东西,再猛地一看,发现在过道的地方,按常理上它应该是一层厚厚的灰土,人一走过,灰土盖满脚面,而这里却截然不同,仅从地上踩的印记判断,这里明显有人经常往来穿梭的痕迹,而且还是一个女人的脚印,这一点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他心说,这会是谁的脚印?(这一印记证明慧儿没有说谎,也就是说,沙华曼珠绑架了安娜。)
水影从一豁口望见了外面刺眼的阳光,估计此时快晌午了,这里实在憋闷的很,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而且臭味熏天,刺入鼻孔,简直能让人昏厥,瞬间不可省事。他用手捂着嘴巴,一鼓作气,迈步朝着深处走去。
这里的房屋有很多,有大的也有小的,方方正正,布局迥异,但是看上去,主体结构还是保存的完整,没有遭到特别严重的自然破坏和人为的蓄意损坏。
正在这时,水影先生突然听见身后“咣当”了一声,一时吓的他身上打了个哆嗦,心里骂了一句,一定是有人来了!他连忙地环顾左右,看看四周有没有可以先藏身躲躲的地方,他一眼瞧见了在前面不远处的一间屋子,有一扇门正半开半掩着,他紧得倾下身子,三步并作两步,蹑手蹑脚地进了屋,一闪身,躲到门后去了,随手拿起身边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把自己的脚印轻轻地盖了起来。
水影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的听着,来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走的很轻快,嘴里还嘟囔道:“天天这么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真是不知道太师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个这么傻吃苶睡的女人,现在也好了,夫人小姐都知道了,太师又是特别惧内,对小姐也是百依百顺,我看他将来怎么给他们母女二人交代,唉,我也该想想后路了,太师这人阴险的很,也不知道那天我的小命就交给他了,唉,人跟人不一样啊,实在不行我就得远走高飞,早日离开这非之地,嗯,到时候再找个男人,生个娃子,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天天送,这送了多少天了,夫人还让我从她嘴里套出一些话来,你看这样的婆娘怎么套出个话来呀,一问三六九不懂,真是烦人,烦死了!”
一时间,水影听出一些门道来了,太师?夫人?小姐?看来安娜的失踪跟大国师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对,是跟老贼沙华曼珠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沙华曼珠为什么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把安娜弄到这里来,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套头秘密吗?还是沙华曼珠和奈都之间有什么过节,他奈何不了奈都,便从女人身上下手,若是这样的话,真是太卑鄙了!
看来要想弄懂他们心想的什么,只要听她的话便可知晓,正所谓要知心腹事,但听背后说。
这时,慧儿来到庙里最深处的那间屋子前,她突然停了下来,嘴里念念有词,只见那屋门自动打开了,慧儿一迈步走进了屋里。
慧儿一手拿着饭菜,看了看地上躺着的女人,说道:“起来啦,吃饭了。”
说着,慧儿一哈腰把倒在地上的木墩扶正了,看了她一眼,说道:“你还把木墩推倒了,脾气还挺 大,来,吃饭了,唉!”
只见那女人披头散发,头发一缕一缕的,盖住了她俊俏的脸,慧儿闻着都有一股臭味,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并捂住了嘴巴,说道:“我说你坐起来好不好,你不吃饭会饿死的。”
那女人可能听到了慧儿的说话声,右手在地上划拉了一下,脑袋稍微转动了一下,她睁开了眼,透过浓密的发间,望了慧儿一眼,仿佛她看到了什么似的,突然她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把抱住了慧儿的双腿,神经地说道:“雉儿,雉儿,是雉儿吗?雉儿,我是妈妈,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女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说完,她便把头埋在了慧儿的双腿间。与此同时,慧儿被吓得直往后退,想摆脱女人的束缚,可是女人紧紧的抱住她的双腿,使她动弹不得,于是慧儿惊慌地叫道:“起来,起来,你快起来呀,我不是雉儿,我不是雉儿。”可是女人的手没有松开,反而是愈加抱的紧了,仿佛钢钳一般,钳住了慧儿的身子,拔也拔不出,动也动不得,突然慧儿灵机一动,一笑叫道:“妈妈,我是雉儿,我是雉儿,你松开你的手,你弄疼我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