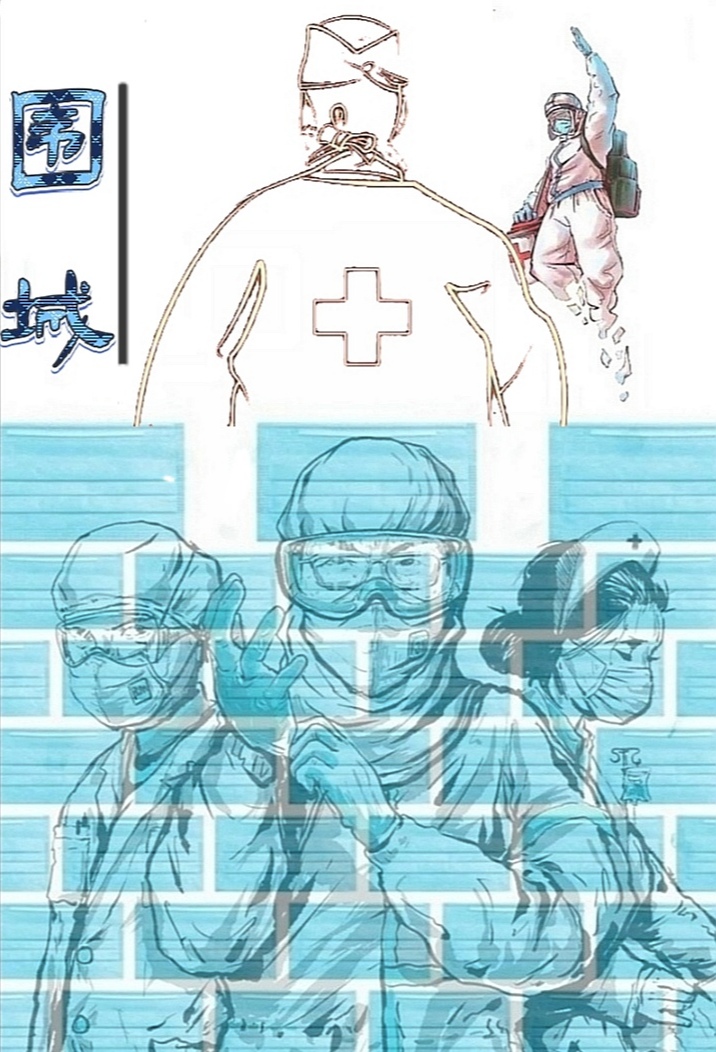直到轺车顶上的驭手马鞭挥动,车队缓缓启行,李玲儿才流下了分别的眼泪,紧紧握住孙旭东的手说道:“君武,得空时去杜记酒店看看,云姑还有东西要给你。”孙旭东听李玲儿突然提到云姑,知道李玲儿对她还是猜疑,尽管心中无鬼还是有些脸红。
看着一辆辆轺车消失在驰道的尽头,旷转头看了看孙旭东说道:“君武,我看了你画给吊的那些东西,真的有那么些用处?”
孙旭东还沉浸在和李玲儿分别的愁绪之中,闻言转头道:“嗯。司虞记得君武在田齐就说过的话么?铁制的兵器最终取代铜制兵器,其实不光是兵器,铁制的器具也比铜制、石制的好得多。”旷点点头笑笑说道:“光是靠器具之利大鑫还有不足,关键还是要靠人哪。唉,也不知道孙先生的水取得怎么样了。”
“司虞所说有理,人不行自然什么都干不成。我让南宫的轺车带了些火药送到林屏,孙先生用了当可加快开渠取水进度。司虞,方才玲儿让我去看看云姑,咱们一同前去吧。”云姑到杜城日子不少了,孙旭东既怕李玲儿误会,更怕云姑误会,是以一直都没去看看她,心中一念至此不觉对云姑更有歉意,不如拉了旷一起去看看,有些事最好还是和云姑当面说清。
这几日边境上已不见胡兵的身影,四乡赶往杜城的百姓每日益多,此时已近午时,到酒店用饭的人已来了不少,小杂役急忙到后院叫女掌柜茯芹。
自从那日李玲儿来过之后,云姑像是受了惊吓一般,一会儿哭一会笑地让人捉摸不定,将茯芹吓得不轻,以为她是每日被关在小店中烦闷所致,无事之时便会到她房中陪着她说话解闷。两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闲话,听见铺子里小杂役叫,伏芹笑着辞了出来,刚出门抬头便见两个男人进了后院,一怔之下才看清是身穿了便装的旷校尉和大将军,茯芹急忙要行礼,却被孙旭东一把扶住。
云姑的房门半开,坐在榻前的云姑听了孙旭东的声音一时竟然怔住,猛然站起身刚起步却又低着头缓缓坐下,直到茯芹领着两人进来,云姑这才站起身矜持地对二人点点头。
“云姑,大将军来看看你。”旷进屋后目不斜视,面无表情地沉声说道。孙旭东却四顾打量着云姑的‘绣房,’笑着问云姑道:“云姑,这地方你还住得惯么?”
云姑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白晳的脸庞涌上了些红晕,良久后才低声说道:“云姑是苦命女子,住在哪里都不劳大将军挂念。”说罢炫然欲涕。
旷和孙旭东看着眼前这位往日骄横的白国公主,一时都不竟语塞,稍顷过后孙旭东呵呵一笑道:“云姑,这段时日杜城军务繁杂,一直没能来看你,别往心里去。”
云姑听了抬头望了孙旭东一眼,眼神就像她脸上的表情一样,让人看不透,又看了旷校尉一眼迟疑片刻后才冷声说道:“只怕大将军不光是军务繁杂吧?大将军不来,是不是怕被云姑害了?”
云姑嗔怪的口气让孙旭东既感尴尬又感奇怪,却碍着旷在当面无从解释,只得嘿嘿笑着遮掩过去,旷校尉未经儿女之事,搞不清里面的名堂,心中只是暗自奇怪,怎么这两人一见了面儿就斗嘴?心中不由不耐烦,对孙旭东作了个眼色后大步出了房门。
旷出了房门,云姑像是暗出了一口气,脸色慢慢也比先前要缓和得多,搬动了一下锦墩示意孙旭东坐下。孙旭东原本约旷一起来,就是为了不让云姑加深误会,更想找着机会解释一番,此刻见旷走了不禁暗暗叫苦,却也只得坐了下来。
“君武哥,是玲儿姐不让你来吗?”房中只剩下二人,云姑脸上有表情更见缓和,轻叹一口气后柔声问道。
“这个。。不是,云姑你方才说怕你害我是什么意思?”孙旭东见云姑比往日更见消瘦,先前的红晕退出,白晳的皮肤竟一见一丝血色,心中很是有些愧疚,想好的话竟一时无法出口,便先问了一句。
“哼,我倒正想问问大将军呢,玲儿姐难道没跟你说?”
“哦,没有啊,她今天临走的时候还让我来看看你,这话是玲儿说的?”孙旭东忽然想到李玲儿肯定来过了,不然她怎么会知道云姑有东西要给自己。
“她走了?”云姑瞪大两眼问道,一副不相信的神情,孙旭东点头说道:“玲儿跟轺车队回田齐了,她来看过你了吧?她走时说你有东西要给我?”
云姑眼中闪过一丝惊疑后,突然从枕下取出一方白丝绢,正是李玲儿那日塞给她的那方丝绢,丝绢上依偎着两只灵动的鸳鸯,云姑呆看片刻后像是醒悟过来,一时间两脸通红地将那丝绢抓拢在手中,对孙旭东冷冷说道:“给你的东西已经让我毁了。大将军,我要歇息了,今后也请大将军不要再来了。”
孙旭东木然地望着云姑,心中实在搞不懂云姑怎么会突然翻脸,看着她用拒人千里的神情下了逐客令,也只得笑笑起身推开房门。
听着孙旭东远去的脚步,云姑打开了那方丝绢,用尖尖的指甲刺着那对鸳鸯的眼睛,狞声说道:“总有一日会让你们变成一对死鸳鸯。”
孙旭东出了杜记酒店,想着刚刚云姑的神情,虽然自己并不爱她,却有些失落的感觉,也不知李玲儿这鬼精灵到底跟她说过什么了,虽省得自己尴尬,却不免招致云姑的怨恨。他满怀心思地进了右锋营,就见旷的一名亲兵跑过来说道:“校尉大人正让小人去寻将军大人,太子营的侍卫来了,请将军大人即刻赶到中营,说是太子爷有要事相商。”
孙旭东急急换了服色,跟着伯齐的侍卫快马赶到中营。快步进了伯齐大帐,只见大帐中一人坐着正在和伯齐说话,见孙旭东进帐连忙收声。伯齐见孙旭东进帐,用手一指那人说道:“君武,这是咸城太叔公府中的内侍刘莆,刚刚从咸城赶来。”
那刘莆丢了手中的陶碗,起身对着孙旭东行了个礼,声音尖细地说道:“小人早闻破虏将军君武大名,今日终得相见,实是三生有幸。”孙旭东还了礼,见他一身尘土还未拂去,想必是一路赶路甚急,风尘仆仆此时刚赶到营中,便连着道了辛苦。
“君武,咸城中风声不妙,大王疑我犹深,伯齐太子之位堪忧哇。”伯齐已听了些刘莆的禀报,眉头紧锁干巴巴地说道:“君武将军是自己人,刘莆,你从头再说一遍吧。”
“是。”那刘莆答应一声,即将咸城近期之事从头细说一遍。
伯齐嘴中像里含了黄莲,满脸的烦躁,一边听着一边用手指甲去掐虎符上的獠牙。等刘莆尖着喉咙全部说完后,孙旭东和伯齐二人仿佛也感觉到了咸城中的暴风骤雨,两人不禁呆若木鸡,良久过后,伯齐一脸惨淡地长叹道:“君武,眼见着咱们便能收服胡人,不光能为大鑫靖了边患,还能得了一支生力军,却不料咱们后院起火,最终是为他人作嫁。”说罢摇头叹息。
朝堂里的事孙旭东知道得很少,眼见颇能沉得住气的伯齐此时已是沮丧不已,也深知大事不好,也不由跟着暗暗着急,要知自己相助的只能是伯齐,若是他做不了鑫王,自己的大事便也做不成,一时间面对纷繁杂乱、波谲云诡的朝局,孙旭东茫然不知所措,
“刘莆,太叔有什么打算?”伯齐嗟叹良久,皱眉问道。
刘莆看了一眼孙旭东,迟疑着却不说话,伯齐见状说道:“君武将军是本太子的心腹爱将,你但说不妨。”刘莆这才答应了一声,小声说道:“临来时太叔吩咐小人,让太子爷早作准备,万一大王百年之后有变,能相机行事。是以在此之前,无论朝堂如何召见,太子爷一定要坚守杜城,万不可轻回咸城。”
孙旭东立即听懂了话中之意:太叔公之意是万一老鑫王死后未能传位伯齐,伯齐便可将杜城之兵,起兵造反,武力夺取王位。孙旭东细思之下也只有如此,心下便有些赞同,正要出声附合,却见伯齐厉声喝道:“太叔公岂有此理?我伯齐就是隐居山林做一农夫,也不会做那大逆不道之事。此话休要再提了。”说罢气哼哼地拂袖而去,将孙旭东和刘莆两人丢在帐篷中**。
孙旭东一下午心神不宁,吃过晚饭后伯齐单人独骑到了破虏军营,只一个下午没见,孙旭东就见伯齐竟像是老了几岁,朝天冠下向来梳得一丝不乱的黑发都有些凌乱。两人进了孙旭东的大帐,伯齐摒退了孙旭东的亲兵后说道:“君武,下午若不是我见机得快,你此刻不定已人头落地。”
孙旭东大惊:“殿下何出此言?”
伯齐冷冷一笑:“下午那刘莆借太叔公之言,说要我相机行事,你是不是正要出声赞同?”
“标下确有此意。”孙旭东自己也在疑惑,那人说的本来就有道理。望着伯齐精光大盛的两眼孙旭东忽然警觉:“太子之意,莫非那刘莆是来试探的?”
伯齐冷笑一声道:“下午你真要说出来了,想来你此刻已人头落地。君武,大王虽发雷霆之怒,但知父莫若子,伯齐算死大王并无废我之心。可为什么大王要这么做我却琢磨不清,不过至少可看出咸城此时的情势确实令人担忧,我面前总像隔着一层雾,怎么看也看不通透,端的是危机四伏啊。”
孙旭东像是在作梦一般,下午伯齐在刘莆面前的作派原来是在演戏,自己却丝毫不知情。此时才领教了人心深似海,在这些人面前,自己实在是浅薄得可笑。他望了一眼两眼幽幽放光的伯齐,心中又是佩服又是心惊,看来伯齐忧虑的不是老鑫王变心,而时咸城中那股涌动的暗流。
“殿下远离都城消息不灵,依标下之见,咱们也须早作打算。要不,杜城的事交给标下,殿下请王召早回咸城?”
“不。堪不破咸城的情势,我绝不可轻回,这时候万事都要小心,一步差了便步步差。大王为什么要如此做呢?”伯齐背着两手,昂头踱步,嘴中念念有声。
帝王心术远非孙旭东能捉摸得透的,只是他心中忽然一亮,对伯齐说道:“太子殿下要是不怕辛苦,标下带殿下去见个人,应该可以分辨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