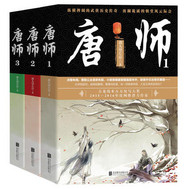荒原上的晚风已有了些暖意,让人颇觉惬意。旷野之中,黄灿灿的一弯弯月下,十几名大单于卫兵手按腰刀,分布成老大的环形,环形正中冒顿和金密弟拥着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相对而坐。
“那汉人军师说他和鑫国有不共戴天之仇,看来不假。”冒顿灌了一大口奶酒,望着眼前火堆上跳动的火焰说道:“投到咱们这儿来,大概就是想借着咱们胡人的力量替他自己报仇。”
金密弟点点头:“照着他们的说法,军师是看出了鑫国有与我们讲和之意,便矫了大单于的军令,派右贤王部灭了与大单于换俘的破虏军,以使两边仇怨更深、胡人失信,就很难讲和了。”
“他们是这样说的?”冒顿有些惊诧地问道。汉人军师城府深沉,令人高深莫测,属胡人最不喜欢的性格,但冒顿对他还是有些好感的,毕竟在冒顿最初登上汉位时,军师帮了他不少忙。但如果鑫人说的是真话,那么军师为一已之私而矫改军令,这可比当初冒顿疑他错传军令要严重得多。
金密弟的说法是孙旭东和伯齐为除去汉人军师而蓄意编造的,但却甚合情理,既然抓住了右贤部夜袭破虏军不是冒顿的本意的马脚,那么无论怎么解释都能说得过去,即便是当面对质,也可令军师百口莫辩,因为军师是汉人。
“本单于原以为他是误传军令,最多不过是为了抢回那队轺车,没想到此人心机如此之深,竟然能看到鑫人意欲与咱们讲和,把咱们当猴子耍了,只可惜右贤王至死都被蒙在了鼓里。”冒顿按着别人的思路想下去,自然就得出了别人想要的结论,不由一阵光火,将手中装奶酒的皮囊扔到了火堆中,稍顷过后,一股黑夜冒出,火堆四周都弥漫着一股焦臭味。
“大单于,那军师工于心计,心肠狠毒,不光是古尔塔的万人队,还有上回立不花的万人队不也是跟着他全军覆没的吗?”
“嗯,这是只草原上狐狸的狐狸,可恨竟让他逃了,不然定要点了这家伙的天灯。还有,卫兵在他帐篷里搜出了几封书信,掐指能算都是装神弄鬼地骗咱们的,全靠的杜城有人给他暗通消息,这种人月亮神迟早会收拾他的。”人只要被别人往坏处一想,就全无是处了。冒顿越想越恨,已将那军师恨到了极处,咬牙切齿地说道。
火堆中一声爆响,四下飞溅出一大丛火星,金密弟一边用手挡住一边说道:“从营地出草原将近两百里,他们不一定能逃出去,说不定半路上便喂了狼。大单于,鑫国太子的信上说的什么?”
冒顿不答却反问金密弟:“金密弟,你是我最信任的兄弟,你看这仗继续打下去,咱们能不能胜?”金密弟低着沉吟片刻,从腰中解下孙旭东送的弯刀,递给冒顿。冒顿迟疑伸手接过后问道:“怎么啦?”
“大单于请将里面的刀抽出来看看吧,这是标下临走时那猎狼勇士送给标下的。”
“哦?”冒顿闻言慢慢抽出弯刀,弯刀出鞘发出的清脆鸣金之声就让冒顿有些奇怪,眼见闪着红光的刀身一点点抽出,不由更是惊奇,直到弯刀全部出鞘,才发现刀身闪动的红光原来是反射的火光。
“这是什么东西打制的?好刀。”冒顿用手指感受了一下弯刀锋利的刃口,那种刀锋如同刮在砂地上的感觉比铜制弯刀要强烈得多:“这是那破虏将军的佩刀?”
“是,不过他说一月之后,鑫军兵士就可人手一把这样的弯刀。”金密弟从怀中掏出一把短刀,递给冒顿:“大单于可以试一下,汉人用的精铁比铜要硬得多,用力便可砍断铜刀而刃口不损。”
冒顿尽管相信金密弟的话,还是接过金密弟的短刀后,与用手中的弯刀相交,一声清脆的鸣金声后,果然短刀的刃口被弯刀砍出一个豁口,冒顿抬眼望了一眼金密弟:“这么说鑫军以后都是用这种兵器和咱们作战?”
金密弟点点头:“还有连弩和作雷响的火器。”火器这个词是毛怀告诉金密弟的。
“这可真是见鬼了,汉人怎么就能鼓捣出这些东西的?”
“咱们的骑射功夫比汉人好,但如今他们的骑甲也换下了长衣甲,轻动灵便并不逊于咱们胡人。他们还有连弩,万弩齐发便无所谓什么准头,尽可与咱们扯平。一连败了几仗,咱们士气已大不如前,鑫军则相反,士气正在兴头上。还有鑫军专门训了鸽子互通消息,也比咱们的斥候要快得多。大单于,情势似对咱们不利。”
左贤王性烈如火,心高气傲之人也说出如此沮丧的话来,冒顿方才还打算与伯齐再作一战的雄心不免淡了下来,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沉声喝道:“左贤王,怎么尽说为他人长威风的丧气话?传到军中岂不扰乱军心。”
“标下所说乃是实情,并非为汉人长威风。若不是大单于问标下,标下也不敢乱说。大单于真要与鑫人决一死战,标下自当奋力死战。”
“哼,这才像我胡人汉子说的话。”冒顿盯着金密弟足有移时,眯着眼睛说道:“杜城的鑫军自从有了那支破虏军后,确实是今非昔比,战力大增。不过,别忘了,四水城本单于还有三万铁骑和一万象兵,真要和汉人决一死战,输羸还不一定。只是,此刻让本单于最感顾虑的却是杜城中被俘的兄弟。”
自己还有一千手下被关在杜城,金密弟惭愧不已,低下头说道:“标下失职,还请大单于治罪。”
“不用了。”冒顿忽然叹了一口气,苦苦一笑后道:“真要治罪,我冒顿罪比你大,八万兄弟跟着我出了四水城,如今只剩六万人。真要这样就罢了刀兵,真让冒顿愧对单于之位。”
两人互望一眼,顿时陷入沉默。金密弟只想一年前,大单于冒顿亲率八万胡兵出四水城,将鑫军打得屁滚尿流,抢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回四水城,那时大单于是何等的风光。谁曾想一年之后,竟让他陷入进退两难之地。
“左王,你看那君武将军怎么样?”沉默中冒顿忽然问道。
“是条汉子。妈的,标下跟他摔跤,也不怎么弄的,这家伙玩儿似的将标下摔了七晕八素。”“哦?你们还摔了跤?”
“正是,那晚标下中了伏不服,那家伙便要跟标下单斗,标下又输了,后来便比摔跤,标下还是输了。只是那家伙喜欢摸鼻子,将标下摔下就伸手摸鼻子。呵呵”
“哈哈,没想到左贤王摔跤在草原上号称第一,从来都是你摔别人,总算是也有被人摔的日子。”冒顿哈哈一笑,心中的郁闷稍减。稍作沉吟后说道:“左王,伯齐信中答应只要咱们跟他们讲和,杜城被俘的弟兄全数放回不说,还会给我们些军粮和物资,不过,伯齐这人本单于却有些信他不过,这样,你派人先跟那破虏将军说,要他点头本单于才信。”
金密弟没想到冒顿感转变得如此之快,正在发怔时,就听一人脆生生地说道:“不用左王派人去,请大单于交给我就行了。”
****************************************************************************************************************
“来人,多取些钱来,重重赏他。”甘虹大声叫道,门外的跟随早已预备好了,托着一个放了五只小金锭的木托进了书房,正要交给一位缩头缩脑的王宫内侍时,两眼放光的甘虹说道:“少了少了,你带他再去取五锭。”那内侍大喜,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后,喜笑颜开地去了。
“世子爷,你们请出来吧。”书房和后房间的门帘一动,一位面如冠玉的年青公子走了出来,吴天明低着身在后面紧跟。那公子两条剑眉下一双大眼颇见精神,高挺的鼻梁一张棱角分明的海口极富男性特征,他进了书房后掩饰不住满脸的笑意:“果然不出臣相所料,父王不光是将伯齐手下抓了,连狐推都给抓了,看看谁还敢提变法二字。”
“世子爷说得是,不过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依老夫看,这时候,世子爷真该多多去伺候大王,以博大王的欢心。不要每日里东游西逛,传到大王耳中,对世子爷有轻慢之心。”
伯牙微微一笑,极其潇洒地一挥手说道:“这个本世子自然知道,就是每天进宫都被大王训得狗血淋头,才出来散散心的,找些乐子,要不这日子过得也太气闷了些。”
“天明,你看如何?”甘虹心中暗骂了一句绣花枕头,转头问一直在低头沉思的吴天明道。
吴天明一直未说话,见问才沉吟着说道:“大王一向对来投的名士以礼相待,即便是浪得虚名的假名士至多是打发他们走人。为何此番会发雷霆之怒,将狐推下狱?”
“狐推不光是浪得虚名,还是一个狂妄小人,竟敢在朝堂公然和大王顶嘴,不抓他抓谁?”伯牙冷笑一声,不屑一顾地说道:“吴舍人多虑了。”
甘虹却被吴天明的话搅得有些忐忑,按理老鑫王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刻薄人,顶几句嘴便会将人下狱,他皱眉沉思后说道:“嗯。天明所说也不无道理。不过,依老夫看,伯齐身为太子,当初要行变法之策都被大王痛斥,狐推是个外臣,公然在我大鑫朝堂叫嚣变法,乱我国政,才致大王发怒,自己身陷圄囹。你说呢,天明。”
“老臣相,大王的心思让人越来越难捉摸了。不过,或许大王久病之人,心火旺盛,行事偏激些也未可知。”吴天明显然对甘虹的分析不太感冒,自己却又拿不出更合理的解释,阴着眼答道。
伯牙对猜别人的心思一点兴趣也无,不耐地看了二人一眼后说道:“我看你们都入了魔道地疑神疑鬼。甘相,太仆大人可还在府中等着你哪。” 伯牙对着甘虹嘿嘿一笑,露出一嘴雪白的牙。
尽管甘虹已将狐姬竭力丢到了脑后,但当他独自坐在轺车上,心中却仍然不时闪过伯牙趴在狐姬粉嫩的屁股上,挥汗如雨地肆意挞伐,甘虹只觉自己整个人被丢到了醋缸子里,禁不住紧紧皱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