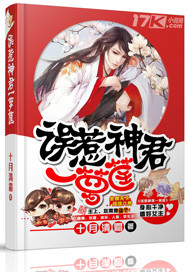勤奋好学而又温文尔雅的咥运,不但很讨李治的欢心喜悦,而且,还加快了一统西域的美梦。
见咥运学业有成,处事干练,又对朝廷忠心不二,就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依然决定,放咥运回西域,协助贺鲁理政,归还山南诸国,扫平山北草原,令大唐势力席卷整个天山南北。
然而,涉世未深的李治,万万没有想到,狼是要吃人的,哪怕你圈养了很久,也改变不了它与生俱来的野性。
自从踌躇满志的咥运,满载朝廷的赏赐厚礼,携带爱妻和一双儿女,及随行的五百卫士,扬起漫漫黄沙,浩浩荡荡弛出嘉峪关的那一刻起,一场空前灾难,便已经悬在了西域的上空。
咥运的到来,和新增一双儿女的喜悦,让贺鲁和龟兹王这个名副其实的“亲家”,欢心喜悦得不能自己。
贪欲好色的桑吉,深知这位文弱哥哥的习性,望着荷花般美丽的女人,能共享的他,也只能是垂涎三尺,无福享受。
忍耐再三,还是借逗玩怀中幼儿之际,将熊掌般的大手,悄然从女人高耸的酥胸划过,竟惹得女人潮红漫花,秋波闪闪。
欢宴结束,眷属散去,只剩贺鲁父子的大厅,显出了短暂的沉默。
贺鲁沉思般地喝下一口奶茶,目光迟疑地瞅着咥运道:“这么以来,岂不是彻底和朝廷闹翻了脸?”
咥运淡淡笑道:“天下是长生天的天下,又不是他李家的天下,您坐镇山南诸国,桑吉回军西进,我来拔掉可汗浮图城和高昌这两个钉子,整个天山南北就是您的王国,到时候,建牙帐自称可汗,谁又能把您咋样?”
一番轻描淡写,但却如巨石落海般的话语,像是彻底点燃了贺鲁心中的欲火,大手一拍,笑声如雷,嚷道:“我早就想有属于自己的天下!”
欢喜兴奋一番,桑吉若有所思道:“会不会牵连到雪狼师父?”
贺鲁不以为然道:“我已经给他说了,他以后就是我们的名义可汗,这人对我们有恩,是草原的福星。”
桑吉微微摇头,嘟囔般道:“怕是没那么容易,师父那人认死理,造反的事他肯定不干。”
见贺鲁脸上显出了难色,咥运“呵呵”笑道:“自古成就大事者,均不计小节,他来固然好,他若不来,我们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总不能因为有羊产羔,就耽误了转场。”
同样的贪欲野心,让父子三人一拍即合,于是,咥运便手持贺鲁兵符,自天山中断一路向东,调集了上万人马,陆续汇集到可汗浮图城周边的部落。
这便有了山北之变。
赶走了裴显,咥运又乘胜追击,挥军过山,不到几日功夫,便攻下高昌周边几座小城,切断交通,将王城围得水泄不通。
这个饱学了中原文化,和兵法战策的狼崽,用老师教会的本领,再反过来对付老师,并将它发挥得淋漓至尽,以至于让久经沙场的骆弘义和裴显,都节节败退,束手无策。
只好一面坚守王城,一面飞马上报朝廷发兵驰援。
敬轩虽说常去贺鲁毡房,但与咥运却很少见面,只知道贺鲁有个不爱舞刀弄枪的儿子,但却没想到这家伙深藏不露,是个有智谋的主。
于是,就打消了先带人赶往高昌的想法,打算通过贺鲁来解决高昌之围。
怎奈,近来的贺鲁行踪不定,派几个点上的人去落实送信,全都扑空,不是说没来过就是刚刚走。
就敬轩四通八达的信息网,几经折腾,都没能见到贺鲁的面。
于是,敬轩脑海里渐渐浮出一个可怕的念头:父子同谋,野狼在有意躲避着自己。
若果真是这样,那他去找贺鲁或是前往高昌劝说罢兵都全无意义,看来,他一直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于是,他叫来鹏飞,对驼队以及庄里事物又作了一番详细安排。
尤其嘱咐一旦唐庄和自己有变,让他一定阻拦江湖朋友,千万不能贸然出手相救,只要四方不动,他自然不会有事。
见贺鲁迟迟躲着不肯露面,敬轩只好连发五道急信给贺鲁,内容只有一句话:“千万别救我!”
翌日的太阳刚刚染红了树梢,就见小的慌慌张张来报:“有大队官兵朝庄上开来。”
敬轩淡淡一笑,拎起事先准备好的包袱,便和三妹出了院门。
足有千人的官兵,刚过庄前的小树林,就兵分两路,朝唐庄包抄了过去。
只见蔡文泰一马当先,身后是百人护卫,威风凛凛的冲了过来。
见敬轩面色平静的立在门首,蔡文泰小人得志般的咧嘴笑道:“有人告你伙同贺鲁谋反,私自募兵,朝廷下旨,封庄拿人,听后发落!”
敬轩淡淡道:“事情总会水落石出,拿人可以,但我有两点要求。”
见蔡文泰微微额首,敬轩从容道:“一,老太太年迈,你不能动她;二,唐庄产权本不归我,你也无权查封。”
蔡文泰刚要急着说啥,就见鹏飞迈着四方步,像个大财主般的晃悠出来,佯装猛然发现似的,赶忙冲蔡文泰躬身行礼道:“草民董鹏飞见过守护大人。”
礼毕又面色狐疑道:“大人这是......”
蔡文泰也没咋理他,扭头冲敬轩狐疑道:“你说唐庄产权不归你,那是归谁?”
未等敬轩开口,鹏飞就谄笑道:“是小人的薄产。”说着,又冲院里喊道:“董宏!把咱家房契拿来!”
董宏应声飞奔而来,手里捧个红木匣,愣头愣脑杵给鹏飞,嘴里还低声嘟囔道:“十来年都没动过,咋就想起了它。”
鹏飞慢慢打开尘封已久的木匣,从中取出两张泛黄的纸张,恭恭敬敬递到蔡文泰手里,满脸谄笑道:“请大人过目。”
蔡文泰满脸狐疑的展开一看,确是前任签办的契约,房屋院落都一清二楚,并无差错,便倪眼瞅着鹏飞,冷声道:“你哪来这些钱?”
鹏飞“嘻嘻”笑道:“家父在阿尔泰山弄金子,发了点小财,正赶上敬轩兄想盖个庄子走驼队,家父就将钱全部投在了这里。”
蔡文泰嘟囔般道:“原来是个空架子。”
说着,把脸一沉,冲敬轩道:“老太太必须带走!听说,她当年就和薛举不清不楚的,朝廷可是点名要整治她!”
敬轩刚要发怒,就见陪伴老太太的婆子连哭带叫道:“老爷!老太太坐化了!”
敬轩听说,手中的包袱不由落在了地上,刚要扭身朝院内冲,就见蔡文泰带人跟了过来。
于是,驻足沉声道:“家母升天,我必须尽孝,三日后我自去衙门,任凭发落。”
话音才落,就见蔡文泰面显不屑,朝手下挥手嚷道:“别听他咧咧,先绑起来再说!”
军士中有知道敬轩能耐的,也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识相的,脚步稍缓,二杆子便蜂拥而上。
只见敬轩旋风般掠过,还未等来人明白,十几杆长枪,便像疾风扫落叶般飘落地上,霎时间,蔡文泰的身旁,便只剩几个呆若木鸡的属下。
敬轩手指惊慌失措的蔡文泰,愤然道:“我‘天山雪狼’向来一言九鼎,快快撤走你的人马,免得伤及无辜!”
蔡文泰见兵士们都暗暗退缩,自己的两腿也在不由得哆嗦,便冲敬轩讪讪笑道:“君命难违,我也是逼不得已,下官敬佩您的为人,那咱三日后府衙再见。”
见蔡文泰带人离去,敬轩慌忙冲到佛堂,见老太太身穿海青,手挂念珠,双眼微闭,面容安详的盘坐在蒲团上,若不是唇手长时不动,也无呼吸,就像睡着了一般。
敬轩立刻跪倒磕了三个响头,挥手让几个哭哭啼啼的婆子出门。
这时,庄里的闲人也陆续赶来,敬轩站立台阶,声音低沉道:“老人家走相很好,已升佛国,大家应该感到欣慰高兴才是,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再哭,有心的,在佛堂前轮流念佛,无意者,可远离此地,不得喧哗走动。”
结果,来者自发列队念佛,随着人数不断增多,声声佛号,如学堂诵文,渐渐弥漫了整个唐庄,飘向远处。
老太太本就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加之敬轩在当地的威望和恩泽,消息一旦传出,便很快惊动了乡邻四舍,前来吊唁的人流络绎不绝,最终都加入到了念佛的行列。
逐渐增多的人群,渐渐漫出了院门,佛号声悠扬飘荡,宛若置身于佛寺一般。
老村长闻讯赶来,拉住敬轩的手,恳切道:“老菩萨仙逝,是我等大事,有啥需求,请国公尽管吩咐。”
敬轩冲老者躬身行礼道:“家母生前所愿,要将骨灰撒到自己的故乡山北草原,我还正在寻思这坟地可如何安置。”
老村长轻捋胡须,若有所思道:“往常当兵人家,若有亲人尸骨不还,就将这人生前的衣物或是用具装棺入殓,称为衣冠冢,老菩萨是不是也......”
敬轩欣慰道:“老爹见多识广,这方面的事我不大懂,还要劳烦您来张罗。”
正说着,只听引馨声脆,佛号悠扬,一队出家僧人,似蠕动的长龙般,缓缓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