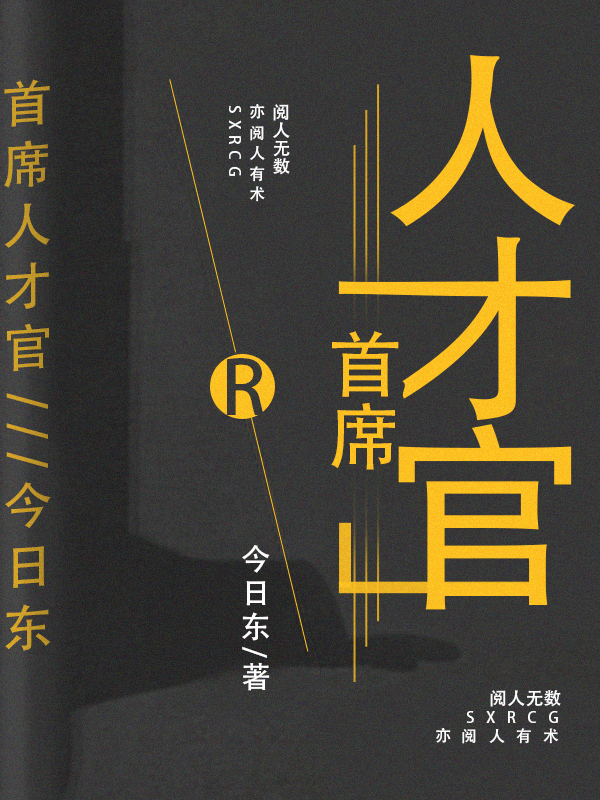花泣打算回到前堂去,听听他们还在说什么,刚打开房门,头就一阵抽痛。
头痛已经有一阵子没发作了,不知怎的如今就突然痛了起来,花泣痛的站不稳身子晃了一下,幸好两手抓住了门,不然可能跌坐下去。
用力的闭上了眼,靠在门上,拿手敲着头,张嘴想喊,喉咙发紧感觉提不上气来,好一会儿才喊出了声:“天玥!”
天玥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连忙上前扶着,花泣摆了摆手,自己坐回了椅上,头上已经冒出了汗,把头靠在椅背,痛苦的闭着双眼,眉头紧皱,半柱香功夫过去才感觉慢慢缓下来,还是有些痛,只是不会如方才那般抽痛了。
“天玥,去厨房看看,大人的药放哪里,去煎。”花泣喘着气,好不容易说出话来。
“是!”天玥立马跑了出去。
很快就又跑回来,急道:“姐姐,没有药,我去问问大人放哪里?”
“不要去,他不得空,别告诉他我头痛,免得他分心,你出去抓。”花泣忍着头痛,起身至书案前,写了几味药给天玥。
天玥拿起方子,急急忙忙的从后门出去街上抓药。
随后很快又回来了,是从前头进来的,花泣疲惫着双眼看见天玥,喊了声:“可是没带银子?”
“不是,姐姐您再忍耐一会儿,有药了,我马上去煎。”天玥说完就跑去了后厨。
花泣也不管她,又闭上了眼睛,感觉人脱力了一般,这头痛,时而发作时而好转,连她都琢磨不透,也不知是不是刚才着急上火,想那监察使的事,伤脑筋伤的痛。
子俞这次恐怕真的危险了,都怪自己,当初只知道诡辩,偷换概念说服子俞不要上报清水亭那事,压根就没想过万一事发,会带来什么后果,或者那时候她根本就不去想会不会有后果,总之,如今子俞被她带进了沟里。
她简直就是来坑害子俞的,而不是辅佐他上位。
也不知叶闰卿是不是瞎了,居然还说她有心计有谋略,有个鬼谋略!
一动脑筋,头又痛了,花泣只能强迫自己不去想,先静一静,或许这样才能好好的思考问题,如今是越急越乱。
天玥端着药碗进来,将碗放至桌上,拿着扇子对着碗扇风。
扇了许久,天玥才将药碗端至花泣跟前,花泣习惯捏着鼻子,一口吞完,好苦,感觉这药比平时子俞煎的苦上许多,子俞不在,又没有烧糖块给她,吞完药汤气就反上来,差点让她吐出来。
“这药怎的和子俞的不像?哪来的?”花泣刚才就觉得怪异,天玥去抓药这么快回来,就是飞去的,也应该没到铺子才对。
“是衙役大哥给的。”天玥见花泣苦的直犯恶心,连忙端了清水来给她漱口。
“衙役?随便谁拿包药你就煎给我喝?”花泣顿时愣住,难怪觉得药味和子俞煎的不同。
“不,姐姐,在宥文哥房里拿的。”天玥又道。
“到底哪里来的?一会儿衙役,一会儿宥文,宥文都走了,他房里怎会有药?”花泣把喝水的碗往桌上一放,直直盯着天玥。
“是前头门房衙役大哥说,在宥文哥房里有药......”天玥被花泣严肃的神情吓了一跳。
“去把他叫进来!”花泣有气无力道。
门房狗子进来,天玥就被花泣打发出去,花泣打起精神仔细看了几眼狗子,满眼的疑惑:“你什么时候来的县衙?”
“回姑娘,去年冬日就来了,我爹是原来的门房。”狗子不卑不亢,朝花泣躬身。
“你,和宥文很熟么?”花泣盯着狗子。
“不是太熟,就是宥文哥走的时候,交代了小的,他的房里还有药。”狗子回的很仔细。
“是他派你来的么?”花泣眼里满是机警。
“姑娘说的是?宥文哥只是交代小的多照看着姑娘!”狗子低着头拱手,不敢抬起来。
“不是说宥文,我问你是不是他派你来的!”花泣盯着狗子不放。
“姑娘指的是?小的不明白!”狗子这才抬起头。
“你不是门房老头的儿子,他儿子我见过!”花泣眼神收紧,她没见过门房老头的儿子,只是想诈一诈。
“这......”狗子突然不敢回话,怕越说越错。
“他在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回来?你给我说实话!不然我马上将你赶出县衙!”果然,此“狗子”非彼狗子,难怪她刚才觉得药汤的味道如同秦书玉煎出来的一样。
狗子转头朝外面看了看,觉着没人,才紧张的近前小声道:“姑娘莫要着急,大公子如今人在帝都,小的也不知大公子何时能回来,若是有信,也是传给杜大哥和秦大哥。”狗子如实说道。
“他还是不信我!人都安插到我县衙来了!你,当门房可以,好好当你的门房,不要插手我的事情,把嘴巴给我闭紧了,听懂了么?”花泣感觉自己头又痛了,大约是想的事情太多,太累,药喝下去还没能起效。
“小的明白,请姑娘放心。”狗子又一拱手。
“别急着走,我问你,都有谁,别告诉我就你一个!”花泣已然满眼戒备,她生怕叶青林插手她的事,到时弄的一团糟。
“没有了,就小的一个,是秦大哥让我来的,不是大公子。”狗子打死不敢再说实话。
“哦!我说呢!你退下吧!”花泣的心这才稍稍安下来,不是叶青林,那就好,说明他还是相信她,这人只是她哥秦书玉派来照看她的,这就对了!
叶青林,他到底在帝都如何了?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去年冬日至今,已然半年过去,难道宝儿至今未曾找到?或者又去了别的什么地方去找了?
如今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秦书玉和杜鉴在两川口,宥文跑了,这个刚刚揪出来的门房狗子也不知道,他只是个小喽啰,还有谁能联系上叶青林?
似乎真的没有人,她很担心,也很想他!
头还在隐隐的痛,花泣只好去榻上躺下闭目养神,子俞进来了。
他面色有些苍白无力。
花泣忍着头痛起身:“子俞,如何?”
子俞叹了口气,摇摇头,勉强挤出笑意:“吟儿,天玥说你头痛又发作了?如今觉得如何?药煎了么?我去煎,你等着。”
子俞说着就要转身出去给她煎药,花泣连忙叫住了他。
这个子俞,自己顶着大事,还不忘回来照顾她,花泣眼泪顷刻就出来了,有那么一闪而过的瞬间,她突然感觉很害怕失去子俞,若子俞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以后的事她都不敢往下想。
“我已经喝过药了,是宥文以前抓好的,子俞,你坐下。”花泣从榻上起来,头还痛着,眼里只有心疼。
“喝了?那你吃块糖。”子俞不知从那里变出来一包烧糖块,给了她一颗。
“子俞,是我错了!”花泣说话就抽着鼻子,她错了,她真的觉得是自己错了,为了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私心,颠倒黑白虽说不上,她用歪曲迷惑的方式,竭力说服子俞不上奏那是事实。
“傻吟儿,说这个做什么!这事不赖你,是我这个为官者没有主见,本该我来担当。”子俞依旧笑笑,似乎他对这等大事丝毫不在意。
花泣知道他是在安慰她,担当?如何担当?去担当了那就是杀头!
“三位监察使都走了么?住哪?”
“两位监察使,还有一位是郡守,我的顶头上官,住在驿馆,这几日会对我进行调查,子俞暂时不能离开这个县衙了!等到结果出来......”子俞轻轻叹着气。
“子俞,是我害了你!”花泣崩溃了,上前一把抱住了子俞的腰,埋头在他胸膛里痛哭,她好怕好怕。
“傻吟儿,别怕,子俞没有做亏心事,要相信监察使会给子俞一个公正!”子俞拍着花泣的背,忙着安抚。
哭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花泣居然感觉头都不痛了。
夜里二更之时,县衙后门鬼鬼祟祟摸出了两个人,是花泣和天玥。
两人一路快跑着去了驿馆,她等子俞回房了才敢偷溜出来,想去驿馆找监察使给他们塞银子,看看能不能通融。
从驿馆后院摸索着上了楼,不知道监察使住在那间房,天玥拉住一个路过的驿卒,给了他一两银子,问监察使住哪里,驿卒收下银子便给她们指了路,随后又小声补充道:“监察使大人傍晚在风满楼吃饭,至今还没回来。”
花泣一心要找人,没发现天玥和驿卒相互使着眼色。
驿卒是自己人。
若不是知道天玥,区区一两银子哪能让驿卒开口,驿馆可不是寻常的客栈,驿卒都两眼朝天,嘴巴都紧的很。
两人来到监察使的房门口,打算找个地方等着,就见三个人上楼来了,那三人,就是今日在县衙里见到的两位监察使和子俞说的郡守。
花泣和天玥连忙装作路过交谈,漫不经心的停在离监察使房门很近的地方,等他们走近,就竖起耳朵听他们在说什么。
“听说卫公子今日会到川口县,也不知到了没有,我等稍后去问问,一定要去拜会!”是今日坐在县衙主位的上官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