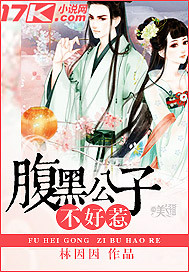天气从春风温润开始进入初夏清爽,水稻在初春种下,形似杂草的秧苗很快绿满山坡,再细细长长的窜出来,经骄阳雨露滋润,才抽穗开出稻花,看着满山随风摆动的稻花,花泣心里一阵阵的欢喜,再有一个月,到六月中,这一年两季的稻谷,上季就能成熟,那时便是收割的时候了,等收割完上季,又要犁田马上接着种下季。
这是她到川口县一年来的心血,也是她所有的希望。
“子俞,快来帮帮我!”花泣爬在坡度微陡的一片灌木丛中,脑袋钻了出来,盘好的乌发早被枝杈勾的蓬乱松散。
“吟儿,你小心些,你,你如何能爬上那去?”子俞暗道一个不留神,这吟儿就溜了,急忙从下头的田边攀上去。
花泣没话说,灌木丛高过她的个子,脑袋缩了回去,就只听见砍树的响动,子俞颠簸攀爬着也钻了进去,花泣才把手里握着刚砍下来拇指粗的树杈拖过去给他,抹了把汗:“来,你把这些拖出去外面,小心点,别把叶子全拖掉了,一会儿再回来拖。”
“你砍那么多?这小树也不能当柴火,要来做什么?”子俞拖着那一堆树杈,当真费力,很多还是被其它的野藤缠绕着,得花力气才能拖出来,而且......吟儿说不能拖掉叶子,可等小树和野藤分离,已经掉的七七八八。
子俞来来回回的拖了好几趟,花泣才停了下来,她也拖了一堆出来。
“看你,满头大汗,哎,这都刮破了,你这丫头,不觉得疼吗?”子俞心疼的拿起花泣的手,她的手背上被枝杈刮伤了好几道口子。
“没事,喊两个衙役把这里小树枝捆好,带回去,就放到城郊,之前放牛的那处地方。”花泣笑笑,抽回了自己的手,忙着整理那一大堆小树杈。
忙活了半日,又马不停蹄的赶回城郊,那片被牛啃的光秃秃的山坡下。
子俞走近了小河边,才发现,不知何时,这里开垦出了几分地,感觉和乡下的水田很不一样,因为这块地里的土是新铺上去的,而且,全是黄土。
“你们几个,来帮忙把这树枝剪下来,不要嫩的,就剪嫩枝下面稍老些的连梗三寸余长,要带两三片新叶,听好,是新叶,不是嫩叶也不是老叶,就是今年春雨那时长出来的叶子,不是去年的,也不是如今夏暑刚发的嫩叶,明白?”花泣卷起两手的衣袖,连裤腿都卷起老高,踩在泥里,指挥着几个衙役帮忙剪树枝。
“吟儿,这些要来做什么?”子俞也听着吩咐,想来帮忙。
“山茶树,摘不到山茶籽,只能剪枝插苗。”花泣手里不停,边忙边应着。
花泣早打算上山找茶树摘山茶籽,但不是那么好找,可能翻几座山也找不到多少棵,茶籽就更少了,还要逮着时候才有,她没有多少空余时间去翻山越岭的找,就想到剪下树枝插苗,如今插下去,可能还要等来年才能种。
这地里的都是黄土,特意去别的地方挖来填在此处,就为了插下去的树枝能在新土中长出根系存活下来,是她的父亲花长亭教给她的方法,茶树质硬,耐存活,只要剪的恰到好处,再用斋土,也就是如同黄土这类的泥土培育,就可以用树枝栽出茶苗来。
只因为那时候百姓都还吃不饱饭,也没人去种什么茶树,但如今不同了,乡下百姓有良田土地,就有粮食吃,光吃饱不行,还得考虑让他们也种一些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改善贫困,等来年这些茶苗种下去,无须如何打理,过个两三年,就能采收,卖给富贵人家换银子。
“吟儿竟懂这些东西,子俞都等不及想喝自己种的茶了!”子俞任由花泣胡闹,她总是喜欢做些标新立异的东西,陪着她闹,还时时夸赞着,只要她开心便好。
忙活了几日,终于把那些剪下来的茶树枝给插了下去,上面还插满了篦箕草,匍匐枝叶用于遮挡日头暴晒,让底下的茶枝在没有长出根系之前,能起到保护作用。
“如此它就能长新芽来?”子俞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书得的多,但多数都是仁义礼智,对这些实用的东西倒是了解的甚少。
“行了,每日要记得遣人来浇水,等到来年春日,应该能长到一尺来高,就可以种了!”花泣搓着手掌,满手的黄泥屑掉下来。
两人正打算进城回县衙,远处一衙役骑着快马奔到跟前,来不及下马就对着子俞喊道:“大人,快回县衙,朝中来人了!”
“朝中?快,马给本官,你随后护送花姑娘回城。”子俞连忙牵过衙役的马,跨跃上去,低头对花泣道了声:“吟儿你慢些走,别急,注意安全,我先回去。”
见花泣点头,子俞才掉转马头,绝尘飞去。
朝中来人?
花泣心里一阵激动,难道是川口县垦荒能让百姓有饭吃的事迹,已经传扬到了帝都?皇上这是来嘉奖子俞?是不是得升官了?
想到这里,满脸难掩的喜出望外,左右看了看,对衙役道:“没马了?”
“没了?”衙役两手一摊。
“我和大人来的时候那马车呢?还没回来?”花泣焦急地朝远处大路上望了望。
“没回,车夫大约以为姑娘和大人要到日头下山才回城。”衙役赶紧摇头。
“让那几个不用忙活了,这就收拾一下,走回去!”花泣一指身后那些忙前忙后伺候茶苗的衙役。
这个子俞,也不带上她,自己骑马跑了,害她如今在这里一边焦急一边激动,这朝中来人可是大事,她可比子俞在意的紧。
快步走了半个多时辰,花泣才被衙役护着回了县衙,顾不上满身泥浆两脚酸痛,直奔前堂,到了堂前的院子里,看见一队的面生侍卫,觉得不妥,从侧门溜回了后宅,梳洗一番换了干净衣裙,这才叫天玥给准备茶水,她亲自端去了前堂。
堂上官位坐着一位看起来来头就不小的官员,下首还有两人,应该也是某位要职官员,子俞端坐在一边和几位细声交谈着。
端着茶过去,几位官员面前已有茶碗,花泣先给主位大人物续上,再给下首的两位续,最后才到子俞,斟完了茶水,就站到一旁,犹如丫鬟一般听后差遣,不知道的还真会以为是丫鬟。
花泣竖起耳朵听他们谈话。
“此事,本官不会偏听一面之词,请叶大人今夜把事情发生详情拟出奏报,待本官调查清楚,自会带回帝都,请皇上定夺!”上首的大人物开口说道。
什么?一面之词?请皇上定夺?不是来颁旨嘉奖的么?怎么听这口气,似乎是来问罪的?
再一看身旁不远处的子俞,面色沉沉,却又不得不被迫带着微笑,连连点头附和。
平元五十年五月,在川口县就任近一年从七品县令的叶寒林,迎来了朝中派遣的监察使,不是来看他的政绩,而是他在朝中遭人弹劾,道去年冬季实施垦荒,清水亭死了十几个百姓未曾上报,隐瞒事实,有徇私舞弊之嫌。
监察使便是来调查核实的。
花泣到此时才明白,今日不是颁旨嘉奖,而真的是问罪。
顿时从满怀激动变的心慌肉跳。
当初这事,子俞坚持要上报朝廷,而她全力阻止,她没想到,这才约莫半年光景,朝中就知道了,不是说,朝廷任由川口县自生自灭的么?这是什么情况?
且不谈朝中是否还关心川口县的死活,现在是追究清水亭大火烧死人县令子俞隐瞒不报的事,这事说的小点,是理政失误,往大了说,那是欺君,欺君什么罪?轻则杀头,重则诛九族!
花泣神思之中忽地抖了一下,幸好没人往她身上看,骤然回神,连忙小心退到了侧门,回了后院。
没法冷静下来,这是重罪!
当初她确实没想到这一层,只以为朝中不会理会川口县的琐碎之事,等她和子俞把川口县民生搞好了,搞大了,只传颂功德去朝中领赏,那些明面不能提的事,久了自然就不了了之,没有人会去再翻那些老账,可她低估了朝廷对川口县的关注。
回屋关上了房门,在屋里来回踱步,心急火燎。
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便是年前城里收税一事,子俞动作强硬,让那些财主硬着头皮割血,缴纳了一整年的营业税,如今朝中突然关注起川口县,指不定就是那些财主背后的大人物怒了,找了个理由弹劾子俞。
还有垦荒,让百姓有了田地,那些山下良田的主人却没了佃农,硬是拖延了春耕,这损失,大约也算到了子俞身上,难保那些地主背后的主子不怀恨在心。
这下麻烦了,子俞危险。
花泣使劲喘了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回想刚才听那上官的语气,也没有多生硬,说出来的话也很中肯,估摸着这几位监察使理应是清廉公正的官员,不然也不能受皇上如此信任,当上监察使。
若是这样,只能从监察使身上找找转圜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