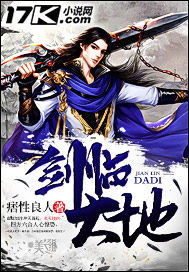慕容恪驰骋在官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勒马不前。
苏玉也停了下来,驱马来到慕容恪身边:“王爷,怎么了?”
慕容恪回望来时的路,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什么,走吧,驾!”
……
叶澜儿返回云鹤山之后,大病一场。
一连几日发着高烧,胡言乱语。
玉飞鸢从她的呓语当中,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澜儿,你这是何苦?既然心悦与他,便去找他。他既然已经不在江西,便一定是返回了京城。即使现在不再京城,早晚也是要回到睿王府。何愁找不到他?”
叶澜儿虚弱地摇头:“姐姐,你不懂。在我心中,这次去寻他,如同一个赌注。赌的是天意。
原本我以为,既然上天能够让我强行催发寻人术找到他的存在,便是有意成全我。可是,后来我们生生错过,这又何尝不是老天给我的一个暗示?”
玉飞鸢轻笑着叹了口气:“澜儿,你说的这些话,自己信吗?”
叶澜儿抿着嘴,不说话。
“傻孩子,你何苦自欺欺人。你是因为胆怯了,不自信了,所以才变出这些所谓的宿命来麻痹自己,想让自己接受这种结果是不是?
哪有这么多的老天的暗示,上天的安排?
这次的事情,不过是不凑巧而已。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不要管他什么王权富贵,管他什么情人蛊毒,你要去争取!
你怎么就那么断定慕容恪会在意你的身份,在意你身上的蛊毒?你怎么就不能大胆地去想一想,或许,慕容恪会为了你一辈子守着你清心寡欲呢?”
叶澜儿听玉飞鸢这么说,噗嗤一下笑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男子?”
玉飞鸢:“你怎么就知道没有呢?”
说到这里,她自己笑了:“我知道,其实这些道理,你都懂。很多时候,你比我都要懂。只是需要另外一个人替你说出来罢了。
好了澜儿,振作起来,好好养好病,然后去京城,找慕容恪!”
叶澜儿笑了一下:“不,我们还是先去西夷。姐姐你也说了,睿王府就在那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是我的,他跑不了的!”
玉飞鸢有些欣慰地笑了,她伸手摸了摸叶澜儿的头:“澜儿,谢谢你。”
“姐姐们!你们要不要这么肉麻?不过是生个病而已嘛,来,澜儿姐姐,快点把你的药喝了!”
天儿端着一大碗的苦汤药,递到了叶澜儿嘴边。
自从毛先祖去了之后,天儿就不在梳原本那种丸子发型,改成了普通小男孩的装扮。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型改变的原因,他突然就显得不那么团子了,隐隐有了一种少年感。
并且,更加显著的一个转变是,连他说话的方式语气都不再是之前的萌萌哒,而变得有些老成起来。
叶澜儿甚至怀疑,之前的天儿,不过是为了讨好毛先祖而装出来的天儿,现在的天儿才是本来的他自己。
如果真的是那样,可真是为难这个孩子了,竟然能够费尽心思去讨亲人的欢喜。
叶澜儿闭着眼睛咕咚咕咚将汤药全喝了下去。
天儿接过空碗,摇摇头:“姐姐,你都这么大人了,喝药怎么跟上刑一样?爷爷可是拜托你照顾我的,可别到时候我得天天照顾你。坚强一点,成熟一点吧!”
说罢,他端着空碗,步履铿锵地走了出去。
叶澜儿目瞪狗呆:“哎,这孩子……姐姐,这孩子是不是吃了什么毒药转性了?竟然开始教训起我来了?”
玉飞鸢忍俊不禁:“天儿一夜之间,长大了。”
叶澜儿擦了擦嘴,重重叹了口气: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好捏的团子了。
休养了三天之后,叶澜儿玉飞鸢与毛顺天一起,踏上了去西夷的路。
西夷与大夏国势不两立,他们甚至连通关文牒都不需要,进入西夷的唯一办法,就是偷渡。
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极为荒凉的路。
连绵的山脉,荒芜的土地。为了翻越这界山,他们吃光了备足了半月的粮食,喝光了所有的水,每个人至少都消瘦了十斤,终于赶到了西夷国的一个边陲小镇。
这里人的服饰装扮与中原大夏国的差异很大。
尤其是女子的发饰和首饰。
在叶澜儿看来他们如同前世的新疆人,一头的小辫子,头上带的是金子做的各种花式的发箍。穿着长裙和长裤,比起中原女子来说,行动要方便的多。
但是,叶澜儿他们还是决定做男子的装扮。因为,这样更简单。
可是他们现在的样子,不好大摇大摆去成衣店。
于是飞贼叶澜儿再次大显身手,钻入民房中偷了人家的衣服,装扮了起来。
头发随便一束,绑上一块抹额,穿着半皮子半棉布的衣服,看上去到有些英姿飒爽。
只是他们手头上没有易容的工具,只得把脸涂得脏脏的,掩盖住原来的容貌。
这个小城距离西夷的都城还有上千里的路程,玉飞鸢好不容易打听着,花重金从一户人家买了了一辆马车。
只是在这户人家逗留的时候,毛顺天发现一个婢女托着一架古琴经过,便使了小孩子脾气,非要这琴。
叶澜儿拉着劝这个熊孩子:到人家里玩耍不要随随便便要主人的东西。
可是天儿如同鬼上身了一半,竟然撒起泼来,无奈,玉飞鸢又掏出金子,重金求琴。
没想到主人这次倒是极为痛快,说是这琴不过是一个乞丐为了讨口吃的押给他的。他们这里的人哪有会弹这玩意儿的,这不刚要仍库房里落灰呢。
他十分大方地将着琴卖给了玉飞鸢,也十分不客气地收了那锭金子。
毛天儿得到那琴之后立刻就收了眼泪,甚至立刻收了他小孩子的模样,变作深沉的少年,一直将那琴抱在怀里。
玉飞鸢和叶澜儿另外准备好了路上所需要的食物和水之后,三个人不作停留,继续赶路。
叶澜儿不会赶车,跟毛天儿一起坐在车厢里。
她看到毛天儿两眼发直,抱着琴不知道在出神地想什么,伸出手来在他面前晃了晃。
“喂,小鬼头,想什么呢?这一路,你一天比一天话少,一天比一天沉闷,没劲了哈。”
毛天儿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半晌,开口问道:“澜儿姐姐,我爷爷临死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叶澜儿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嗨,没什么,就是把两本很重要的琴谱送给我了。可惜我又不会弹琴,真是浪费了。怎么,你想要?姐姐看你这么喜欢琴,不如,我把琴谱送给你吧?”
毛天儿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至少比叶澜儿要严肃的多:“澜儿姐姐,爷爷给你的东西,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关键时刻,这两本琴谱,可抵得上千万人的性命。”
叶澜儿嘴角抽了抽,伸手毛天儿的头上拍了一巴掌:“你能不能不要一副大人的口吻跟我讲话,我真的适应不了好吧?我知道,毛前辈可是左手魔琴,他的琴谱,我肯定会保管好的。
但是,对毛前辈来说,最重要的可不是琴谱,而是你啊。”
毛天儿叹了口气:“对天儿而言最重要的 ,又何尝不是爷爷。”
叶澜儿坐到了毛天儿的身边,揽着他的肩膀:“所以,你是因为思念爷爷,所以见到这琴才会使性子非要买下?”
毛天儿将叶澜儿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拿开,坐到了她的对面去。
“不,我之所以非要这把琴,是因为这本就是爷爷的琴。”
说罢,毛天儿将着七弦琴放在自己的腿上,双臂展开,双手抚弦。
顷刻间,如水般悦耳的音乐从他的指尖流淌而来。
叶澜儿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音乐,她看着毛天儿那双仍然带着婴儿肥却无比优美地舞动着的双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曲终了,叶澜儿迟迟地回不过神来。
她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玉飞鸢早已停下了马车。
她此刻静静地坐在车厢门外,满面清泪。
久之,叶澜儿终于回过神来。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只有八岁的男童:“是毛前辈教你的?你这也弹得太好了吧?你这简直就是音乐神童,当代莫扎特啊!”
毛天儿摇摇头:“爷爷他从未教授过我。”
叶澜儿呼吸急促了一下:“那你怎么学的?”
“我还小的时候,每当夜里趁我睡着,爷爷总会抚琴。我听得多了,就学会了。”
叶澜儿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心说这比莫扎特还要莫扎特啊。
“其实,爷爷那天跟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要把我送到西夷的赫连部对不对?”
叶澜儿惊愕,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其实我都知道。从小我就知道,我有一副蓝色的眼珠,这不是大夏国人该有的样子。而西夷的赫连部,全部都是蓝眼珠。
爷爷就是害怕我长大后,会忘恩负义,会如同西夷的那个护国大将公孙赫一般血腥屠戮大夏国人,才从不肯教我功夫。
我理解爷爷的担忧,我日日扮演一个可爱的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就是想让他能够偶尔放下担忧,不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后悔。
现在爷爷走了,我也没有必要在掩饰最本来的自我。
我早就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个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