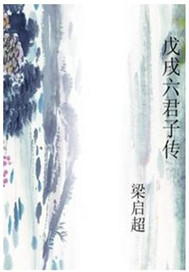今年夏天,苏娅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多年的广州太热太闹,太脏太乱。自己心爱的羊城,怎么会黯然失色呢?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离开学还有三天,苏娅就逃命似的飞到了北京。什么也没干,睡了三天。
明年就要开始实习,所以第三学期实际上是在校的最后一个学期。
本学期苏娅计划了许多事,结果只完成一半:出版了一部长篇纪实作品;而电影剧本及配套电视剧《生活永远差那么一点》,酝酿日久,终未能升华成醇醪。
本学期苏娅常无端地不耐烦。致使她与共处一室的司马云磨擦不断升级。
司马云身上既继承了一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其劣根性。
有一件事颇能体现司马云的个性:
东南某地一位大老板,欲独揽本地烟草专卖权,借此成为超级大老板。大老板找到司马云,请她打通关节,如成功,可得重酬10万元。
这事司马云办得很顺利。
大老板大喜,让司马云在车内坐着,等他办妥最后的例行手续。司马云等了2个小时,还不见大老板出来。如此空等,让司马云烦躁不已,以她的个性,那烟草贩子要是胆敢和她耍花招,劈手夺回批文,就撕他个稀烂。正要付诸行动,转念一想,不好太冲动,闹僵对谁都没好处,就开着那大老板向朋友借来的“丰田”车,返回了学院,有这车在手里扣着,还怕那烟草贩子赖账不成?在停车场泊好车,不经意间看见“CD”唱片中间有一块金灿灿的手表,便顺手拿过,装在自己的手袋中。她的“地雷专家”这许多年来,一直戴着他们结婚时买下的“上海”表,早应该改朝换代了。
次日一早,大老板便来到学员宿舍,司马云说:“我还以为你要瞒天过海呢。”
大老板忙说:“岂敢岂敢。”向司马云要回车钥匙,与她一同来到停车场。
打开车门,大老板东翻西找,神色凝重起来,急惶惶问司马云:“你昨天见到车上的一块手表吗?”
“没有啊。”司马云面不改色,心下思忖,此人也忒小气,不见了三五百块钱的表也这么大惊小怪,真正不失农民本色。
大老板顿足道:“糟糕!这是我为你预备的谢礼呢,卫星发射纪念金表,市价10万,再转手起码12万啊!”
司马云红了脸,说:“是我运气不好。丢了就丢了吧。”
大老板自然心中有数,说了些客气话,给了5千块茶水费,并有意无意把购买金表的发票丢在地上,称谢而去。
司马云赶紧收拾起金表发票,回到宿舍,对苏娅咧嘴一笑:“真好笑,我偷走了我自己的东西。”
苏娅也觉好笑。
苏娅与司马云闹翻,为的是一件比这更好笑的事:司马云的一个平凡的连环屁,吓退了苏娅的一句不平凡的呼之欲出的好诗。
这一天是星期五,苏娅傍晚时分打电话回广州。儿子关东说:“爸爸又去桂林了。”
近来关山海老在星期五去桂林,桂林分公司金经理精明能干,是老“期货”了,用得着总经理每个星期都去亲临指导吗?何况,指导业务为什么总选在星期五?周末周日期货“休盘”,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千回百转就绕到了羊秘书身上,一想到羊秘书就想到酒店客房门锁上的“请勿打扰”,越想越觉得大有问题。苏娅在桂林时,曾明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又很不明智)地避开了这个问题。而事实上所谓的“避开”永远是自欺。
想到自欺就很烦,很烦就很难写出好诗。好不容易快要揪住一句,却被司马云很没有诗意的响屁吓退,苏娅一下子气上眉尖,掷笔发火:“你放屁不能斯文点吗?”
司马云大惑不解,苏娅从未如此顶撞自己,憨笑一声:“你怎么忽然管起屁事来了?”
“恶心!”苏娅脱口而出。
“我大大方方放屁恶啥心?偷偷摸摸放屁那才真叫恶心。”司马云也认真起来。
苏娅仍然有点不讲理地重复那两个字:“恶心!”
“你真的这样看我?”
“恶心!”苏娅已近乎孩子气。
一连三个糟糕的“恶心”激得司马云跳起来,从苏娅床底下捉出她“开夜车”用来煮面条的电炉:“你违章烧电炉就不恶心?”
抓过电炉,隔窗扔下四楼,也不管是否对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不堪设想的威胁。
苏娅也不甘示弱,站起身,一脚把司马云夜里使用的痰盂踢出门外。
自此,两人再不说话。
无端与司马云闹翻,汪静等一干与司马云有嫌隙的同学,拍手称快,苏娅更多的倒是惆怅,甚至有几分歉疚。其实她并不觉得司马云怎么“恶心”,尽管司马云身上有着某些恶习,但一年多来,并没怎么计较,她能够理解,人们为了美好地生存,有意无意间做下的一些不太美好的事儿。难得的是:司马云做出不文之事,并不掩饰,做过之后,便坦荡荡地说:“我又做了一件卑鄙事……”天下远比司马云卑鄙的大有其人,可有谁大大方方坦言自己卑鄙呢?就凭这一点,已觉得司马云堪称“君子”。只是因为自己实在没心情,也就懒得去同司马云和解,就这么不声不响,各怀各的心思,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要复习考试了,苏娅上课很少记笔记,临考前满脑子一盆浆糊,心想,这一下可全砸了,她知道司马云外粗内细,课堂笔记从来一丝不苟,可她又实在不好意思问她要笔记看。
正束手无策时,司马云把笔记本丢到她的桌上。“明天考试,这笔记本也许用得着。”
翻开那工工整整的笔记,苏娅心里一下涌起了深深的歉意……
10月20日,苏娅28岁生日。中午,她没练钢琴,打个电话回家。关氏父子竟谁也没想起今天苏娅生日!苏娅好生惆怅,放下电话,乘车至王府井书店,买下一套精装的《追忆逝水年华》,蹲在书店台阶上,向一位中学生借来一支钢笔,在书的扉页上端正题字:
苏娅:
祝你生日快乐!
苏娅
1994.10.20 北京
提着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苏娅回到学院,下午继续上课。
苏娅不想跟任何人说出今天自己生日,不然相好的同学们定会逮住她欢歌笑语,花天酒地,热闹一番。
没有兴致呐。
晚餐时,要了很多菜,吃起来全没有往日的滋味。毫无意识地等待什么,就叫发愣吧。她想。
汪静问她在想什么。她说她在想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变傻。“那是因为吃饱了撑的。”汪静说,唤几个人来把她丰足的菜全共了产。
回到宿舍,门房胡大妈迎着苏娅,说:“下午有人给你打电话,说晚上8点来看你。”
“是谁?”
“不知道。”
苏娅也没多想,管他是谁呢。
生日的秘密价值,只有自己才知道。苏娅一个人坐在宿舍里,也不开灯,想自己的心事,想自己28年来的光阴故事,就像亨利·詹姆斯所说的那样:“给自己写愉快而无用的信……”
这也是幸福!
不知什么时候,整个宿舍楼闹革命似的喧哗起来。有线喇叭里响起胡大妈的声音:“413,413,苏娅接客。”
苏娅打开门,一愣:一至四楼的楼梯扶手上,直到通向房间的走廊两边,插满了点燃的生日彩烛。
莫非,晚餐时,自己毫无意识地等待的东西就是这些好奇的彩烛?
接着,喇叭里一个男人说:“苏娅,说不清楚的‘爱情傻瓜’,祝您生日快乐!”随后就用洋泾浜英语唱起了五音不全的《生日快乐》歌。
朱朱!
谁也不会滥用这“傻瓜”的特权,除了朱朱。
因了这些彩烛,学院灰暗的宿舍楼,就像枯木逢春,开满鲜花。
苏娅眼含热泪,跑下楼梯。
出门张望的男女学员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和着喇叭里朱朱的腔调,齐声高唱那支人类幸福地唱得最多的歌。
远远地,朱朱向苏娅露出“1号傻瓜”的傻笑。
带着28朵玫瑰,28磅重的蛋糕,朱朱从东京借道香港飞到北京,只为苏娅的生日而来,此举不仅让渴望浪漫的空中小姐感动不已,连对现代爱情故事并无好感的门房胡大妈也动了心,特意允许朱朱违反消防管制条例在楼梯上插满彩烛,还允许他使用其专有的有线喇叭。学院规定,晚10时后,任何男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进入女生宿舍;同时在通往女生宿舍的走廊上砌上一堵墙。但这些措施,抑制不了爱情的潮汐。在爱情游戏中,苏娅始终不乱方寸。男生中同样形只影单的林森临时赶制一柄丘比特之箭,试图向苏娅射去,苏娅连忙躲进有中国特色的深宅大院,层层设防。苏娅因此被大家戏称为“本世纪最后一位淑女”。
殊不料“淑女”在水一方,自有迢遥的“良人”,生日之夜,自天而降。大家惊疑,继而欢呼,从宿舍一涌而出,一拨人马抬起那28磅的蛋糕,挤满413室。
毕业后各奔东西的学员们,至今还记得苏娅那场盛大的生日晚会。朱朱妙语连珠,不时引发哄堂大笑,连一向郁郁寡欢的苏娅,也兴奋得满脸泛起少女们才常有的潮红。来自日本的28磅重的蛋糕大家分食了一半,另一半由汪静首先发难,刮下一匙嘻嘻笑着,准确地摔在朱朱的鼻尖上,使他看起来像是古装戏剧中的小丑;大家笑声未停,朱朱大笑着将手中纸碟中的蛋糕一下子扣在汪静脸上,最漂亮的汪静立刻变成了天底下最难看的丑八怪。接下来,大伙笑闹成一团,纷纷把奶油蛋糕乱涂乱抹,谁也未能幸免。胡大妈见闹得没谱,与管理员上楼来,打算提个醒,一出现在门口,脸上也被抹了一把,瞧众人面目全非的样子,她笑得比谁都响,拿一个苹果,下了楼。
大伙尽兴散去后,汪静怂恿苏娅,今晚留下朱朱,反正司马云也不在。苏娅涨红了脸,说: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与朱朱清清白白。别胡思乱想。”
“清清白白一说出来就不清不白了。”汪静一脸诡笑,带上门走了。
苏娅歉意地对朱朱说:“对不起。我的这些同学都想入非非。”
朱朱说:“我也爱想入非非呢。”
“别逗啦。”苏娅说着,站起身。
把朱朱送到学院门口。
的士来了。朱朱说:“我买的是双程机票,明天上午就要返回日本。许多来不及说的话,看来又要带回去了。”
苏娅心中震颤了一下。她又何尝不是有许多话要说呢?想也没想,跟朱朱坐进的士,到了酒店。
朱朱的“步步高升助长灵”让他在日本大发其财。但异国他乡的“想爱就爱”并未有多少爱的原汁原味。很大程度上,他是为了逃避苏娅,逃避想爱而不能爱的她,而远走那岛国的。问题是,你想逃避什么时,也就什么也无法逃避了。这是爱的悖论,也是自由的悖论。
朱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旁观者,意味着他只能注视着她,见证着她,就像一团过眼烟云见证着天空。
又像在茫茫人海中掩藏的侦探,不放过敌人的每一个细节。对朱朱来说,苏娅就是一个亲爱的“敌人”,时时刻刻给自己温柔的杀伤。只有保持某种距离,才不至于被她“击毙”。然而,你怎样时时刻刻警惕一个男子汉的热血,不至于使爱情最深刻的恐惧到来呢?
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朱朱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然勇往直前,在离别苏娅一年多之后,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来为她过生日。
在酒店客房里,两人默默对视一刻,他握住她的纤纤素手,说:“苏娅。我想告诉你,爱就像战争一样,是生活中最严肃的事情。”
他的话让她吃了一惊,瞧见他眼里异样的光芒,极端地盯着她,像一把阴影中的匕首。她不敢直视,低头看他握住自己的手,像小时候聚精会神地看蚂蚁搬家,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汗毛、毛细血管,一一在目。
朱朱已兵临城下,“战争”一触即发。
去年的100束玫瑰以及“傻”事种种,犹如一发发重磅炮弹,至今硝烟未散;尽管朱朱的“敢死”行动,并没能攻破苏娅的堡垒,却也使苏娅领略到了爱情独有的风光,心底里微微为之颤栗。只是因为拘泥于比军纪更严明的爱情规则,才没有铤而走险,投身这场注定没有好结果的爱情战争,落荒而逃。
时隔一年,销声匿迹的朱朱突然间卷土重来,苏娅猝不及防,亦惊亦喜之际,一不小心已陷入脉脉柔情的重围之中。
苏娅没怎么抗拒。她一直苦心构筑的婚姻城池,因关山海的背叛,已出现可怕的裂缝,不堪一击,何况是朱朱切中要害的致命的一击。
跟随朱朱踏入“的士”的那一刻,苏娅心中惶惑,自己这是远离爱情而去还是投奔爱情而来?只是本能地觉得朱朱不应该就这么回日本去,今夜应该发生点什么,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现实应该水落石出了,开始或者结束。
读者预料中的事被慢慢推向高潮。
朱朱捧着苏娅的手,表情夸张,像欣赏一件稀世珍宝,小心抚摩,小心把玩,小心说:“请问,我可以吻吻你的手吗?”
苏娅没作声,心下思忖,“想爱就爱”的朱朱咋变得这么迂腐?
“沉默就是默许,我可以这么认为吗?”朱朱说着就把嘴凑向了苏娅的手。
吻遍苏娅每一根手指以后,朱朱抬起头,见苏娅面无表情微闭双眼斜靠在沙发上,又说:“请问,我还能吻吻你其他地方吗?”
朱朱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轻薄浪子,苏娅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心头掠过一丝不快。很想抽出手来,拂袖而去。但她最终没动,也没说什么,她已经习惯了朱朱玩世不恭,何况朱朱为她付出的已太多太多,说一两句过分的话也不算过分。
“沉默就是默许,我可以继续这么认为吗?”
苏娅正要大声喊“不”,却被朱朱的一个长吻堵了回去。
深长的吻使苏娅如坠入深渊一般,觉得恐惧,也觉得刺激。被压抑多年的情感突然喷薄而出,爱情规则如同许许多多的规章制度一样,如今早已不被人遵守,为什么要我做最后的守望者。
吻到热情洋溢处,苏娅发出了大部分女性此刻应有的**,双手紧抱住朱朱,今夜,她想爱就爱。
经过两年的“战争”,朱朱今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胜利,可以挥兵进城,长驱直入了。
成功在即,朱朱却没有策马进城。长叹一声,他放开苏娅,竟站到窗前抽起烟来。
苏娅感到自己正在被抛弃,像汪洋中的一条独木舟,离岸边越来越远。她木然看着朱朱的背影,内心的焦躁和羞愧,使她觉得此人简直可耻。她充满幽怨,说:“你从日本回来,只为了要羞辱我吗?”
朱朱回过身来,泪流满面,说:“苏娅,你为什么不拒绝我,痛骂我呢?我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流氓,只为了让你恶心我呐。”
朱朱的眼泪让苏娅大为惊疑:“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把红红的烟头在左手掌里摁灭,揉碎,朱朱的眉头皱也不皱,走上前重新握住苏娅的手,说:“苏娅,对不起,我绝不是戏弄你,我只是作践我自己。我对你说的故事中,隐瞒了一个细节,当年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我被老婆踢坏了身子,再也做不成男人了。”
苏娅透心冰凉,说:“那么,人们传说的你的风流韵事,都是假的?”
朱朱轻轻拭去苏娅眼中的泪花,笑一笑:“其实这也没什么,因为不能爱,我才能想爱就爱;因为不是男人,我才能为男人所不敢为。”
苏娅抱住朱朱,说:“朱朱,你是个真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