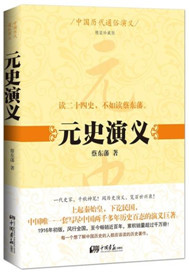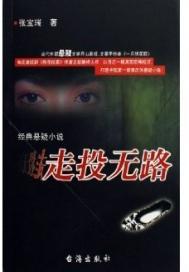8月29日,苏娅奔波了一天,办好了一切手续,晚上又打点行装,整理文稿书籍,忙到深夜,蓦地想起冷落了儿子。明天就要飞过长江以北,黄河以北,直到长城脚下的皇城根儿,第一次出这么远的远门,第一次在较长的时间内离开孩子和丈夫,她的惆怅首先来自一个女人对感伤的思索,其次才来自对离别即将到来的事实进行判断。仿佛灿烂阳光中飘移的影子,第一次,她觉悟到时光的流逝与一个人淡淡的一笑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就这样,她在儿子的床头坐了很久,发了很久的呆。
“唉,女人,”关山海从枕边抬起头,说,“就像一道谜语一样让人猜不透。你大概想把这个家也搬到北京去。是不是?”
“我爱你……”苏娅在感伤的思索中,被一种独白式的孤单所左右,情不自禁说了一句非常真实、又非常不真实的话:“真实的是心声,不真实的是言词。”
“别,别,”关山海的双手做了个暂停状,说:“别让我失眠。好不好?明天我还得去上班赚钱。”
苏娅笑了那么一笑。其实,两人都在不同意义上的错觉中。
而与朋友(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黎曼和李修玲),领导和同事,均来不及话别了,电话也没心思打,甚至与爸爸妈妈,也没通个消息。“到北京以后再说吧。”她惆怅地想。
30日上午9时30分,苏娅站在客厅中央,仿佛站在客厅中央全方位扫视一圈,就能想起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带齐。院方突然来电:“有话要说,请赶快来政治处!”
关山海很烦,说:“你的医院比关东的幼儿园还婆婆妈妈,敢情不是开你的欢送会吧?”
话虽这么说,还是主动开车,一溜烟把苏娅送到了B医院大门前。
苏娅歉意一笑,让他在奔驰560里待着,说:“你抽支烟吧。不会影响到赶航班的。”
而心里,她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来由,又好像根本不需要来由。到B医院工作4年多了,政治处的办公室她不知去过多少回,这次她被异样的陌生感包围,步子怎么也迈不踏实。
喘了一口气,推开那门。
政治处主任郝大姐长得慈眉善眼,擅长把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情味结合起来,因而深得医院上上下下同志们的敬重。前天,她对苏娅考取大名鼎鼎的诗艺学院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和勉励,并以经验的口气提及北方气候与南国气候的差异,关切地谈到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应注意的身体保健及饮食方面的几个问题,让苏娅谢了几谢。
苏娅一进门,郝大姐以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招呼她坐下。
她欠身坐在门边的折椅上,那样子仿佛随时准备抽身而去,飞往北京。
除了郝大姐,屋子里还坐着院领导及其他几位军官。苏娅礼貌地向他们笑了笑。对方笑或不笑,笑的很勉强;不笑的脸上,则像一段新修的马路一样平板。
“我想知道这……”苏娅又疑惑又尴尬。
郝大姐的开场白从肯定苏娅的工作和学习讲起,渐渐过渡到此次谈话的实质性内容上来:“小苏,你还没转业,办完转业手续才能去上学。”她顿了顿,仿佛为了让苏娅有一个思想准备,说,“你暂时不能上学……”
苏娅一听,不由得弹直身子,惊问:“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考上了,先上学,转业手续,正常办。”
院长摆摆手,让她安静坐好。
苏娅顺从地坐下,确切地说,更像是挨着椅子半蹲着,满脸不解。
“是这样,”郝大姐的神情既有组织的严肃又有个人的同情,说,“你没办转业手续,就仍然是一名军人,读地方大学,是不允许的。”
苏娅心里咯噔了一下,就再也没听清楚郝大姐下面的话。
一股委屈之泪,不由得涌上眼眶,苏娅说:“我不明白……”
办公室里出现一阵难堪的沉默。
院长伸手摸了摸已有些白发的鬓角,清了清喉咙,说:“小苏,我们只是通知你暂时不要去报到。”
苏娅惊愕不已。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
是谁,废寝忘食,啃完了一门又一门需要考试的课程?
是谁,心急火燎,在赶考路上,跑得心脏几乎都要跳出来,为圆一个久远而又亲切的大学梦?
又是谁……
眼看希望变成泡影,苏娅哭出了声!包括面部表情十分僵硬的人在内,以院长为首的领导都为她感到不同程度上的难过。院长又摸了摸自己鬓角上的白发,说:
“小苏,别伤心。你先回去上班,千万不能闹情绪影响到工作……”
院长的话还没说完,苏娅就掩面跑出了政治处办公室。
以异乎寻常的耐心,在B医院门前待着的关山海,无所事事观望街上的人群,发现人群中也有无所事事观望自己的闲人,便觉十分无聊。已近中午,本次航班的飞机恐怕快到北京了,苏娅还没出来,就让他感到医院找苏娅谈话不是一般的“婆婆妈妈”,以他的性格,从来不会坐等什么。可现在,除了坐等,你又能干什么?
他用烟头,把过期作废的机票烧了个洞。正试着要烧第二个洞时,苏娅满脸泪水,坐进车内。关山海似乎并不吃惊,不动声色地问:
“怎么,出事啦?”
她咬咬嘴唇,点点头。
“啥事?”
她扭头瞧着他,把原委陈述了一遍。关山海把手头刚抽了几口的“555”,往车窗外一丢,冷笑说:“不可能!是不是有人在暗中与你过不去?!”
“是谁呢?”苏娅一点儿也想不起自己曾在哪里得罪过谁。
关山海又弹出一支烟,点上,狠狠吸两下,说:“管他呢!你还想不想上学?”
“这还要问吗?”
“入学手续带在身上吗?”
“在。”
“我直接送你去机场,赶下午1:30的航班!”他又把刚抽了几口的“555”,往车窗外一丢,一边说,一边发动奔驰560,向机场奔驰而去。
“可我连一件衣服也没带呀?”
“来不及回家去取了。”他说,“有钱,就什么都有了。”他用手机指示自己的财务人员小娟速送人民币和港币各一万到白云机场检票口,接着对苏娅说:
“到北京,你要舍得花钱,学会花钱。花钱也是门学问呢。”
“可是,”苏娅下意识回头,朝车后窗看,说,“我这不是明显违背了组织纪律吗?”
“你都转业了,还管那么多,广州这边有事我顶着。”关山海说。
抵达机场,他让苏娅在车里静静地坐一会稳定心态,马不停蹄,托关系找熟人,跑得满头大汗,搞来一张迫在眉睫的高价票,还是头等舱。苏娅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
“这时无论花多少钱都值。关键时刻花钱,才能真正体现钱的价值,比你在商场漫不经心购物花钱,远远来得真实。懂吗?”
她点点头,若有所悟地,感激地。
小娟把钱送来了,附带一束玫瑰,一并递给苏娅。关山海一愣,警觉地问:
“这玩意哪来的?”
小娟一笑,说:“听您说关夫人要去首都上学,我买的,表示一点心意。”
“不错,不错。”关山海笑逐颜开,说,“你善解人意。回去我给你涨工资。”
苏娅正要对小娟说几句好言好语,关山海催促她赶快登机,还有10分钟,航班就要起飞。
苏娅过检票口之前,想与关山海临别拥抱一下,见他没有半点儿女情长的意思,便作罢了;过检票口之后,她回头想再看一眼,却只瞧见他已走远的背影,边走边打着手机。
飞机不断拔高,苏娅的心却不断下沉:广州已越来越远,做梦似的,说离开就离开了,尤其当这离开仿佛是一种匆匆出逃时,它唤起你心中感念的东西,自然比从心中失落的东西要少得多,要微不足道得多。舷窗外的天空,有一种说不出的蓝,蓝得使人隐隐想哭!
当然,她没有哭,手拿一束玫瑰,空空地坐着,空空地想着。
头等舱里除了她,只有一位中年男士。她进舱坐到他旁边时,向他笑了那么一笑。他正展开一叠报纸,稍稍侧过头,点一点,那意思仿佛是说:“你请便。”便接着看报,神情有点冷。
不知为什么,苏娅感到他浑身散发的这种“冷”很吸引人。不仅具有高贵气质,也很可能具有隐藏在高贵之后深深的平易。从这种“冷”的辩证中,你自然会估摸到他的职务和地位非同一般。他的衣着,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休闲式西服并非花哨的名牌,但质地上乘,大方得体。他很注意读报纸的头版,带着审阅文件似的职业性的眼光,翻到后几版,就大凡是浏览了。
看得略略倦了,他放下报纸,伸手摸摸头发,手掌在后脑勺上轻拍了两下。他头部侧面的轮廓极富雕塑感,表明他的坚定,和可能的极强的思辨力。
心里本来空空荡荡的苏娅,坐在中年男士身边,慢慢也有了坚定感。猛然,她意识到为什么头等舱只有两位乘客,应该设想,此次航班的头等舱是有意为这先生空着的,可见此人来头不小,自己不过是一个临时搭乘进来的“闯入者”。因此,她忐忑不安,把玫瑰从左手放到右手,又从右手放到左手,末了,干脆双手握着它。
中年男士见身边这年轻而漂亮的女人有点心神不定,便和蔼而幽默地问:“小姐,你双手紧握玫瑰,像握枪一样,大概不是去执行军务吧?”
苏娅腼腆一笑,说:“我去诗艺学院进修。先生。”
“看起来,你是第一次去北京?”
“啊,”苏娅惊诧他的洞察力,想反问一句他为什么看得出来她是第一次去北京,转念又想这可能并不礼貌,说,“是的。但愿我坐在这里,没有使你感到不便。”
“此话怎讲?”他摊摊手,说,“我们都是乘客,是平等的嘛。”
“这头等舱里,只有您和我。”苏娅的一只手松开玫瑰,这与她内心的放松有关,说,“我是匆匆托关系买高价票挤进这头等舱的。在我之前,只有先生您,一个人在这里。”
他听着她的话很有意思,明知头等舱很空,偏要用个意味深长的“挤”字,而加重语气的“只有先生您,一个人在这里”这句话,表明估摸出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总是会被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低的领导干部看得太高太重,他们刻意安排的种种规格和排场,比如说,一个人独占一个头等舱,如果不是这个女的暗示,自己还真的以为是乘客量严重不足所致。他若有所思地摇摇头笑了那么一笑:
“小姐,你很敏锐,叫什么名字?”
“苏娅。”
“小苏,”他认真地瞧着她,问,“你怎样看我们两人坐头等舱的这个现象?”
“很正常,也很不正常。”她说。
“你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哦。”
“先生你难为我了。在您面前,我哪敢对事物进行判断?”
“小苏,你不仅敏锐,”他笑道,“还很狡猾。当然,是艺术的狡猾。能告诉我,你搞什么艺术吗?”
“诗。”
“难怪,你的狡猾,给我的印象,又为什么如此直率和清纯。”他说,目光里暗含赞许。
“先生,您是个大艺术家吧?”苏娅故意装糊涂,问。
他当即指出:“小苏,你的狡猾又来了,想装糊涂套我。是不是?在你这个年龄时,我曾想过要成为大艺术家,但后来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能请问先生的大名吗?”
“小苏,你一口一个‘先生’,叫得我怪别扭的。我姓廖,就叫我廖大哥吧。”他巧妙地回避了她的问题,又不让她失望。
此人很亲切、坦荡,也很自持神秘。苏娅与他在短短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中,从邂逅到相识,仿佛命运安排似的既偶然又顺理成章。临下飞机时,他随意地在一张纸片上写了个电话号码给苏娅,而她,把那张纸片也随意地塞在手袋里。
这说明:一个人以为命运的开始,大多是虚构的,而不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