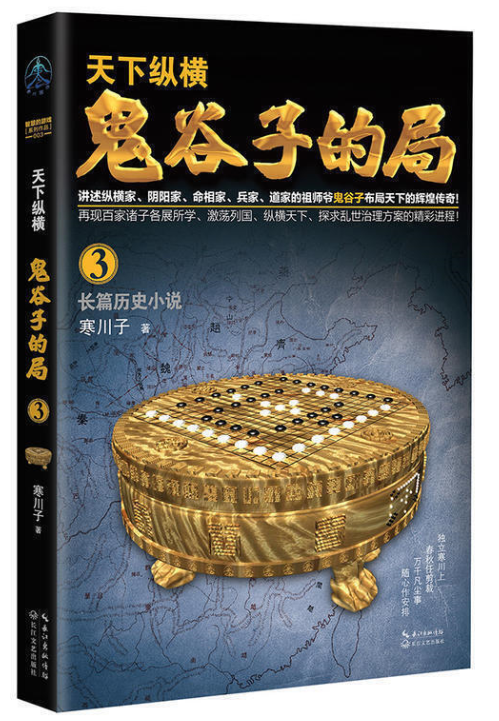严格地说,一首诗必定是另一首诗。诗人在提笔写下第一行诗后面对的仍然是和提笔之前一样的无穷的可能性,对于某一首诗的具体的修改则仅仅触及这无穷可能性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以有限对无穷,正如生命之于时间,必有莫大的哀痛与惋惜。这就有理由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诗集在编排上与别的诗集稍稍有些不同。
这部诗集的初编本无特异之处。但在具体审读、编辑的过程中,作者遇到了一个难题:她无法肯定那些已经修改定稿的诗篇确实优胜于它们的初稿,或者说,她在二者的对比中感到了某种程度的困惑和痛苦,因为她忽然觉得相当数量的改定稿并不比初稿更好,甚至还要差一些。对于她,这种困惑和痛苦并非仅仅出自对那些诗篇新旧稿的优劣对比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写作正处于求变之时,这是每一个有成就的诗人都必须面对的诗艺之狱。作为一个严肃而并不腼腆的诗人,她诚恳地希望能将这种变法的困苦向同行、评论家和普通读者稍稍作一些展示。普通读者可以据此更多地了解诗人的甘苦、一个优秀诗人成长的不易,评论家可以因此获得更多言之有据的、较为全面的话语,同行则无疑将从中受益并将有益的反馈施之于作者。我个人认为,对于一部有价值的诗集,这绝非额外的要求。而作为一个编辑,即使只有这三条理由中的一条,我就无法拒绝这种“变体”。但我还是有所担忧。其一,说到底诗歌写作毕竟是个人化的劳作,过分的坦率是否会导致某些有背初衷的误解;其二,一个真正有远见卓识的诗人的耳朵虽必善纳众声,但若众声一辞,耳中所闻只是集中在某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恰好是诗人此刻感触最深(比如变法之痛),急欲得诸认同的,则于诗人不无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任何认同都会带给被认同者一定程度的欣慰和沉迷,对于世俗生活这自然绝非坏事,但对于一个寄望于不断跃进的诗人的写作,这种欣慰和沉迷却极可能是一个障碍。基于上述原因,作者和我最后商定只在以下七篇的篇末附上它们的初稿:
《你好,忧愁》(《火之缘》)、《失眠夜的梦呓》(《失眠夜的胡言》)、《单音鼓》、《大风吹动心灵》、《救救心灵》(《上帝请闭上你的眼睛》)、《为思念赶一场命运》(《静谧如雪》)、《如履薄冰》。
这些初稿较之修定稿,或有更充沛的情感之力,或更多句式的变化,或近乎面目全非,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虽只寥寥数篇,却也足证其余。作者因担心这部诗集作如此“变体”而无说明会显得唐突而费解,嘱我写点说明文字,遂成此编后语。
王清平
199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