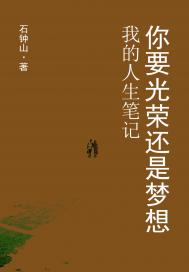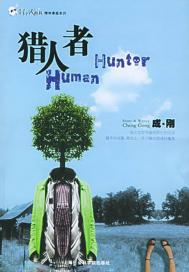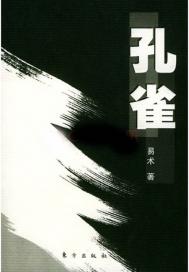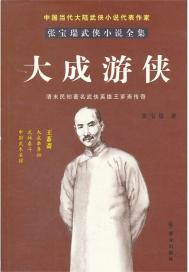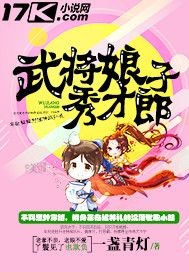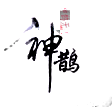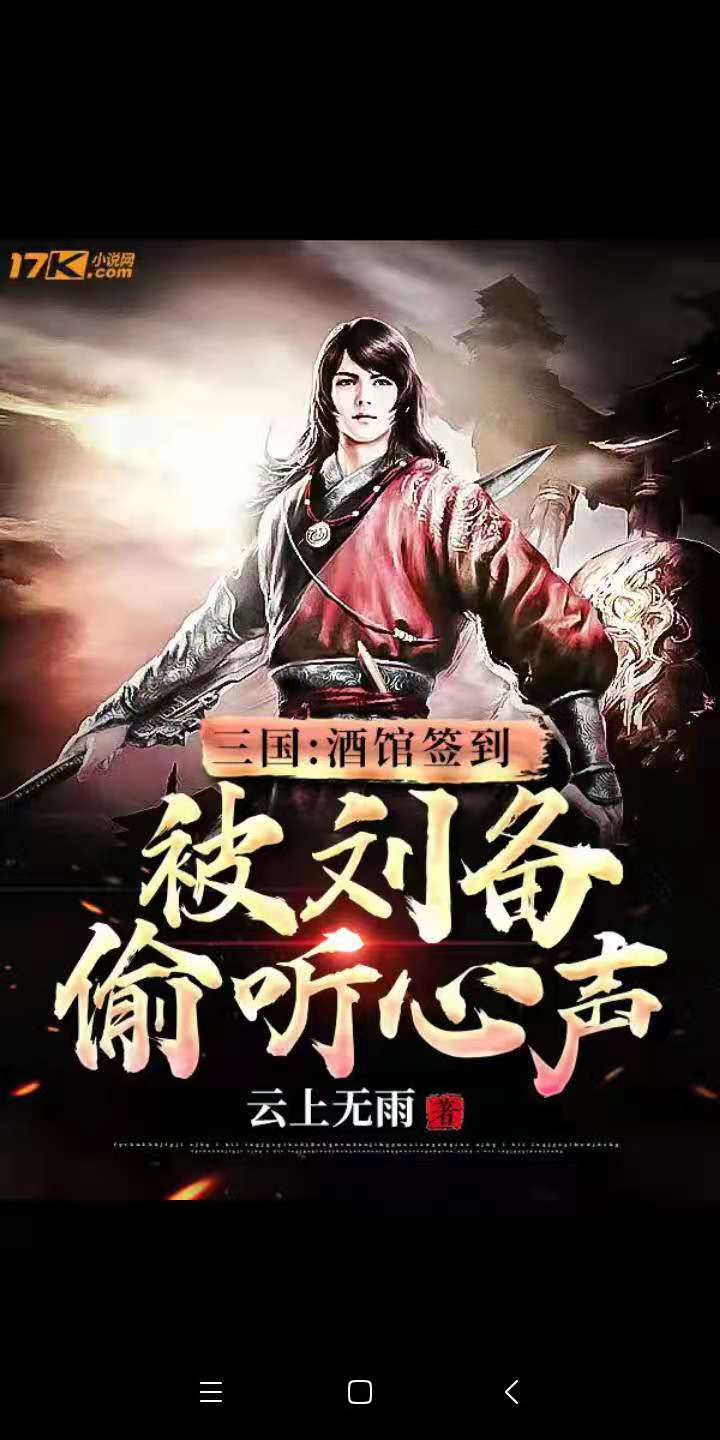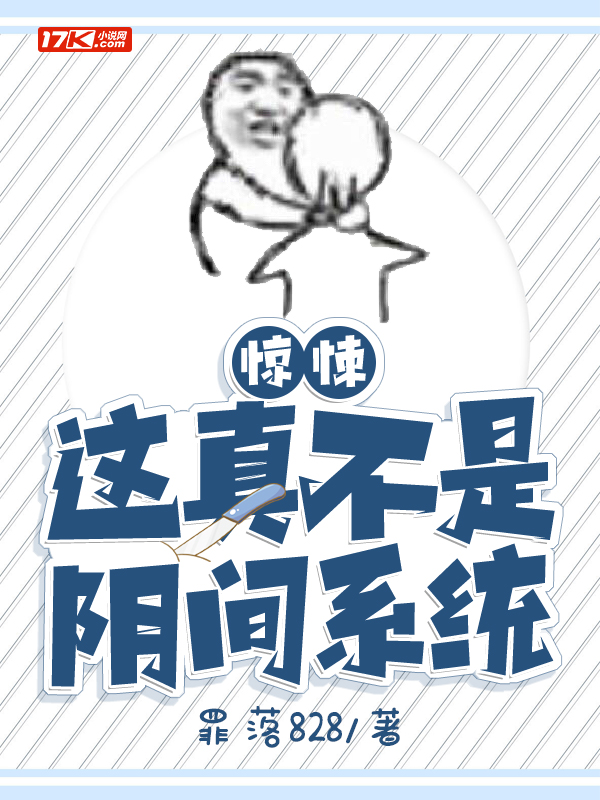◆温铁军
因为我目前正在从事的与生态文明高度相关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尽管对于本书作者作为重点讨论的动物蛋白质垂直整合的产业知之甚少,但由于我更看重的是它所关联的源头,也就是土地和农民。因此,借作序表达一些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目前我国农民在经济基础方面基本上还处于高度分散、无组织状态。高度分散的农民不可能和外部成规模的主体之间通过谈判形成正常的契约关系。在农业产业化的初期,中国分散的农民和国际市场一碰,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时期出现的“农户 公司”的模式给农民带来了某种缓冲,至少使得中国农民不必直接面对残酷的国际市场。但是,随着产业资本迅速扩张和社会剧烈变革,“公司 农户”的模式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和农民的所有问题,三农问题成为了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农业产业化困惑的表象,还表现在农民之于土地、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深层问题上。
根据我在世界各地农村的考察,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东亚那些以小农经济为农村经济基础的日本、韩国等,尽管都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照样存在“三农”问题。韩国农民在香港诉求,坚决反对全球化,就是因为韩国的“三农”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不论韩国的工业多么发达,其农村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凋敝的。在这些东亚以小农社会为基础的国家,化解或缓解“三农”困境,主要是靠新农村建设,韩国叫“新农村运动”,日本称之为“农村整治”,我国现在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于资源约束的国情相似,所以,尽管说法不同,政策内容却相差不多。
有人希望把美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翻版到中国来,似乎认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制度就万事大吉。但需要明白的常识是,“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仅有17万农场主,一个农场有几百公顷,农场所有者称为“farmer”,应翻译为“农场主”,而不应简单化地翻译成农民,美国农场主和中国的“农民”是异质性很强的两种不同经济主体。既然政策和理论的对象如此不同,难道能把美国的针对农场主的政策和理论搬来中国用吗?
话题回到本书。
以一只鸡为媒,扫描中国农畜食品产业,应该说是一种新颖的思路。也许有的人会说:从粮食安全,到国际贸易,从一个养鸡农民的流水账到农畜食品产业的破局,这些话题如何统摄到一个主题之下?
这句话正好问到一个关键点上。
农业产业化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从中国的土地上衍生的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其背后都链接着纷纭复杂的、涵盖着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要素。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追溯,其源头应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生态功能问题。从农村的生态功能的恢复,到农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再到农民疾病控制,只有实现农村的生态功能恢复和回归,在另一端,城市的食品安全才能得到来自源头的保障。但是农村生态功能的恢复,并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终极答案。这个问题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执法系统的良性运转、公民道德的自律与完善、当代文化的断裂与修复等诸多社会化问题。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围绕一只鸡,能衍生出如此丰蕴的话题。
关于本书的内容,引起我阅读和思考兴趣的素材,浓缩起来,其实也就是这只鸡,以及书中写出的一个鸡农吕忠喜的流水账。
我想说的是吕忠喜,这个看似极普通的东北农民,他的生活和工作,极类似于我一直阐释的农村生态功能恢复进程中的农民人物。
这个人到现在为止,先后和鱼、鸡打交道,尽管捕鱼、养鸡的过程,没有什么诗意,没有可供诗人抒情的素材,更没有感天动地泣鬼神的戏剧性经历,甚至没有更丰富的可供记者挖掘的内容。但是,正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民,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当下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生活形态剧烈转变的时期,依然保有着农民的秉性。他的生活一直根植于他周围的土地,他的文化没有被割裂,他的生活没有被所谓的经济大潮所中断、打乱,他的工作状态延续了中国农村的文脉。但是,透过“公司 农户”模式,他以及他的家庭又有机地和一个产业、以及这个产业的发展、勃兴、崛起联系在了一起。这也许正是一种正常的农村生态模型。
另外我想说的是这只鸡。
本书提供了30多年前的一只鸡,和当下中国动物蛋白质产业崛起框架下的一只鸡的比对。同是这样的一只鸡,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产业经济的成熟,而变得语义迥异。
30多年前,一只鸡,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日常生活开支的来源。另外,这只鸡依然延续着小农经济社会特有的身份。
而现在,这只鸡从形态和基因上看,与30年前的那只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围绕这只鸡生成的语义,却显然早已逾越了小农经济社会体制下一只家禽的内涵。
同样是这只鸡,在中国的农畜食品产业亟待破局的今天,它成为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个符号。在这个符号的上、下游,链接了经济的、文化的、产业的、个体的诸多要素,使得这只鸡成为一个饶有趣味的元素。
大成集团从民生所需的油脂起家,之后介入到饲料行业,而在新的产业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定位已然成为动物蛋白质垂直整合的产业,大成找准了产业经济的命门。透过一个本土企业的成长,我们也可以看出,近30余年以来,中国农畜食品产业发展和试图超越的一个轨迹。
我们乐于看见这只大鸡的崛起!
是为序。
2007年12月10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