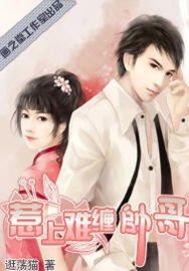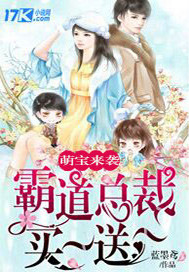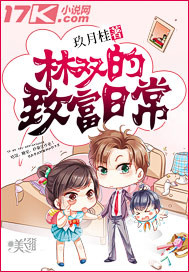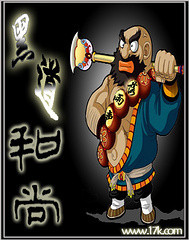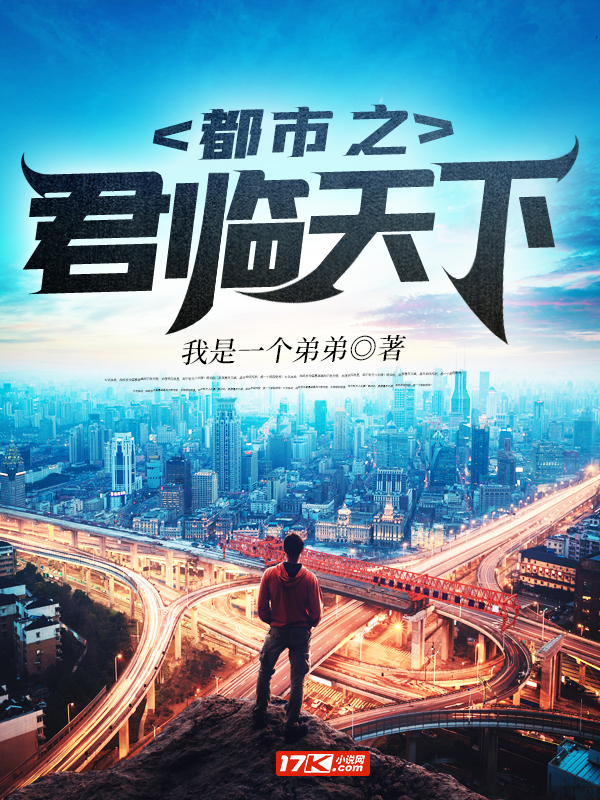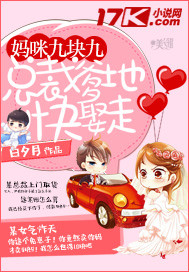第四部 山道弯弯
第一章 崭新的年代
路,本是人走出来的(当然不是现在的水泥路),走出来的路,当然是曲折的。
格针岭人走出来的路,更是山道弯弯。
格针岭村西有个高土岭,名曰“脱磨山”。就在这脱磨山下,有一个叫“鬼翻锅”的山泉,不知它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地球变化形成的,或许是哪个勤劳之人开凿的。这个神奇的山泉,方圆丈余,深过六尺。泉水冬暖夏凉,夏天,你触水就觉得冷如冰;冬天,远远望去,又如一锅开水在翻腾,冒着团团热气,那可真像“鬼”在搅翻了锅似的。这个山泉,以此得名“鬼翻锅”,真亦名副其实吧!
山泉水自山而下,加上雨水冲刷,日积月累就在格针岭这个小村前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沙溪。溪水叮咚潺潺,汇入了八里屯的西河。溪水两岸是养育格针岭人的田园土地,岸边长满野草野花,还有自生的杨柳树、刺槐树和山枣树。小沙溪给这个小山村既增添了秀丽的色彩,又浏览了格针岭人走过的弯弯曲曲的生活之路,也记述了格针岭人的欢乐和苦恼,还记载了这里一代又一代人跨过的漫长的岁月。
时间已到农历戊戌年,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使人难以忘怀的年代。中国的农村从初级合作社一步跨入了人民公社,这一大步,真是一个***,是个破天荒的时代的跃进!中国的农村提前步入一个跃进的年代,一个崭新的年代。
风景秀丽的格针岭,现在是春机盎然,使你醉,让你甜,任你赏。遍山腰的刺槐花香飘十里,满村周围的格针花醉人心扉,溪边、沟边的山枣花让人留恋往返。花儿引来的蝴蝶翩翩起舞,环绕于花丛之间;花丛中的野鸟五颜六色,竞相争鸣。千姿百态的生灵,群芳争艳的生态,好像预感到什么,它们毫无约束地展现自己,似乎害怕再没有它们原生态的明天……
洪家从陈圩子搬到格针岭已是第三个年头,这一家子现在仍是生活的很苦,先是四口人挤在本家看场的一间小草屋子里住,去年在本家爷们的帮助下,在这间场屋的西头用草粘土坯作墙,本家爷们送来几棵干枯了的洋槐树木棒做梁,从山上割下的野荭草作了上盖,又盖了一间小草屋,这下总算宽敞了一些。洪宜章和儿媳妇枣花从野外割些刺荆条,围成一个一人多高的“院墙”,用荆条和刺槐树细杆又做成一个“大门”,这一家子外出就可用锁把这个“小家院”锁起来了。
平安可没忘记花妹给他的那只小狗,他什么不干就最先考虑狗的住处,自己取些木棍和树枝给黑狗搭了个窝,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黑子”,这会儿“黑子”也长大了,就成了“大黑子”。
勤劳之人总会“丰衣足食”的。经过洪宜章和枣花辛勤的开垦,洪家现在像在陈圩子时一样,自己又有了个理想的“小菜园”。洪宜章和枣花利用起早贪黑的时间,把小家院子外边本家用场的剩余的一片荒地一锹一铲的,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整理,种上了一沟一洼的青菜、萝卜、黄瓜、四季豆和韭菜等等,洪家的吃菜问题解决了。
平安向他的同学要来了一些梨树、桃树、杏树、樱桃等果树栽在园头园边。春天到了,洪家的“小家院”别具一格的展现了果花争艳的美好景色。当然,金秋来临的时候,这个小家园更是硕果累累。
洪家人的衣食住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然也在不断的变化。这家人只住着二十平米的茅草屋和木栏栅的小家院子的经济条件是现实,可,现在也要随着形势的需要,一家人的思想境界也必须走向当前化。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现在进入了人民公社,分配原则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该不一样了。上级要求人民群众应该具有“好思想”,财产也好,土地也罢,一切的一切,都是公共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财产、土地、物件,口头馋就是:“大家伙的”,“人民公社的”。大体你不必担心一切,这会儿真是“天下无贼”、“人心无私”了。
格针岭的人烟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从入初级社时的几十户人家,由于社会安定,人气逐年增加;全村现在已经有一百多户人家;人口由不足二百人,现在也增到四百五十多口人。在外地逃荒要饭的漂泊的,都觉得这个小山村日子好过了,都开始陆陆续续返回家乡。
解放初期的那个县现已划归陵海县八里屯公社。
格针岭村属于八里屯公社的赵埝大队领导,这里设了一个生产队,队长是原来的“老村长”叫瞿志金,会计是朱满仓,还有一个队委是余赤红,另配一名妇女干部。
瞿志金虽然年龄不足五十岁,可他身经新旧两个社会,已是非常老练成熟的村领导了,不管是过去村工作,还是现在生产队的事,他管得头头是道,“家”当得合情合理,村民也好,社员也罢,都称他是个好村官。社会的发展迅速,他似乎又有点“不适应”。不可理喻的号称“二流子”的、刁吃懒干滑得像“泥鳅”似的余赤红,人家硬是配给他当他的“助手”,当了“贫协主任”,表现好的思想好的人只因为当年有过历史污点,他们就不能当村干部。可不管怎么说,社员心中有杆秤,瞿志金在生产队里就是“包青天”,余赤红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不言而喻的“潘丞相”。
瞿志金仍然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意愿,在生产队的工作上,他大胆地分配他认为可用的人来管理“机要”工作,仓库保管员,他用了干过几年山匪的瞿志龙,余赤红认为这个保管“本质”不行;瞿志金认为,那是旧社会逼的,他志龙是“劫富济贫”,现在他把生产队的仓库管理得连老鼠也别想从那里盗去一粒粮食。瞿志金又用了他的西邻居洪宜章当了瓜田的“把式”,瓜田每年收入上万元,解决了生产队的所有开支,还能增加社员们的分配;余赤红说姓洪的过去当过“凉家的管家”,瞿志金说他也能给生产队“管好瓜田”。余赤红硬是把个孤身一人的赵傻头推选当“园头”,说他是贫农。社员们一百个不满意。那个赵傻头啥也不懂,只会打水浇园,五、六亩地的一个大菜园子,基本上毫无收入。社员们说,历史问题是该讲,讲不出“钱”来,那又讲什么呢?谁能讲出钱来、种出钱来,俺们大家都拥护他,他就是我们最好的兄弟。
瞿志金还是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他的最大希望就是让格针岭人过上好日子。
生产队的牛栏旁边,建了一个特大的大粪池,每天生产队把社员每家每户的牲口粪,人粪尿,全部按工分论质论价集中入池;又把公家牛栏的牲口粪,猪圈的猪屎尿也集中入池。在这个大池中把肥料沤“熟”了,再运入大田中使用。社员们每天在生产队出勤,按工分报酬,早晚出勤男女工平等——两分;白天男女同工不同酬,男工拾分,女工八分。这样到生产队“分红”时,就按每户肥料、专业、出勤累计工分来分配生产队的粮食、钱款,“多劳多得”,但人口有百分之六十的“基本口粮”,只是抽取百分之四十的粮食“按劳分配”,这也解决了老年、儿童、病弱残等人群的基本口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