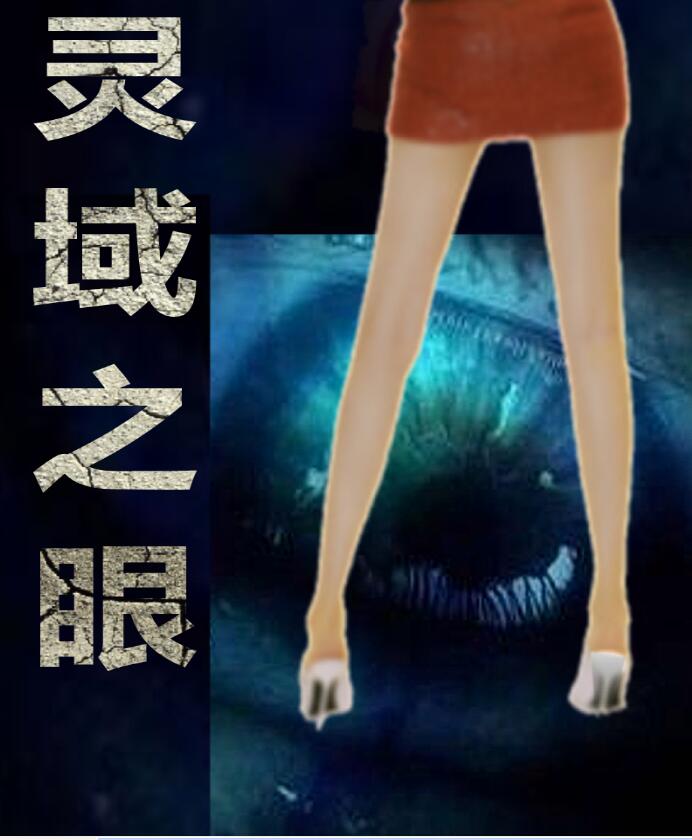【神医急救无名客 虎符难掩天地心】
极光城的城门之上,城主陈道秋站在城头深切地向远方瞭望,他时不时地向身边的侍卫问道:“还没有到吗?神医还没有到吗?”忽然,角楼的瞭望仓之内的兵士大喊:“到了,神医到了,前方三里处有两匹快马,后面一人人擎着一面白底黑字的旗帜,是神医妙手仓公山!”
陈道秋一听,立刻大手一挥道:“开城门,快去派人将神医迎入城里!”众卫士道:“令。”不多时,一队人马,银装铁甲,手持利剑,浩浩荡荡就从城门飞奔而出,快马加鞭,不一会儿就将仓公山接了回来。
陈道秋立在在城门口相迎道:“仓神医一路上颇有辛苦!”仓公山一看倒是大惊,连忙下马,走到陈道秋面前道:“城主乃上卿,我们如何敢让城主屈尊在此相迎啊!”陈道秋倒是满不在意,又说道:“还望神医不辞劳苦,暂缓休息,先与我同去救治一人,那人情势危急,要是去晚了,怕是回天乏术啊!”仓公山一听,神情凝重道:“敢问是谁受了如此急症!”
陈道秋也不答话,直接就将仓公山引入城墙根底下的一座极其隐蔽的宅院之内,一路护卫排开,大道直行,走得飞快。仓公山随着陈道秋进入里屋,只见一位男子瘫卧在床,面色煞白,毫无一丝生气。仓公山立刻走到那人身边,只见他左胸有一道很深的剑伤,直插入心窝,伤口四围有淡淡的绿光冒出,陈道秋道:“这是我极光城的一员大将,近日被奸人所害,剑刺胸口,我虽然用七转还心丹暂时为他保住了性命,怎奈伤势过重,无论城内医师如何施救,都不见起色,还请仓神医妙手回生,保我将军一命。”
仓公山听闻之后,便让陈道秋撤去众人,只留陈道秋和一个端水的小奴,细心切脉,之后又是一阵听胸,望眼,还时不时用一根极细的银针刺入胸口的剑伤之内。一把拔出之后,他举着手中早已发黑的银针给陈道秋看道:“我手里的银针是专测剑气的感气银针,凡是伤口之内还留有剑气,伤口就如同千刀万剐一般,别说是七转还心丹,就是疗伤圣药‘玉壶冰心’,也不可能将他的伤势医好,只有想办法将他伤口之内的剑气吸出,或者直接割去坏肉,让血脉自行流转,只是他伤在心脏,不可除去,只好由外界输送一道真气进入他的体内,先帮他护住五脏六腑,在想去除剑气之法!”
陈道秋一脸茫然道:“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剑气还能留在伤口之内,更不用说将它去除之法了,这可如何是好?还请神医指点!”
仓公山道:“这道剑气不同寻常,极为霸道,所以才有此一出,想必此人的剑术造诣,已经是不再七老之下。”他转头又问,“难道是被某位九剑所伤?”
九国之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由九剑所伤的人一律不准救治,因为九剑乃天下公推的德剑,所持皆为当世之正义,他们不会无故出手,更不会无故伤人,只要九剑一出,必然是惩治天下恶贼,人人得而诛之,又何来医救之说?
陈道秋立刻摆手道:“当然不是,九剑天威,谁人胆敢冒犯?”他细思了一会儿,心里想道:“当然不能让他知道这是云开天工阁阁主欧开所伤,更不能让他知道此人就是行刺蓉王的独孤一剑,得找一个更好的由头来把这事掩盖过去。”然后说道:“此人是我最得力的部下,姓陈,我派他去北疆求购灵丹妙药,不想被玄武国的高手当成偷药的贼人,身受十多处剑伤而归,其他伤势早已完好如初,只有这一处,几乎要害了他的性命!还请神医慈悲在心,定要救下他!”
仓公山听了陈道秋的言语,低头沉吟了一会心思道:“陈姓?难道是同宗?看来道秋公始终不想透露此人姓名,自有他的道理,我看还是救人要紧,九剑是不会枉杀好人的,既然出手,当然也不会放那些恶人一条生路,还有留一些医治的机会。”他抬头对陈道秋说道:“如此,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然后他命人取来药包,又叫众人在空旷之处,铺上板席,将那受伤之人放在木板之上,四周围上幕布,叫众人看守,闲人退散,不准有人打扰。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他双手摊开,那药包之内突然飞出几百根银针,只见他手指来回轻拨,呼吸渐急,只见那几百根针就飞速插入那受伤之人体内,不用一炷香的时间就成了一个“针人”。所有的针都用完之后,他又拿出一把小弯刀,轻轻割开那人的左臂,让那鲜血直流,而那木板之上的人便是没有了一丝血气。
他左手运气,重又将那左臂流出来的血放在手掌之上,用真气拖住,渐渐的一点点黑色的水珠便从血液里凝结而出,鲜红的血液,又被他由心脏的伤口灌入,如此反复九次,终于是在那人脸上看见一丝血气。
他将手掌里的几滴黑水,往地上一扔,只见泥土瞬间发黑,白烟直冒,他又拿来火把,一把把这黑土焚烧了一遍,这才双手运功,将那台上之人体内的银针取出,根根发黑,他用自带的白药布将黑针包好放回药包之内,这才拭去头上如雨的汗珠,走出幕布之外,对着陈道秋道:“我已经用‘百针换血大法’将他的伤口的剑气去除,你可以按照常理来为他医治恢复了。”说罢,已是走路踉跄起来。
陈道秋即刻命人道:“来啊,快去带神医进去休息,等一下我亲自去道谢。”说罢就进入的幕布之围里面,看着稍有气息的独孤一剑,他又掏出一颗“七转还心丹”,送入他的口中,心里暗道:“欧开老兄,只好对不起了,你那云开城的几百年荣耀也算到头了,我这极光城可还是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同一日,蓉城将军府之中,世子孟熊接到蓉王的手谕说:“我儿孟熊,汝既为我蓉国兵马大元帅,自即日起,全权统领蓉国上下所有兵马。特命虎符使将虎符赐送于你,自当亲领大兵,爱国爱民。特许左右手持紫金斧钺,前来蓉王宫听封,接纳虎符。”
手下众人劝道:“以前蓉王和殿下有隙,故命殿下远涉边疆,自从蓉王去国,从云开归来之后,终日躲在深宫,我等皆不知上意为何,此番又将这千般贵重的虎符相予,名为把蓉国大权交于殿下,实则想以此来试探我主的忠心,只是蓉王隐晦,不可捉摸,入宫或恐有变。”
又有谋士谏曰:“我听说蓉王在云开遇刺,是蓉王妃花蕊夫人为我王挡住了那致命一剑,这才得脱,如今这花蕊夫人重伤未醒,只怕是蓉王有求于殿下,此次入宫定然是为了医救花蕊夫人,宫里的庸医怎么比得上我们将军府的大医官,‘千手’阿木铁。”
孟熊却把宝剑握在手中,突然大笑起来,说道:“今日,这就开始了。”然后他招来几名影卫道:“传令下去,马上令所有八虎即刻回城,专诸归位待命,自有大事商议!等到八虎一起到齐,我等就立刻进攻面见我王,接受虎符!”
是夜,就有飞鸽传书传到河山镇外大营,收鸽之人一看,那鸽子浑身紫金飞羽,红喙黑爪,一看就知道乃是蓉城将军府特急密函。那收信之人一拿到鸽腿之上的密书,便一刻也不敢停留,直直就往胡如云的营帐送去,只见帐内三个人影晃动,春声迭起。那人也顾不得许多,立在营帐之外大声一喊:“大帅,有紫金飞羽鸽送机密信到。”
胡如云只一听“紫金飞羽”四字,就一把推开怀中女子,扯下一张虎皮披在腰间,飞步走出营帐,一掌把那送信之人拍死,将那人手中的密信扯开看道:“虽然这密信千万重要,可是你终究是坏了我的兴致。”说罢,便把那密信吞入口中,立即回身,看着又迎上来的尤氏姐妹,胡如云道:“世子有急信,我必须马上起程回去,怎奈良宵苦短,佳人难随啊!”尤稥一把抱住正在摘取衣物的胡如云,娇声道:“我姐妹自然不能跟去,只是大帅何不明日一早再动身,难道我们两姐妹还不如这一纸破字吗?”
胡如云一听,脸色骤变,直接朝着尤稥脸上“啪啪”扇了两记大耳光道:“是去是留,还轮不到你们说话,你们此番进攻河山镇,也别躲在这营帐之内了,我就命尔等暂代我大帅之职,你们一定要身先士卒好做表率!要是有所差池,一定是严惩不贷!”说话之间已经是将青衣长衫,紫金腰带,虎纹长靴,一切冠服饰品,统统穿戴完毕,扔下一枚帅印,就策马扬鞭而去。
尤稥莫名地受了这两次苦打,心内羞愤至极,直等到那马蹄之声听不见了许久,才敢放声痛哭起来,极其悲伤。尤美亦是心痛,轻抚尤稥的玉背道:“好妹妹,你可别再流泣了,咱们虽是苦命,也不一定非要为这狗男人当奴当婢的,咱们的性命自己做主,如今这狗男人不知为何事自己跑了,单单留下我们,明日定要遭那流沙帮的毒手,还不如今夜也收拾收拾,赶快启程,带着众姐妹逃了去。”
尤稥却是止不住的抽泣,点头回应道:“咱们受过的苦还少吗,只是原本以为终于碰到一个可心的人,怎叫一张破纸,就显了原形,还不如那些金银之客呢,本该就假情假意。不像这般,倒叫我动了真心是,此番是更伤心了。姐姐,你莫要管我,你快去通知大家,这里却是不能再待了。”尤美亦被她说得有几分动情,只是淡淡地笑着,泪水婆娑,相拥在一起。
两人商议完毕,便各自穿戴完毕,悄悄出了营门,这几路盗贼各有各的营帐,尤稥尤美一起到自己金雀阁的那几处营帐之内,轻声将众人集结到一起道:“大帅有令,叫我们先撤退回本来地方去。说是要断了那流沙帮的粮草,给他们一个教训!”说罢,就把大帅印往空中一举,大喊道:“连夜出发!”众人一看那大帅的帅印竟然在阁主的手里,无不欢喜地听令,纷纷行动起来。
这金雀阁本是龙首城东边的一处小村里面的小帮会,都是些落魄的女子组成,还有一些着实是混不到饭吃的男子,也跟在帮会之中,做些看门护院的本事,在尤稥尤美的率领下,投靠了蓉城将军府,领了不少的银子,跟在一众真盗匪后面,捡遗拾漏,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好处。只是这一次得罪了流沙帮,又没有了撑腰的主子,为保性命只好逃走。
刚向北走了不到十里路,尤稥就倍感疑惑道:“姐姐,我们要是回到原来的地方,被那些流沙帮的人找到怎么办?我们定是打不过他们的,难道就束手就擒吗?”尤美细想了一会儿道:“妹妹说的是,我们的老窝是回不去了,只好变着道去一个可以收留我们的地方。”这时尤稥便指着西南方向道:“我听说,西南的夜郎城里面有一个姑姑,倒是对我们这些落魄女子照顾有加,不如我们去投了她吧!”尤美一听,赶紧摇摇头道:“从这里去夜郎,不知道要走多少里路呢,又不知道有十几路盗贼在路边等着我们,这太危险了。”尤稥举起手中的大帅印道:“姐姐,你看这个,这是那个狗男人丢下的,有了这枚大帅印,只要我们向西走,过了涪城,到了蓉国境内,便是要粮有粮,要马有马,那个时候,怎么会走不到呢!”尤美看着尤稥手里的印章道:“你说,这是他好心留下的么?要是这样”话还没有说完,尤稥就说道:“要是什么,肯定是那密信之中有些重要之事,比给一帮乌合之众当头领还要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就像扔一块烂骨头一样,把这印扔掉了呗。”尤美叹道:“你是说印章,还是说我们自己。”尤稥眼里充满了恨意道:“我早就看透了这些个狗男人!没有一个有良心!管他做什么,现在我们就靠着这枚印章过活了,不,就靠我们自己过活了。”说罢,就止住众人,领着众人又往西边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