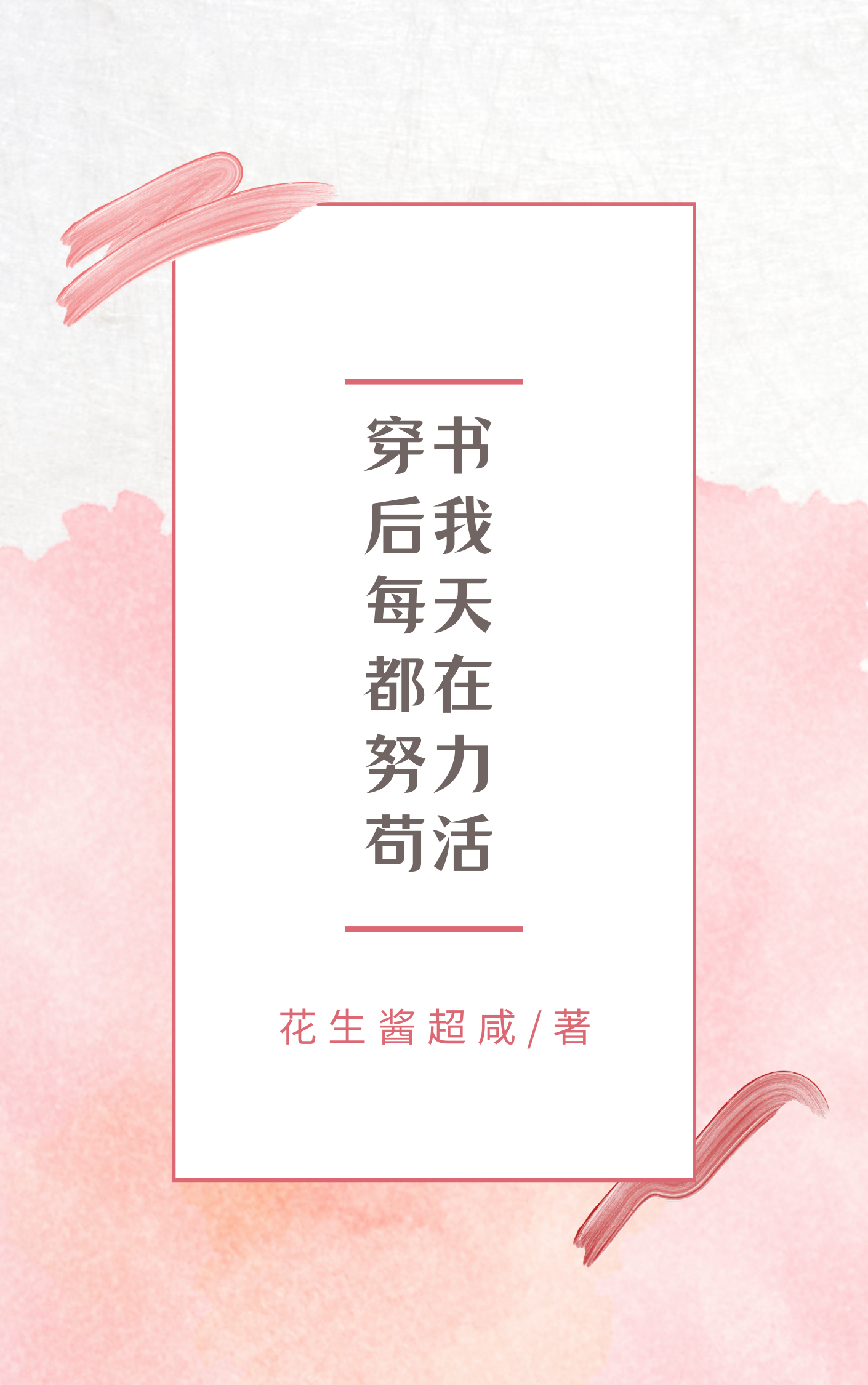“单凭说说就把罪名往下官头上扣,未免太牵强了吧?卫宗主,您当真以为,这朝廷之中,只有你一家独大吗?是黑是白,单凭你一张嘴?太可笑了。”周玉倨傲的一躬身,冷道:“卫宗主虽是下官的顶头上司,但下官也不怕明白告诉您,下官不是软柿子,您若是执意往下官身上泼脏水,下官就算螳臂当车,也要跟您斗上一斗。”
周玉和李德两个人点燃了开矿用的火药,亲眼看见那矿洞和王太医待的房舍坍塌一尽,才敢放心的下山报信儿。知道矿山的账目是死无对证,周玉说话自然干挺直腰杆,理直气壮。
元熙见他说话怪硬气的,心里就萌生出许多反感。朝廷之中,除了太子一党,便只剩下萧容深的和亲王党了。他周玉曾经就是东林州府里的州官,自然也属于旧派势力。
元熙不以为然的哼了一声:“周大人真的好胆气啊。”元熙凛然扫了他一眼:“跟本宗主斗?你凭什么?”
“下官凭的是一个道理的理字。”周玉冷笑一声:“卫宗主在东林开府,无非是想像从前的上官府一样威风,只是如今东林州还有下官的府衙在,宗主觉得我府衙分走了您的权势,心里自然会不痛快,这本是人之常情。宗主看下官不顺眼,下官躲着您便是了,可宗主要是硬要栽赃,下官就算没有底牌,还有这条贱命呢,一定会奉陪到底。”
这话颇为刺耳,连钟妈妈都听不下去了,厉色道:“你大胆!污蔑宗主,知道是什么罪名吗?”
周玉面色一哂:“你大胆!”
钟妈妈一怔,周玉继续说道:“你不过是宗主府的一个奴婢,又什么资格在这里耀武扬威?你不过仗着卫宗主的势力罢了,哼,跟主子同乘王侯品级的赭呢车马,招摇过市。这都不提,本官是朝廷命官,你有什么资格呵斥?本官倒想问问宗主,这个僭越的奴婢,该当何罪?”
“你!”钟妈妈瞪着周玉,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大人,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元熙将钟妈妈拉到身旁,绵里藏针的说道:“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位钟妈妈服侍太子爷多年,可以说是看着太子爷长大的。如果本宗主没记错的话,当年太后娘娘宫中的一个梳头侍女出宫返乡,你周大人可是亲自置办了宅院,毕恭毕敬的把那侍女请进院子里的。怎么,今儿这态度倒和从前不同了?莫非在周大人心里,太子爷不如太后娘娘,不值得你恭敬对待?”
周玉唇角抽了抽:“下官是朝廷命官,怎么会讨好逢迎一个梳头婢女?那必是有人刻意毁我名声,宗主怎么会相信这种市井流言?”
“市井流言?”元熙慢悠悠的把头晃了三晃:“这是六爷说的,怎么?周大人的意思是,六爷在诬陷你吗?”
周玉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一点儿血色也看不出了。他的主子萧容深是亲王,六爷也是亲王,而且是皇后嫡出的亲王,身份自然比他主子还要高贵许多。周玉不敢说话太放肆,只能把满腔愤懑憋在心里。
钟妈妈见他成了一个软柿子,也转过身去,不屑的哼了一声。
“欺软怕硬。”她嘟囔完,抬眼往上山看,也不知道涂博安挖得如何了,能不能救出几个活口。
涂博安在带兵在矿洞外挖了两个时辰,奈何山体塌陷的太厉害,巨石把矿洞口都堵死了。涂博安觉得头皮发麻,矿洞就那么巴掌大的空间,里面能有多少气儿?百十来个人陷在里面,就算不被砸死,过不了多久也会被憋死。
“大人,那边那个砖瓦房已经全部挖开了。”一个士兵跑来报告。
涂博安三步并作两步的冲到瓦房的废墟前:“可找到王太医的尸骨?”
士兵们摇摇头:“这房里没有人。”
涂博安打了个激灵:“怎么会?”
士兵们七嘴八舌的答道:“回涂校尉,确实没有人,这房子虽然塌了,但却不至于把人砸成粉末儿吧?属下们翻了两遍,连丁点儿人影都没有。”
涂博安有些恍惚,他揉揉太阳穴,人生的大悲大喜来的猝不及防,涂博安咧开嘴笑了起来。这么说,王太医还活着?
涂博安伸手点了点:“派五十个人去山上搜,无论如何,也要把王太医找到!”
涂博安这五十个人沿着一些不起眼的小路往山下走,冷不丁撞上了周玉设下的埋伏。周玉派来埋伏的衙役们没有接到任何撤退的命令,还都傻傻的蹲在路边的草颗儿里。刚才山摇地动,这些人还不明就里,片刻间就看见五十来个身穿甲胄的人从山上下来。衙役们见状,自然觉得是周大人出事了,纷纷跳了出来,拔刀相向。
涂博安手下的府兵也不是吃素的,三两下就把这几个废物点心缴了兵器,按在地上。
“土匪啊?怎么办?”
“杀了算了,打家劫舍的东西,留他何用?”
“也好。”
一句“也好”说完,十几个士兵纷纷扬起佩刀,被按在地上的衙役们吓了一跳,忙亮明身份:“谁是土匪!我们都是东林府衙的衙役,你们敢动手?”
“衙役?胡说八道!衙役怎么穿成这样?”
被按在地上的衙役不服,从怀里掏出各自的腰牌。
“还真是东林府衙的衙役?”涂博安的手下有点发懵,但他们毕竟跟了涂博安许久,知道校尉的脾气。涂校尉眼里揉不得半点儿沙子,要是知道东林府衙的衙役们办成劫匪在半路埋伏,肯定是要大发脾气的。涂校尉最看不得这种蝇营狗苟的事,也以铲除杂碎为人生乐事。不管怎么说,把人带回山上,交给涂校尉处置就对了。
这五十个人便分成两拨,三十个人继续搜查王太医的下落,二十个人则负责把这些衙役押解到涂博安面前。
果不其然,涂博安一看这些假土匪,气就不打一处来。一脚踹倒一个还觉得不过瘾,破口大骂:“一群下作的东西,朝廷给你们俸禄养着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办成土匪鱼肉百姓的!”
涂博安骂完,忽的想起他们是周玉的手下。敛去怒容,浮现出些许欣喜。那几个衙役揉着被踹得生疼的肩膀,莫名其妙的望着涂博安,心想这个涂校尉莫不是个神经病?一会儿阴一阵晴的。
“校尉大人,这几个人怎么处置?”
涂博安哼了一声:“把他们押到宗主面前,宗主自有裁夺。”
刚从半山腰爬上了,现在又要爬下去,几个府兵累得两条腿儿都发木,但涂校尉发了话,他们自然不敢有半句抱怨。涂博安勾勾手,甩了块五两的金锭过去:“你们今儿个有功,拿去打酒,回府后,本将还有重赏。”
……
周玉望着自己府衙的衙役们,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自己聪明一世,怎么会犯这种顾头不顾腚的错误呢?自己的衙役冲撞宗主府,不就等于说他周玉举兵反叛朝廷吗?
这个罪名可不轻,周玉咳了咳:“你们几个好大的胆子,竟敢假扮匪徒袭扰百姓?该当何罪?”
几个衙役愣了愣:“大人,不是您要我们?”
“住口!”李德喝道:“你们几个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情,还敢污蔑大人?”
周玉阴沉着脸,本以为自己手下的衙役能跟他有点默契,一头认罪,一头搪塞,这事情就能蒙骗过去。谁成想他们竟然口无遮拦,差点把自己供出来。
几个衙役一听这话,心里更加慌乱了,连连向周玉磕头求救:“大人,大人我们可都是奉了您的命令啊,小人家中还有妻儿老小,小人是冤枉的!”
钟妈妈掩口笑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周玉往元熙处看了一眼,见她并没什么表情,忙上前一拱手道:“宗主,下官实在不知情,这些个衙役做事不成体统,从前混赖惯了,下官从前糊涂,还替他们遮掩,但如今既然冲撞了宗主府的人,那就是以下犯上,违逆朝廷,下官再也不敢欺瞒了。这些人交给宗主,请宗主定夺。”
元熙看也没看周玉一眼,只是摆摆手,示意自家府兵把这几个衙役带下去。
“周大人,你也知道这是违逆朝廷?”
空气似乎凝滞住了,周玉吞了吞口水:“宗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该不会真的相信几个衙役的胡沁吧?”
“为何不能信?”元熙转过身,厉色望着他:“东林府衙离矿山有几十里路,这里的百姓们都穷的叮当响。衙役们就算是欺压百姓,也不会舍近求远,跑到这个地方来吧?不是你周大人的指使,谁相信啊?”
李德见周玉的气势越发减弱,忙上前和稀泥:“宗主,周大人为国为民一直忠心耿耿,您不能因为这几颗老鼠屎,就把周大人这一锅好粥给端了吧?宗主若是不信,大可以把矿山上的百姓都叫来,听听他们口中的周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元熙冷了李德一眼:“周大人是什么样的人,本宗主再清楚不过了,又何须听别人说?再者,衙役的话是一面之词,难道百姓的话就不是一面之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