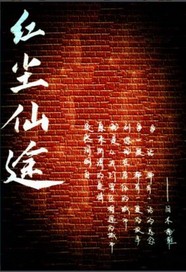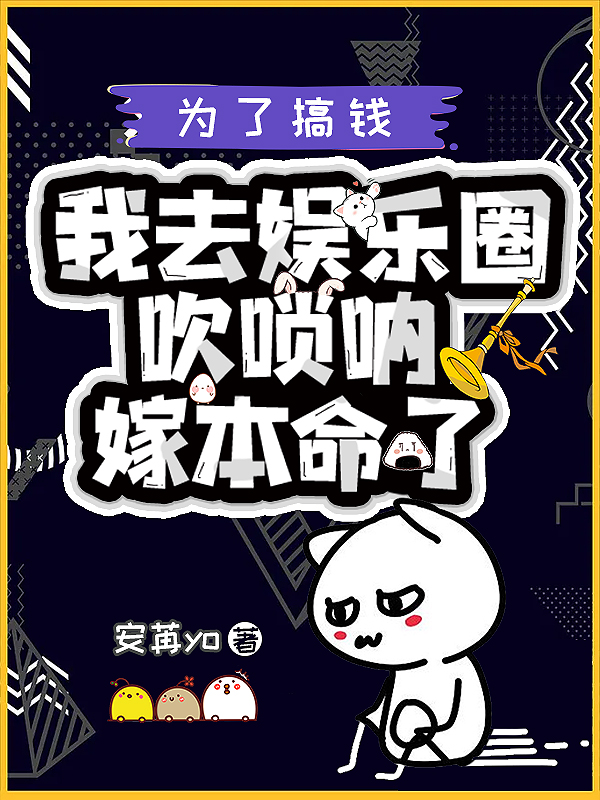午时过后,宗主府的八百多府兵便把矿山围了个严严实实,其余二百多人奉命查抄东林州府。元熙缓缓跳下马车,持盾牌的甲兵忙上前掩住。
宗主府的校尉姓涂,名博安,是容湛从新军里提出来的。这人二三十岁的年纪,却练得一身好武艺。在东林新军训练的校场,他曾一人独挑六人,深受容湛的喜爱。这次东林新军全部开拔到归云州与吕国作战,涂博安本也想跟着去,但容湛却执意把他留下了。
涂博安挎着一柄宝剑,仰头望山上瞧,心里挺憋气。这小小的一座矿山,也值得这般兴师动众吗?不过是抓一个贪官污吏,至于出动上千人吗?真正的战功都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像他这般,大兵压境去对付一群劳工,哼,胜之不武。
涂博安见元熙下来,便把脸上的不满收了去,大步跨过来,冲元熙一拱手:“宗主,什么时候攻山?”
元熙上下打量了涂博安一番,唇角微微扬起一道难以察觉的弧度。难怪容湛不肯把他带上战场,说到底,还是太沉不住气。
“涂校尉不要太心急了,还没怎么着呢,便要攻山,出师无名啊?”
涂校尉抿着嘴,心里老大个不乐意,出师无名?那又何必把府兵调过来呢?
“那咱们现在按兵不动?”涂博安问道。
“派两个人上山去,叫周玉带王太医下来回话。”元熙轻描淡写的回答道。
“哦。”涂博安将头上盔甲褪下,一股热腾腾的白烟从头发里蒸腾出来。他勾勾手,叫过两个人:“你们俩,按宗主说的办。”
那两个人对视一眼,行了个军礼,便顺着山路往上走。山路崎岖不平,还有周玉早早设下的埋伏,这两个人自是有去无回。山下,元熙和涂博安等人等了两个时辰,仍不见动静,心里觉得不对劲。
“按道理,两个时辰也该打个来回了,怎么还不见回来?”涂博安把剑鞘摆弄的卡啦卡啦响。
钟妈妈警觉的望向元熙:“莫不是让周玉给扣下了?”
“有这个可能。”涂博安仓啷一声拔出佩剑:“末将这就派人攻山!”
元熙只看了他一眼,还没来得及说话,便觉得山顶上一团红硕的东西倏忽闪了一下,顷刻间,山摇地动,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众人吓了一跳。巨石沿着山脊滚落下来,撞击到地面的岩石棱角,迅速碎裂成更多的小块,再从不同方向陨落。碎石从四面八方毫无征兆的滚落下来,砸伤了几个拿盾牌的士兵。随着巨响,八百个士兵似同时遭到了撞击一般,左摇右摆,涂博安将佩剑插在地上,勉强站稳身子。
钟妈妈吓了一跳,忙去扶住元熙:“主子小心!”
涂博安心里咯噔一声,忽而又那么一丝慌乱,但很快稳住了心神。
“是矿洞爆炸了?”涂博安自言自语的问道。
涂博安忙点了几十个兵,循着山路往上走,想靠近矿洞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士兵们走出了不到半里路,便看见两个灰头土脸的家伙嘴里嚷嚷着什么不清不楚的话,像疯子一样从山顶上冲下来。那两个家伙衣衫褴褛,露着肉的地方都被血呼住了。
几个府兵便将这两个人带到山下,送到元熙面前。
钟妈妈低头看了这两个人一眼,一个是周玉,另一个是他手下那个叫李德的家伙。钟妈妈不禁皱皱眉,望着元熙,觉得莫名万分。
元熙凝眉望着他们:“发生什么了?”
周玉嘴里呜呜咽咽的,半晌才嚎啕着说出一句完整话:“矿洞,矿洞坍塌了,劳工们还在里面。”
这话说完,周玉和李德两个人便相继捶胸顿足的嚎哭起来。涂博安愣了愣,万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他一把抓起周玉,也顾不得周玉身上的伤口,引得周玉丝丝哈哈的痛呼。
“我问你,王太医呢?”涂博安吼道。
“王太医,王太医他喝醉了酒,没跑出来,怕是被乱石砸碎了!”李德说罢,眼泪大颗大颗的落在胸前,左右开弓的抽起耳光来:“都是小人的错,小人不该拿那陈年好酒出来,若不是如此,王太医便能跑出来了!”
涂博安嘴角激烈的抽搐一阵,一把掐住了周玉的脖子,他的指节随着手上的缓缓用力而渐渐发白。
“王太医死了,那你为什么还活着?”
“我……”周玉艰涩的说道:“将军,谁不想活?难道我活着也是罪过不成?”
“涂校尉,放开他。”元熙淡淡的吩咐道。
“宗主!他们害死了王太医!您难道还要放过他吗?”涂博安涨红了脸。
“我说放开他!”元熙瞥了涂博安一眼。
涂博安悻悻的松开手,将周玉推了个踉跄:“算你小子走运!”
周玉猛咳了一阵,捂着脖子,大口大口的穿着粗气。周玉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谢宗主开恩,谢宗主开恩!”
“周大人,你刚才说矿洞怎么了?本宗主没听清楚,劳你再说一遍。”
“坍,坍塌了,矿洞坍塌了!”周玉磕磕巴巴的说道。
“好好的矿藏,怎么会突然坍塌?”元熙冷然问道。
周玉在脸上摸了一把,掩盖了慌乱的眼神:“宗主,别问这么多了,快派人去救人吧!”
“涂校尉,你现在立刻带人上矿山,务必要找到活口。”元熙厉声命令道。
涂博安一拱手:“领命。”
先前还满心无趣,现在整颗心却是悬在半空,矿山上几百条性命生死未卜,涂博安想想便觉得心乱。还有王太医,他们两个交情不错,称得上往年知己,若是王太医真有个三长两短……涂博安一想到这儿,心里就七上八下的。将八百府兵全部派上山,只留下五个人保护元熙的安全。
周玉见涂博安走了,同李德对了对眼神,悄咪咪的站在元熙的车轿旁,一言不发。
想着王太医好好一个人,一夜不见,便死的这么惨,钟妈妈心里不落忍,冲周玉狠狠剜了一眼。周玉自然知道钟妈妈的心思,束手而立,道:“钟妈妈,我知道您老人家和王太医交情深厚,可谁的命不是命?王太医去了,下官活着,可活得绝对不苟且,您不至于用这种眼神看我们吧?”
这话音儿里带着莫大的讽刺,一个是老太太,另一个是半百的中年人,才刚见过几面,哪里就交情深厚了?男女授受不亲,天悬地隔的两个人,交情若是深厚了,他们两个人岂不是有情况吗?
钟妈妈一时语塞,轻轻啐了一口,把头扭了过去。
李德冲钟妈妈哼了一声,原来也是个色厉内荏的坯子,这就接不上话了?
元熙瞥了周玉一眼,淡然道:“周大人能活着固然好,但京城有句老话,不知你听说过没有。不做亏心事,不算命短长。意思是,人没有做缺德事,就不用担心活不长久。”元熙徐徐转过身,凛了周玉一眼:“苟且不苟且,还要等涂校尉在矿山上清查以后才能定论,周大人还是不要把话说的太绝了。”
周玉滞了一下,钟妈妈抢白他们,他倒是可以还嘴,但元熙是东林宗主,他的直系上司,面子上来说,他是绝对不能还口的。
周玉只得将手拱了拱:“下官明白,请宗主放心,微臣绝不是苟且之人,下官这就回去,将府衙中大小官吏都叫来,组织家丁衙役上山救人。”
“不必了。”元熙漠然望着他:“东林府衙已经被本宗主的府兵看管起来,矿山上有涂校尉的八百精骑,救人足够了。”
“看,看管?”周玉身子颤了颤,茫然的望着元熙:“宗主这是何意?”
“何意?周大人难道不明白?”元熙微微垂下眼睑,不屑的望着周玉:“周大人,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戏码,演上一次便够了,若是演的多了,只会让人生厌。”
怎么,这么快就要秋后算账了吗?周玉吞了吞口水,脑袋还有点儿转不过弯儿来。好吧,既然如此,那他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周玉振作精神,正色道:“宗主,下官不知道身犯何罪,要劳动宗主大驾?”
元熙冷笑一声:“周大人,矿藏无缘无故的爆炸,究竟是什么缘故?再者说,你用东林府尹的手令,去调我宗主府的账簿,是不是以下犯上尊卑不分呢?光是这两条,便能治你一个渎职犯上之罪。”
周玉沉默了一阵:“把崩塌说成爆炸,看来,卫宗主是非要治下官的罪不可了?”
元熙冷漠的望了他一会儿:“是我要治你的罪吗?”
周玉不以为然的笑了笑:“不是吗?除了宗主您,偌大一个东林州,还有谁能治下官的罪呢?”
“周玉,你给我听好了,你犯的是国法,可不是我要治你。”元熙冷笑道:“你以为本宗主好糊弄吗?爆炸就是爆炸,扯什么崩塌?卫家商号在吕国同官府合作采矿,火药炸塌的山什么样儿,我再清楚不过了。”
周玉咬咬牙齿,含恨望着元熙,若不是京城和亲王府离得太远,他未必就没有办法对付她,只是还要听和亲王的意思,这才耽误了最佳时机。
“周大人,你不觉得你的谎言应该重新编一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