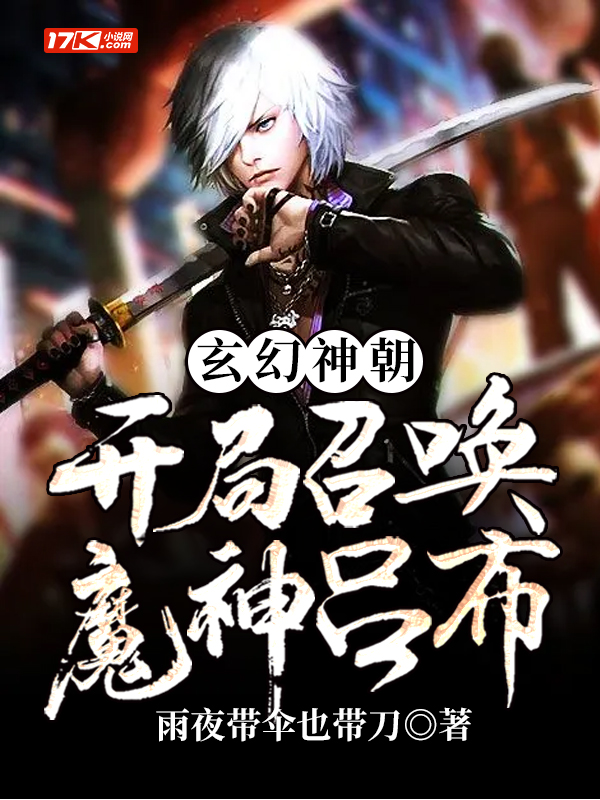那两个獐头鼠目的年青人从城楼上露出了头,伴随着一阵恐慌不已的战栗,那个有着一双贼忒兮兮眼睛的汉子说话了:“李鸦儿,你……你……你好大胆,我幽州与你有何仇?你要兴兵来犯?”
虽然他人长得不怎么的,但是这番话说出来倒也有一番义正严词的味道在里面,但是他要面对的不是一支会和他讲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军队。他要面对的是一帮缺衣少食,为了吃上一口饱饭而不惜奔突万里来到他幽州抢粮的一帮强人!
李克用用他的独眼瞥向了城楼上的那两个身着明光铠、内穿锦袍的年轻小子,发出了一声嘲笑的鼻音,说道:“我沙陀人与你幽州现下确实无冤无仇,但是你们也知道的,北方大旱,我沙陀人所在的几座城池都已经断粮好几天啦,难道公子你不应该可怜可怜我们这些下等民么?”
朱友文倒没料到李克用也会这样的口才,暗地里笑出了声,原来能做上沙陀首领的,还真都是那么不简单呢!
那两个站在城楼上,四周围的都是些彪悍的士兵的两个年轻人,其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个满身符纸的奇怪青年,他晃了晃他的小脑袋,发出了一阵怪异的笑声:“咯咯,你们沙陀人倒还真的是恬不知耻呢!哼哼,想要抢我们的粮草,那可要看看你有没那种实力呢!来人给我架上!”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数百个健壮的汉子推出了好几百张机器,朱友文在看到的第一眼就被吓坏了,一句话脱口而出:“弩机?”
这种代表着冷兵器时代里最为精良、杀伤力最大的兵器有着一个用木轮组成的底座,可以方便地进行移动,而底座的上面则是由好多个精密的本头零件搭建而成的弩机的本体,一张张由猛兽筋制成的弓弦上被好几个弩手用巨大的力量拉了开来,一支支足足有一人长短的巨箭已经被搭在了弦上。
看着所有沙陀人都露出了惊慌错乱的表情,刘守文又开始咯咯咯地怪笑起来,一面讥笑道:“瞧,彪悍的沙陀人也开始有害怕的表情了,嗯嗯,老哥,你说我们捉到了他们的头头是生炸了吃呢,还是油煎了吃?反正现在粮食紧缺,我想要是吃人肉的话这些肌肉结实的蛮子倒是很不错的选择呢!咯咯……”
站在他身边的那个贼眉鼠眼的年轻人也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嗯,老弟这个想法不错,要是留他们活口多的话,我们还可以吃上新鲜的呢!”
站在古战场里的朱友文望着城楼上那两个嚣张之极的两个小子若无其事的在谈论着吃人肉如同在说着吃狗肉吃猪肉一般,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心说总算知道古代里这些人变态之处了,想到了自己曾经的义父,那个城府无比深厚、心底异常歹毒,曾经倍受黄巢信任的人,曾经可能也在黄巢的命令之下吃过人肉,不禁又开始恶心了起来……
李存勖看着身边的朱友文脸上神色瞬息万变,于是便走到他身边轻声问道:“义弟,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么?”
朱友文摆了摆手,说道:“无妨,只是有些紧张罢了!”
李存勖以为他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攻城战而感到紧张,不由地哈哈哈地笑了笑道:“想当年,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也如你一般紧张,但是后来在我父亲的呵斥之下终于硬起了心肠动手杀了第一个人,这才真正体会到战场上的冷酷和快乐!唉,什么也虽说了,你会明白了!”说完拍了拍朱友文的肩,这是一种男人表达友情的方式,朱友文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没有来到这个时代之前的那帮狐朋狗友们,大家曾经也是这样年轻过,大家也曾经这样荒唐过,快活并痛苦着,不知道明日到底在何方……
但是一转眼间自己就已经如梦魇般地来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最为复杂的社会里了,他多么想如果这一切都是一个梦,一个你醒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的梦,什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都不在回来,一觉醒来,又会见到曾经的那帮死党,那些也会用力拍着自己肩膀说着脏话的兄弟!
虽然眼睛有一点点红,但是朱友文还是没让李存勖发觉出自己的异样,他缓缓地拔出了曾经的“义父”赐给自己的那把用上好材料打造的长剑,缓缓地吟诵起李白的那首《侠客行》诗句:“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
声音是那样的雄壮,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苍凉,他的声音传了出去,他手下的那个千人队听见自己的将官竟然在开战之前呤咏起了诗句都是惊讶不已,粗通文墨的李存勖从慷慨激昂的诗句里听出了悲壮之意,不禁对自己的这个义弟在开战之前吟咏起这样豪迈的诗句充满了佩服!
整个千人队在千人长朱友文的带领之下开始吟诵起来,燕赵大地之上充满了之种慷慨悲歌之音,城楼上的幽州军听见一部分沙陀人竟然在开战之前念叨起了什么,仔细一看,竟然又发现吟咏这些诗句的兵士们个个脸上充满着悲愤难耐之意,个个目龇欲裂,怒发冲冠,仿佛对人间大地的种种不平种种黑暗有着莫大的仇恨!
幽州兵人才感觉到了恐慌,因为幽州人在这些人的脸上没有看到过多的恐慌,有的都是悲愤,那是一种发自于内心,充斥于整个战场之上的斗气,没人有怀疑这些沙陀兵的战斗力,他们才是战场上的骄子!
一段激昂悠长的牛角号声响起,围住幽州四门的沙陀各军都开始了攻城前的准备,尤其是颇为精锐的李克用麾下的黑甲军,一匹匹健硕的战马都披上了甲胄,马上的健儿更是全副武装,只露出了森森的两只眼睛。
李克宁、李存霸各帅部曲,麾下的精锐步军和弓军也各自拿出了自己的攻城利器,一座座由朱友文想出来的“车盾”已经在先前被架在了前面,车盾上蒙的一层又一层厚实的硬牛皮毫不掩饰地说明了它的防守能力!
而那些攻城利器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有专门用来破城门的攻城锤、有专门用来射敌的床弩,虽然比之于幽州人那先进的机弩要落后了一大截,但是这已经是算是沙陀人最高的科技水平所在了,威力自然也不容小视。
城楼上的刘守光、刘守文兄弟看到沙陀人竟然还不知好歹地挥军攻城,齐齐冷笑一声,命令手下的军士全部架起了机弩,发散着寒光的箭头无疑在告诉着沙陀人攻城的后果,但是令这兄弟俩惊讶的是,随着李克用部发出了最后一声短促的号角声,沙陀人开始攻城了。
守城军开始以弩机相迎,一支支硕大的弓箭携带着巨大的威力向着沙陀人来攻的各个方面呼啸而去,朱友文看着那一支支弓箭在他所设想出的“车盾”之上被阻拦,终于枪了口气,但他也知道,这样的盾并不能抵挡住代表着这个时代里已经登峰造极了的弓弩制造工艺所造出的机弩,只要能支撑着沙陀人渡过护城河那也就代表着已经成功一半了,形势颇为危急,朱友文跟着李存勖的一声呼喝,一展马缰,人已如流星般箭射而出,能不能成功,来不来得及只能听天由命了,是死是活,看此一搏了!
沙陀人的四门攻击队开始发动,马军的先进最快,携带的车盾也是最多的,每个硕大的车盾由着最前面的好几个十夫长所携带,后面紧跟着的是每队的将领,再后面便是疾驰着的马军大队人马,再往后面就是一些人数较多的步军和弓兵了,这些人可就没有那么好的命运了,他们所携带的车盾也是最少的,每阵箭雨过来,他们的队中总能死伤好大一片,而且被那种威猛的弩箭所射中的话,基本上就是代表着你的丧命了,死状基本都是惨不忍睹,但是战场之上唯一存在的念头就是前进前进,那些被射死的军士刚一倒地,后面就又会涌上更多的士兵踩着他们的尸体而冲锋。
幸运的是,朱友文看到在车盾的掩护之下,马军损失尚少,等到他们奔袭到城下之时,那些机弩已经不能再伤他们分毫了,奔到城下他们就开始了攻城,各个攻城之利器像不要钱似的砸向了城楼之上那些刚刚还在耀武扬威的守城军士,很快的,人数远远少于来攻沙陀人部队的幽州渐渐已经没法顶住攻势了。
尽管还有一阵子的落石、木檑之类的打将下来,但是那已经不能左右战场局势了,死伤甚众的沙陀人将会以他们的性命替他们那些惨死的战友们报仇雪恨。
毕竟不是和沙陀人是塞上的精英,这些缺乏锻炼,整天游手好闲的关内兵基本上档不住沙陀人的几波猛攻,四门之上都已经出现了裂痕,刚刚渡过河的,死伤无算的步军和弓兵也已经各就其位,庞大的攻势让幽州人的守城信念毁于一旦,城楼之上,刘守光两兄弟正在商量着最后的对策,胆小如鼠的刘守文正在疯狂的抱怨他那正在定州的老爹为何要自己城池不保而跑去强占人家的城池,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随着东门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个匆匆忙忙赶来的传令官大声报道:“报二位公子,东门已被沙陀人攻陷,请地位公子速速上马,让臣下保护您退避沧州!”
刘守光毕竟要比他哥哥胆子大点,犹豫道:“这样恐怕不妥罢?若我等撤离此城,那父亲岂不要以罪杀我们么?”
刘守文急道:“啊呀,我说弟弟唉,都什么时候了,那些个沙陀蛮子杀人可是不眨眼的,我们不离此城照样也是被他们杀,再说了我们是父亲的亲儿子,他怎么忍心杀我们呢,就快点逃吧!”
刘守光摇了摇头,叹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逃便逃罢!”
城外,沙陀人大队人马已经攻破各个城门,纷纷进城了,正在满城满街地搜寻刘守光刘守文兄弟二人呢。
幽州,这座北方重镇终于陷落在了沙陀人的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