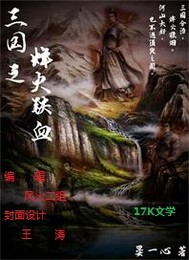为了不引起怀疑,高班福交待完侯三之后,为了不落人口实,就立即赶回了牢房里,径直从狱卒们平日里藏酒的柜子里,随便取了一坛酒:“那高升酒肆的酒赶巧今日卖完了,真晦气。”
一面掩饰着出去未买酒的事实,一面又期盼着何府快快回信,看这样子里边现在关押着的那李锦琴怕是要遭受不住了,要招了,这样的话势必会对何仲伯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的,万一没扛住,说了些不该说的话,那岂不是要连累一大片人倒霉。
现在牢房里面守卫森严,高班福也是有心无力,只期望那侯三快快将消息传送到位,何焕公子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就算是最后没能保住何仲伯,这给他通风报信,他何焕岂不是又欠某一个大人情,日后少不得好处。
高班福那厮越想越起劲,手里拎着一坛酒又来到了女监室,看到衙门里的书办先生已经写好了两份口供了,用眼睛假意随便瞄了几眼,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高班福将酒坛子放在余去非的面前时,女监门外有一狱卒连滚带爬,神色慌张的跑来禀报:“不好了,余大人,那何仲伯不知何故方才突然暴毙了。”
“什么?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余去非确实未曾料到这伙贼人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看来这牢房里还有他们的眼线,不然怎么知道何仲伯关押的确切位置。
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余去非即将要撬开李锦琴的嘴巴时,即将要坐实了何仲伯罪名的时候却突然暴毙了,看来这里边的文章是越来越大了。
这趟水是越来越浑了,这帮人之所以这么着急的要杀人灭口,说明他们心里边感觉到害怕了,说明余去非抓住了对方的七寸。
余去非不敢大意,赶忙派人将事情火速向赵构禀报去了,何仲伯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创伤面,脖子上也没有勒痕,余去非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异样。
赵构接到了消息后,与康履等人立即骑马匆忙的赶到了牢房:“余大人,什么情况,好好的怎么会突然间暴毙呢?”
“估计,有人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将对躲在暗处那些人产生不利,才痛下杀手,弃卒保車。不过这只是据下官观察猜测分析得出的结论,具体的死因还有待仵作勘验之后才能确定。”
赵构走进关押何仲伯的牢房,先是从地上环绕了一周,也并未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只是在这潮湿阴暗的牢房之中,那铺垫的稻草里因连日来未更换干草,混杂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正当赵构要离开之际,左脚无意中踢到一个瓦碗,是平日里牢房里用于给烦人盛水喝用的,想起前世中在武侠小说里经常会有的那么一个桥段,某个轻功了得的人从屋顶顺个直线到地上,然后用根细竹管将吸好的水喷到线上,让重力的作用将水滴落到碗中,而这水是被下了毒药的。
赵构又抬头往屋顶上看了看:“让人到屋顶上去看看,这个位置的瓦片是否有松动过的迹象。”
那余去非也是脑袋瓜子活泛之人:“国公爷你是说,他是被人下药毒死的?那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赵构现在也还只是猜测,还不能最终确定。
余去非此时看向赵构的眼神不禁又多了几分崇敬。
这时爬上屋顶的两名狱卒回话道:“国公爷,真神了,这上头有两片瓦确实有被挪动过的痕迹。”
“行了,那你们下来吧。”
又转过头对余去非道:“你要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下去。此人必定是一个轻功了得之人,不然当着你们的面在你们的头顶上行走,竟然没有一点动静,不仅如此此人还是一个用药的高手。”
余去非点头称:“是,卑职一定尽早将此人抓捕归案。”
赵构出了关押何仲伯的监狱门,不经意间发现其中的一根门柱上明显有用锋利的锐器所刻画下的痕迹,赵构凑近一看,那上边赫然是“我来也”三个字。
来人挺猖獗的,还敢留下名号,这是赤裸裸的公然向衙门叫板。
叔可忍婶不可忍。
“余大人,赶紧去查查这个‘我来也’是个什么来头,这是在公然的挑衅,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里。”
这是继在北方叶竹隘分别以来,南下之后,童二与诨号李铁枪李全初次见面,二人选在一处僻静的小酒肆见面。
童二开门见山:“看来李兄又是在江陵接到大买卖了,不然怎么现身于此。”
李全带着江湖人特有的狡黠,又有点半戏谑:“彼此彼此,想来童大总管你也是了。怎么我到哪里,哪里就都有你。”
“你——”
童二还要向李全探听消息,虽然很是气愤,即便是脖子上青筋凸暴,也还是忍气吞声:“江陵府监狱发生的囚犯被毒杀案子,是你李大侠的手笔吧?”
李全大惊失色:“是吗,请问童总管哪只眼睛看到的呢,我还正想说那是您的手笔呢。”
童二端起手中的茶杯,浅浅的抿了一口茶:“你忘了,我们的眼线无处不在。”
李全不听童二扯闲篇,如果童二果真确定是他李全干的话,就不会坐在这里与他喝茶了。这只是为了试探,那何仲伯的确是李全毒杀的,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是李全认为何仲伯这个人渣死有余辜。
“如果童总管没有别的事情的话,那在下就告辞了。我义兄胡青云前次相见之时,还心心念念的吩咐在下,不可直接与您接触,哦,对了,待会儿茶钱你付哈。”
就这样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时间过去四五天了,案情毫无进展。何仲伯一死,现有的所掌握的线索就全断了。
远远躲避在汴京城府中的李昌宁,自从犯了案以后,一路彻夜从江陵府策马狂奔回汴京城,心里也是怕的要命,就怕哪一天衙役们上门来抓捕他。
这几天一直老老实实的待在府中,可以说是足不出户了,与往日的那些在汴京城的一起耍的公子哥们也断了往来,这完全不是李昌宁平日里一贯的作风做派,事出反常必有妖。
李昌宁的娘李梅氏,还以为这儿子如今转了性,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整日抱着本书端坐在书房里。那是李梅氏没有进的书房里来,看看李昌宁手中读的是什么书?——《柳三变词集》。
这日李甫下朝后,又询问起他那个宝贝儿子李昌宁来:“怎么一进门没见人呢,是不是又跑到外边鬼混去啦?”
李梅氏冲着李甫就来了个白眼,“近日昌宁乖巧的很,躲在书房里用功,大概是开窍了,准备来年的科考。”
李甫一副跌掉下巴的吃惊表情:“果真如此?”
自己的儿子那是什么揍性,他这个当爹的还能不清楚,若果真能改邪归正自然是极好的。
但话又说回来了,人的秉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事出必有妖。不行,得当面问清楚来才能放下心来。
“管家,这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你去书房把少爷叫出来一起吃晚饭吧。”
管家李寿听了李甫的吩咐后,面露难色却迟迟不挪动脚步。
李甫看出不对劲:“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去叫少爷了吗?”
管家李寿稍稍抬头看了看李梅氏,只见李梅氏正满脸愠怒的瞪着自己,吓得李寿刚刚要吐露出来的话又活活的吞进了肚子里。
李甫看了夫人一眼,就知道她坏了事情,可是李甫也是无可奈何,李甫向来是个妻管严,当初李甫还是个穷秀才的时候就嫁给了他,要是当初没有李梅氏这个贤内助,也就没有李甫今天的高官厚禄了。
于是李甫挥了挥手,示意李寿退下去。
李甫改变了策略,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李甫知道她这个夫人是吃软不吃硬的主,于是李甫准备了一箩筐的好话想要向李梅氏献媚。
“夫人,你须知,这慈母多败儿,这些年你看看宁儿,成天过着游手好闲的公子哥生活,整天做些下贱的营商的算计活,须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钱赚的再多,没有个官身护着,那也迟早是要为他人做嫁衣的。
夫人也出身耕读之家,岳父大人不也从小教授你熟读四书五经,若夫人不是女儿身的话,以夫人之才华,为夫也不一定敌得过啊。”
一席话说的李梅氏怪不好意思的,是啊,那些大道理李梅氏哪能不知道呢?可是,一旦转变为母亲的身份后,李梅氏就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就将那些圣人圣言抛诸脑后了。
为免李甫再婆婆妈妈的唠叨下去,李梅氏适时打断了李甫:“好了好了,老爷你莫要再说了,你看,饭菜都凉了,奴家知道错了,以后尽力避免就是了。”
李甫也知道今天说的有点多了,再说下去的话晚上夫人又不让上床睡觉的话就糟糕了。李梅氏也已经难得的服软认错,算是给了李甫一个台阶下,得了,见好就收吧。
李昌宁好一会儿才耷拉着脑袋,从书房里出来了,一见到李甫心里边就有点发虚,在整个李府,也就他爹李甫还能镇得住他。
李昌宁这些年仗着李甫铺就的关系网,平日里跟着何焕、王闳孚等公子哥赚了不少钱,往常那见着李甫都是昂扬着头颅的,都是趾高气扬的,今日却一反常态,犹如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
俗话说的话,知子莫若父,这李昌宁是个什么货色,当爹的李甫那是最有发言权了。李甫瞧着今天李昌宁那副怂样,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发生。
“怎么啦,与人博彩又输了,还是投壶博戏输了。又或者是在哪个勾栏里与人争风吃醋落败啦、、、、、、?”
李甫边吃边数落着这些年李昌宁的斑斑劣迹。
这都不算多,还没讲完呢,只听地上“扑通”一声响,李昌宁就跪在了李甫面前,李梅氏看这情形知道肯定大事不妙了。赶紧去将门关严了,将身边的下人都打发出去了。
“宁儿,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快速速说来与为父听。”
李昌宁这时候再也绷不住了,就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虽然有些不齿,但是为了保命,也只好如实交代了。
李甫听完李昌宁的供述后,当真是气得七窍生烟了,反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了李昌宁的脸上。
“你这逆子,怎么敢犯下如此的重罪,还是朝臣之女,这下丢人现眼都丢到官家面前去了。这让我还怎么去在朝为官哪,畜生啊,我李家怎么就出了你这样的一个孽障。”
那李梅氏虽说是平日里,有些溺爱和骄纵李昌宁,现如今造成如此的局面,也是悔不当初,但是那当真是自己心头上掉下的一块肉,见犯下了如此的大错,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李梅氏哭哭啼啼的:“老爷,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该想着法子怎生弥补才好。”
“弥补,怎么弥补,说得倒轻巧。你是不知道,那何栗也是封疆大吏,并非没有跟脚的虾蟹,还有,现在权知江陵府的是当今的九皇子,你觉得要怎么样来用金银财宝来收买呢?”
李梅氏听得丈夫如实说出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儿子当真是在劫难逃了,可怜他们夫妇二人这一生膝下就只有一子,到头来还得白发人送黑发人。想到这些,李梅氏就悲从中来,两眼婆娑,豆大的泪珠一颗颗的从眼睛里滴落了下来。
那李昌宁听完李甫的一番分析,吓得当场犹如一滩烂泥般,瘫坐在地上了。
李甫看到眼前这不成材的逆子,就来气:“现在知道害怕啦,告诉你,晚啦。早干嘛去了,早干嘛去了,但凡你有点羞耻之心,但凡你有点敬畏之心,也不至于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爹,爹、、、快救救孩儿吧,我不想死,不想死的。”
这个时候李昌宁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只要能保住性命,一切就都还可以重来。
李梅氏也附和道:“是啊,老爷,求你就救救宁儿吧,总不能让咱们两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你们别吵了,宁儿也是我的孩儿,何尝不想救他。这样,事发也过去好些天了,估计衙门还没有破案,也还没有怀疑到你的身上,这样,宁儿你听爹的,尽早返回江陵府去,并且还要让人相信并知道你一直在江陵府,近期从来就没有来过汴京城。别耽搁了,你今晚就乔装打扮连夜出城返回江陵府去。”
李昌宁起身后,刚转身又忽然想起来:“爹,那家里的这些下人们都知道我回来过啊,不然把他们都、、、”
李昌宁用右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坚信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说话,才不会有泄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