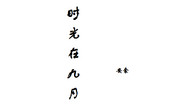第43章 平淡的日子
爸爸待不了几天,在上海没两天就又回去了,弟弟留在这,玩到九月一号,开学再回老家。
在上海的日子,加了一个弟弟,也增添了许多乐趣,虽然他盯上了我的电脑。
但我习惯于让他,而且我自己用电脑也不知道玩什么,便随他了。
除了看电视,绣十字绣,他还会陪我下象棋,我的象棋是上初二时我们班一个男生教的。
但棋技只停留在懂规则上,比如象走田,马走日,車横走竖走……
因此经常输给弟弟,很多时候,弟弟都不想和我这个菜鸟级别的玩,但我都缠着他陪我下棋。
有时候妈妈看到,也会说一句:“陪她下一盘。”
小时候,弟弟不会的作业,我教的没有耐心的时候,弟弟就会哭鼻子,现在倒反过来了。
妈妈下午煮的豆浆,两个人喝,晚上,开着空调,三个人看新版还珠格格,水浒传。
一天一天过去,又到了我去复诊的时候了,每次去复诊,我都有些高兴。
因为这说明我又平安无事的度过了一个星期了,我离正常人的生活又近了一步。
但这次去复诊,医生还要帮我做一个腰穿,说是检查脑子里有没有坏细胞。
简单来说,就是脑子有没有坏?!
我从没做过腰穿,在这之前就先向前辈打听了什么是腰穿。
腰穿的基本操作是,抽脑脊液出来检查,其实和做骨穿差不多,也是需要打麻药。
至于疼痛,个人觉得没有骨穿痛,只是,做完后,患者需要平躺在床上六个小时,不能动,否则会有头痛头晕等症状。
平躺六小时这一点比较磨人。
从上午躺到下午,中午饭我也没有吃。
妈妈担心我会饿,特意回家了一趟,做了东西给我吃,同行的还有弟弟。
我还一直以为他在家玩电脑打游戏呢,看到他来还是很高兴的。
一个人孤独久了,别人的一个不经意的行为,你都会认作是关心。
虽然我懂12岁的弟弟,有没有关心我的那份心,但我还是很开心。
妈妈是用之前在移植仓用的陶瓷碗装了食物过来,打开盖子,一股鸡蛋的香味就飘了出来。
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尤其是脑袋,看不到是什么东西,但能想到味道,一定很好吃。
弟弟端着碗,特意倾斜了一个角度,让我能看到,是一块块金黄色的饼。
又不像饼,和饺子皮大小。薄薄的几片。
妈妈说,是用面粉和着鸡蛋液摊成的薄饼,怕上火,只用了几滴油,开小火稍微煎了一下,成型后再放锅上蒸了一遍。
姑且叫蒸鸡蛋饼吧。
我躺在床上,是妈妈夹着蒸鸡蛋饼一点一点喂进我口里的,躺着吃东西,有点不舒服,生怕呛到肺里。
所以我吃的很慢,妈妈想的很周道,还带了奶粉。
没错,就是奶粉,杯子,调羹,吸管……
医院里除了药,最不缺的就是开水。
将带来的奶粉用调成的温开水泡开后,妈妈再插进吸管,这样我躺在床上不用动也可以喝了。
在常人看来,也许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无理取闹,但这在医院,很常见。
很多病人都是外地来的,有的人甚至是东北那边的,他们来一趟医院很不容易,病人吃的东西又特别要注意,不可以吃外面买的食物就是第一条,还有就是菜不能炒的太上火,不能放太多油,除了盐不能放其他调味料……
于是,无所不能的病人家属,便想出了许多妙招。
去饭店借厨房,或者去还在这里租住的病人家属家借,有的家属甚至直接带材料现煮。
我有一次星期四来医院复诊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一个从老家赶来复查的移植几年的病人,他妈妈带了小电饭煲,面条,油,盐……
病人抽完血后,她妈妈直接就在医院大厅里煮起了面条,煮好后,病人拿着电饭锅就开始吃了……
一开始看到可能会觉得新奇,但设身处地的想想,谁不是被白血病逼的那个?!
不过,被逼成这样的我们,都是希望病赶快好,赶紧恢复好能去上学,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男生,跑进诊疗室做骨穿检查,没到十分钟就出来了,还活蹦乱跳的。
他梳着平头,皮肤是健康的黑,看不出一点生过病的样子。
妈妈打听到,那男生移植四年了,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了。
移植四年就能这样了,是不是四年过后,我也可以变成他那个样子,我心里是羡慕的。
妈妈对我说,好了就让我去上学。
我点头,此刻完全没想钱的事,想上学,很想上学。
每次在空间看到同学们的动态,我都会刻意避开不看,因为怕看着不知不觉,心就飞到学校了。
但病好了,就能去学校了吧。
移植的病人和学校的同学有点像,也分同期。
比如,和我同一天移植的上海男人,还有张一涵,也是和我同一天。
上海男人没我这么幸运,拉肚子还在继续,他已经搬到三楼了,还是三楼唯一的VIP病房,不过妈妈说他的拉肚子还没好。
可能因为我好了,他没好的缘故,他妈妈经常会向我请教一些病情,尤其是关于腹泻的病情。
张一涵是我们三个中恢复的最好的,也可以说她是最幸运的了,竟然和她爸爸配到了全相合。
她移植的是她爸爸的骨髓,但也因为如此,她没有排异,更没有别的什么感染。
她爸爸是厨师,经常会换着花样煮食物给她吃,我在隔离舱那会食欲大开的时候,羡慕的不得了,好希望自己也有个当厨师的爸爸。
不过我的爸爸也不差,虽然做的饭难吃,但他爱我,他没有放弃治疗我。
张一涵的妈妈我见过,戴着黑框眼镜,高高的个子,想必张一涵个子也很高。
可能是因为我和张一涵同一天移植的,她和我妈妈关系很好,有事没事就爱一起聊天。
话题不用猜,也知道是关于我俩的病情的。
我还在隔离舱的时候,她在窗外看过我,不过我出院后,就很少碰到她了,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主治医生的原因。
听妈妈说,张一涵恢复的是真好,但有一点“硬伤”,血小板长不高,甚至有时候还低于三十,她妈妈也因此犯愁。
而我正好跟她们家相反,血小板高达八百多,从移植成功之后,就没降下去过。
这个,可能跟我之前吃的药有关。
还没移植的时候,晕倒入院,血小板为7的那次,医生给了我一瓶药,红色糖衣药丸,小小的一粒,我只吃了两粒,之后血小板就再也没低过。
其实我是想把这药的事跟张一涵妈妈讲的,但我不记得药的名字,而且我也怕自己说了,害了人家,便没提这事。
直到之后的几年,我又想起药的事,才后悔当初没跟张一涵妈妈说,可能我说了,那件事就不会发生,张一涵也可能不会……
暑假的两个月过的很快,爸爸又来了上海一趟,来看看我,顺便带弟弟回老家报名读书。
我很想多讲讲弟弟的事,但想来想去,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讲的。
弟弟在的日子,除了家里多了一个人,也除了生活也比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亲切些,还有……
没有了。
下棋,玩游戏,喝豆浆,看电视,睡午觉……
特别平常的琐事,像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我都这样子度日,其实,他在的日子,平淡的很不起眼吧。
没去上海著名的东方明珠,也没去热闹繁华的外滩,就在郊区的房子,待了两个月。
弟弟临走的那天,我才发觉,原来生活中少了一个人啊,妈妈跟我说:“弟弟走了,感觉房子都空了一大半。”
妈妈和我是一样的感觉,也许,最容易忽视的,才是最不能缺少的。
弟弟走了,生活又回归到我和妈妈两个人的生活。
我烦,她也烦,很多次,我午睡起,走到她房间门口,都看到她坐在椅子上,不知道在干嘛。
我问她:“妈妈,你在干什么?”
“我在等着晚上做饭。”她回道,一句很不经意的话。
却让我涌出一抹心酸的情绪,因为我,妈妈只能整日陪着我荒废时间,除了照顾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让她学着绣十字绣,绣好了还能卖钱,但她说看着那一个个小格格,眼睛就花。
后来,偶然的一天,她去老街买了毛线回来,她给我们织毛衣了。
我一件,爸爸一件,弟弟一件。
妈妈织的毛衣很暖和,我后来穿了好几年。
夏去秋来,我还留在上海,每个礼拜的周四去检查,医生会根据你的身体,适量的减药量。
时间一长,我吃的药大概都能叫上名字,其中有一种名叫甲泼尼龙片的药,是椭圆型的白色药片。
也是激素。
我以前就了解激素,比如,打了激素的鸡鸭是不能吃的。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在网上查了关于长期吃激素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