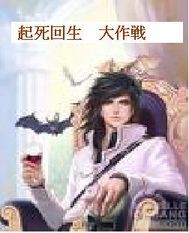第10章 因为激素
退了烧后,我的人渐渐精神起来,胃口也逐渐好了,就连平时不喜欢吃的医院食堂的饭,现在也能吃一大半。
我家乡的口味偏辣,而上海的口味偏甜,我本是吃不惯的,我也不知道为何,突然就觉得平时看着都没胃口的饭菜变得美味起来。
我以为这是退了烧,身体好转的原因,但是,十五床的一件事,让我知道,不然!不止是!
退烧的第二天,那是早上的时候,我把妈妈从食堂阿姨那打来的一大杯稀饭都吃光了,包括下稀饭的小菜,面包,我佩服自己居然吃了这么多。
吃完饭,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躺在床上照常等待护士来上针。每个病床都有责任护士,一个责任护士可能负责几个床位,也可能只负责一个床位。
当时我和十五床的责任护士正好是同一个,我看到她先把药盘放在十五床的床头小桌上,应该是要先跟她上吧。
于是,我像个等待打疫苗的小孩子,乖乖躺好,等着护士姐姐来打针。
病房里的病人手臂上大都有PICC管,护士给病人上针不需要多久,不用从静脉打针,只需在管口,通管,接管,调滴速,大概就好了。
但也有例外,十五床的病人,她的管子就插在了脖子上。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看到护士正拿着碘伏往十五床病人的脖子处涂涂抹抹,应该是消毒。
我在想,脖子上肉那么少,管子插在那里肯定很疼,我还没来得及想象那是怎么样一个疼法,就听到隔壁病床旁边护士尖细的声音。
这家医院的护士大部分是上海人,说话的声音也都是尖细尖细的,若不是她们身材不一样,胸口还有标牌,我真的分不清谁是谁。
护士说:“你这管口松了啊,得重新固定一下。”
“啊?松了?”十五床病人是一个老人,和之前的金陵老妇年纪差不多大,不过她的个子比较小,身材偏胖,说话的声音也听着含糊,我的床位若不是在她隔壁,我肯定也听不清。
“嗯,松了,得重新缝针。”护士强调了一遍。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人有耳背,我感觉护士这次说话的声音明显比之前还要大。
接着老人又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句我实在没听清,紧接着就听到护士说,“缝针,你现在别动,你动的话那管子容易跑,到时候堵到了血管要拔了重新插的。”
说完,护士转身往门口走,她留下了护士药盘,应该是要去拿什么东西。
只是,护士还没走几步,老人就像是没听到护士刚才说的话一般,她仰起脑袋好像要找什么东西。
从刚刚护士来到这一幕,我和妈妈都看到了,见状,妈妈急忙对十五床的老人说:“别动,诶,护士……”
妈妈边说着,人已经制止住十五床的手了,护士那边闻声,也赶紧几步并一步走过来,“你别动啊!你家属呢?”
护士说完,又看了眼我妈妈,问:“她家属呢?”
“不清楚。”妈妈摇头,随即说,“应该还没来。”
十五床老人是上海人,她的子女白天会来,但晚上不陪夜。不过他们为老人请了一个护工,从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开始算,好像是一天一百还是多少,忘了。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也没心思记那些。
我想,这个点,老人的子女应该还在来医院的路上吧。
护士没办法,只好让妈妈帮忙照看一下,然后迅速去拿缝针需要的东西。
妈妈为了转移老人的注意力,和老人简单聊了几句她子女的事。我看到现在乖乖躺在床上说话的老人,又想起刚才她鲁莽的举动。
脑子里突然回忆起妈妈曾经跟我说的,十五床病人脑子有问题的事。
难道是这个原因?反正如果我脖子上有管子,而且随时要重新插,我不敢。
护士很快将东西拿来了,我眯眼看了一眼,还真是针!缝衣服的针!
我看到护士将一种黑黑的线穿进针孔,那应该是手术用的医用缝线。
护士将管口处的肌肤消了毒,然后对十五床老人说:“现在帮你把管子缝在皮肤上,不要乱动啊。”
“哦,不动。”老人的回答像个孩子。
但,接下来!
“啊……唉哟……”
“我还没开始呢!现在打麻药啊,别动。”
“痛……唉哟……”
“别动啊,麻药没打到的话,缝针的时候疼我不管啊!”
“不动了,我不动了……啊哟……”
我听着隔壁病床的痛叫声,觉得脖颈一凉,好像自己也感觉到那痛意。麻药的痛我是知道的,酸,胀,麻,然后毫无感觉。
至于缝线,我没经历过,当时我心下想的就是,以后医生一定不要给我缝线啊,连她一个大人都叫痛,我一定承受不了。
管子固定好后,护士才帮老人上药,挂水。
这个时候老人已经消停了,躺在床上,好像累了,护士帮她挂药水的时候,我听到老人问护士:“挂的这是什么药水?”
“地塞米松。”
“啊?什么药哦?”老人说的话真像个孩子,懵懂,无知。
我看到护士周身的气息明显有些不耐烦,她提高音量,再次说道:“地塞米松,就是激素,激素!”
这次,她用的是上海话说的,可能是真不耐烦了吧。
我听不太懂上海话,不明白护士说的“地塞米松”是什么,于是我扬起脑袋,说的家乡话,问妈妈:“那护士说地塞米松是什么药?”
“激素。”妈妈回,她接着跟我说:“你那天退烧的时候,护士在你手背上推的那针药,你还记得吗?”
我摇头:“不记得。”
不等妈妈再开口,我好像猜到了我是因为什么退烧了,之前烧的那么厉害,不可能无缘无故退烧的。我问出了心中的疑问,对妈妈说:“那不会是激素吧,我是因为打了激素才退烧的?”
“嗯,你打的那针就是激素,不过这两天也在挂激素,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体温。”
激素……
我以前在电视上也听说过激素,社会新闻上常报导的,哪里的鸡鸭打了激素,哪里的猪肉鱼肉打了激素……
只是,没想到我也有打激素的一天,还有,激素不是对身体有害吗?也能退烧吗?为什么医生要给我打激素?
那个时候,我不懂这些,医生也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回答你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无聊的问题。
我真正了解激素,是在几年后,那年,我差点因为激素丧命,我和它……说的深点,算是过命的交情了吧。
……
不是别的原因让烧退了,而是因为激素,这让我心里有些失落,还有打心底对这种药物的排斥。
不过,不好的心情仅于几分钟,体温太久没有正常过,发烧好了后的我嘚瑟起来,也是逗比一枚。时而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哼着歌,时而跟妈妈说笑,笑出声……
可能我是病房里最小的病号,又是外地人的原因吧,我们特别受人照顾,他们对我的照顾,大多数是给吃的。
发烧的时候就经常会有好心的病友送吃的给妈妈,只是那时候意识不清楚,也不记得谁给了我什么吃的。
现在的我没有再发烧了,加上我的逗比举动,他们就更喜欢问我的事拿我开心了。
比如,在学校成绩好不好?
刚发病的时候,是什么症状?
说的最多的是,她们讲我第一次做骨穿鬼哭狼嚎的那一天。通过跟她们聊天,我才知道,原来她们都做过。
她们还传授给我做骨穿的经验,像是做骨穿要找女医生,因为男医生力气大,没轻没重的,相反,女医生温柔。
我不知道她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被她们的话逗笑了。
她们的年龄大多五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有四十岁,但她们的心态,真的跟小孩子一样,虽然生了病,仍然笑的那么灿烂。
也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会有那么一刹那,忘了自己是个白血病人,甚至忘了自己生着病,忘了手上的PICC管正输着液……
住院是枯燥的,但是有这么多病友在一起的病房,是温馨的。她们会让你觉得,你并不孤单,你还有千千万万的白血病患者和你一起对抗白血病。
她们就像是天上的繁星,看着星星点点,但她们身后,是和太阳一样炙热的阳光,给予你力量,打败白血病的力量。
……
三天过去,我没发烧,我成功从高热的苦海中解脱了。身体不难受的日子总是过的那么快,医生通知我们,马上要进行第二次化疗。
但是,在那之前,要先做一个骨穿,看看坏细胞还有多少。
骨穿!
我听到这两个字脑袋都是懵的,真是说什么怕什么,前两天她们还在讲骨穿的事,现在就要做骨穿了。
而且他们的速度还不是一般快,早上查完房,就立刻有医生拿着手术包过来了。
我:“……”
想起病友跟我说的话,我急忙捂紧自己裤腰带,说:“我要女医生帮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