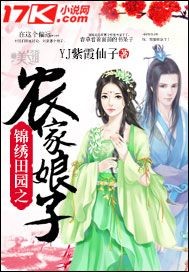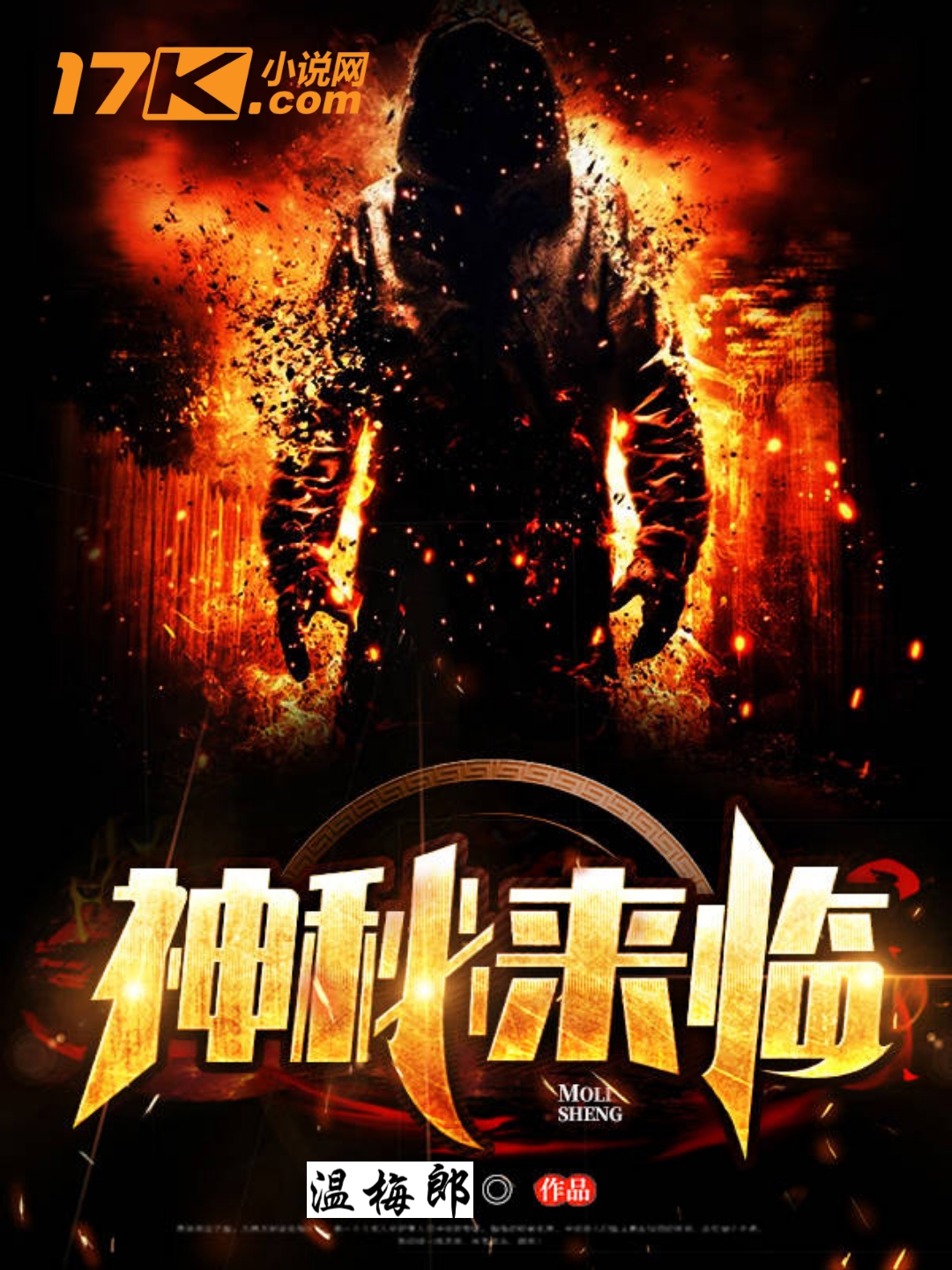绛金色的纱帐重重叠叠,丈余宽的池子雾气缭绕,九只石雕龙口中缓缓的流出温润的水,水经过龙头下方一块突出的竹篾,发出清脆的声音,像鸟鸣,似蝉啼,煞是好听。
偌大的池子正东方,斜坡而上锻造成一只玉石的龙榻,一四十岁左右中年男人赤-身半躺在玉石塌上,大半的身子浸入水中,矫健的身躯在水中更加的健硕。
男子眼眸轻闭,静得如同画中的垂钓散翁或踏雪书生,只颤动的眼睫、匀称的呼吸,诏示着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当权之人。
男子的肩部之上,一年过半百的无须男子跪在地上,用手肘轻轻的顶着明黄中衣男子的肩部,先是轻轻按着,随即“卡喳”一声用力,中年男子舒服的轻哼一声,似喃喃自语道:“还是公公的手法最得朕心。”
骆公公深知皇上并不希望自己答话,默然不语,手肘却不停留,继续着在男子颈部及肩部,甚至胸部上下游走的按动着,哪里轻,哪里重,哪里用手肘,哪里用指腹,都是恰到好处,多一分力嫌多,少一分力嫌少。
“殷明月长什么样?”皇帝没来由的问出了这么个奇怪的问题,令一向自持力很强的骆公公,不由得手停了一停,怔了怔神。
皇帝轻锁了下眉头,骆公公忙郑重跪下施礼答道:“回陛下,老奴未曾见过,也未曾探过,但想着魏司农多年不近女色,此次却求着皇后和太子爷来向陛下求情,这女子定是人间绝色,世间少有的。”
皇帝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半天才揉了揉太阳 穴,皱着眉峰,瞪着还在跪着的骆公公道:“跪什么跪?不过闲聊打发时间而矣,朕被这些后宫的女人吵得头疼,你继续帮朕松散筋骨,别停。”
皇帝随即翻了个身,大片的后背展示给了骆公公。
骆公公得了令,犹豫了片刻,半跪起身子,继续帮皇帝松背骨,只是心头更加的谨慎,自己一丝一毫的情绪变化,透过这手法,皇帝陛下只怕马上就感知得到。
皇帝舒服的轻哼两声,随即轻叱道:“这倒是勾起朕的好奇心,魏爱卿一向冷心冷肺,对朕也是七分敬三分畏,对朕交办的事情使七分力留三分,对此女倒是十成十的掏心掏肺。”
骆公公手上加力,从皇帝的颈部下移至颈椎,按着其中一只椎节道:“即然如此,万岁爷为何不将查盐之事交托给十成十忠诚之人呢?”
皇帝将脸贴在玉石上,玉石的温度熏得脸色潮红,却无比的熨贴,皇帝轻吐了口气道:“这江山一图,朱丹为红日,雀蓝为青山,砗磲为白雪,在于‘知人善用’,在于‘恰到好处’ 。这魏知行便是如此。魏家家族凋零,无外戚专权之忧; 魏知行性情淡溥,无结党营私之患,与泯王有夺妻之恨,对朕‘忠诚’绝对毋庸置疑。只是这个小小的农女,让朕觉得这‘忠诚’之中好似多了些什么,就如同朱丹里混进了蚊子血,让人心中着实不快。”
朱丹里的蚊子血?骆公公恍然,皇帝能坐在朝堂之上,自是有着一颗七巧玲珑心,对平衡之术、读心之术甚通,怕是看出了魏知行对皇帝也存了私心,甚至耍了手段,对魏知行生出不满之心,只是碍于还要依赖于魏知行牵制泯王。
如此情景,怕是这殷明月的命运,要两悬了。
骆公公小心翼翼道:“万岁爷,这殷明月虽是一介农女,但却夹在了齐阳郡王与魏司农之间,一个要殿前御审,一个让手下留情,这可如何取舍?”
皇帝笑着从水池中站了起来道:“这个好办,就用‘拖’字决,时间总会给朕答案,坐山观虎斗,乐在其中。”
骆公公拿过明黄色的衣裳,帮着皇帝穿了起来,在系胸口的带子时,低声说道:“即然蚊子血恶心到万岁爷了,不仅要打死了蚊子消了它的气焰,还要反过来恶心恶心它的主人为好。”
皇帝陛下一把抓住了骆公公系带子的手,将骆公公手掌的青筋都掐了起来,吓得骆公公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头磕得山响,连呼饶命。
齐皇帝带着狐疑的眼色盯着骆公公,半天才轻叱一声道:“何罪之有?公公说的对,恶心到别人,总比恶心到朕一人来得好受些。只是这事儿要做得不留痕迹,这朱丹,朕还是有用的,江山一图,不能没有红日升起。”
骆公公再次磕了一下头道:“万岁爷可记得前几日 吃的‘佛跳墙’?去年吃的‘一桶(统)江山’?前年吃的‘小五珍’?”
皇帝点了点头,这些他还是有些印象的,每年春节,骆公公都会责成御膳坊研制新的菜色,刚刚骆公公说的这几道,是每年菜式最新颖的、口感最好的菜色,自己的印象颇深。
骆公公荣与俱焉道:“回万岁爷,这些菜色均是出自一人之人,就是老奴家族中最为出众的侄儿-----骆平。他心思轻巧,一片赤诚,除了对老奴限制他自由颇有微词外,可堪大用,最为关键的是,他与殷氏明月同出朝阳县,感情甚笃。”
齐皇帝眼色一眯,半晌才道:“这几日朕的嘴巴寡淡无味,让他进宫到御膳房来孝敬几日吧。”
骆公公一脸欣喜磕头谢恩,却又一脸踌躇道:“万岁爷,小的亲自给他净身?”
齐皇帝眼睛瞪圆了怒道:“你敢!?你这一双老手只能留着给朕松骨!骆平朕有大用,你若是敢私自给骆平净了身,朕就给你净二遍身!让你连出恭都出不得!!!”
骆公公吓得磕头如捣蒜,嘴里连声保证道:“万岁爷息怒,小的不出宫!永远陪着万岁爷,绝不出宫!!!”
齐皇帝不怒反笑,瞟了一眼侍候了父皇和自己两朝的老太监,佯装嗔怒道:“老狐狸!偷换概念!朕说东你说西,你说‘出不得恭’,你答说‘绝不出宫’,当朕听不出来吗?也罢,谁让你是朕中意的老人呢,饶你一次。”
齐皇帝一甩袖子出了纱帐,八名宫女纷纷给更了新的衣裳,待迈步踱出浴室之际,回头看了一眼仍跪在地上的骆公公,轻声答道:“你这打蚊恶心主人的主意,朕甚是满意,否则,朕还以为骆总管是魏司农的人呢,体己话太多,一个时辰都没有聊完。”
骆公公的脸上登时呈现了一层薄汗,抖如筛糠。
就在一个时辰前,魏知行与骆公公进行了交心的谈话,这场谈话,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也是他所不想接受的,却又不得不接受的。
此时的他,十分庆幸自己留下了一个自私的心思,为骆平将来铺路,这才在心细如发的皇帝面前挽回了一丝颜面。
送走了皇帝陛下, 骆公公长舒了一口气,撩起一捧水,抹了一把脸,心中则寂然,自己,已经成为了魏知行的一枚棋子,不能让骆平再成为魏知行的另一枚棋子,既然如此,不如让骆平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皇帝陛下的一把锋利的剑也好。
骆公公却忘 了,剑是双刃的,伤了别人的同时,也可以伤了自己,于骆公公而言,伤人伤己伤骆平都己不再重要,他只要,给骆家一个未来的领头雁,一个庇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