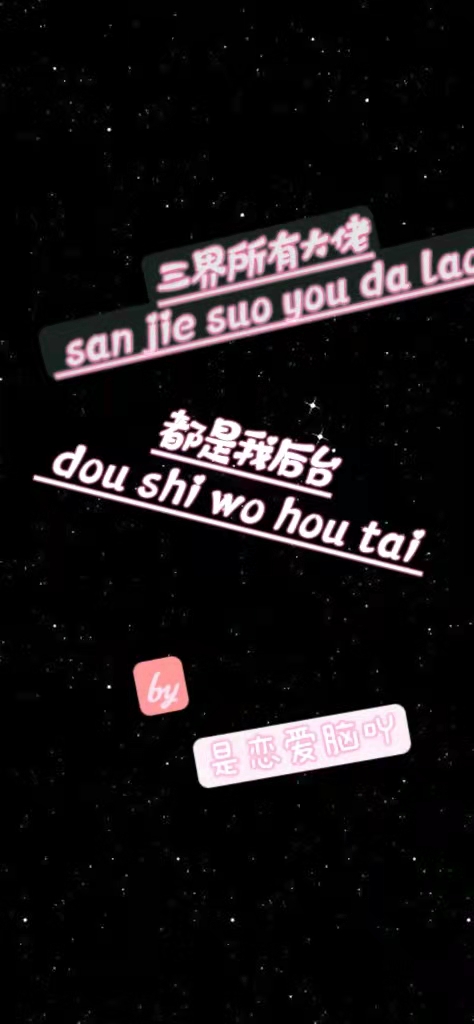北方大雪皑皑,冰冻三尺。
南方的京城却是温度适宜,略微冷瑟,却绝不如北方的寒风透骨。
两辆囚车砸砸而响,走在肃然的正德大街上,声音如此的清晰;囚车之后,二百名黑鹰卫银衣亮甲,一脸冷寂。
出行得早的商贩,只抬眼看了两眼囚车中的人贩,默然低下头,继续做着自己本来做的事情,丝毫未在心头激起一丝波澜。
在这天子脚下,押犯、鞭笞、绞首、分尸早己是司空见怪,隔三岔五便会有人被押至菜市口,或是举家,或是全族,上百条人命,也不过是瞬间魂飞烟灭。
在这里,人命,真的不如寻常百姓口中的一口吃食来得重要。
一队快马迎上前来,为首之人谦和施礼道:“魏司农一路押解重犯,舟车劳顿,小王这就派人将人引至大理寺妥善安置,明日早朝便可面圣起奏。”
魏知行忙谦然回礼道:“齐阳郡王如此多礼,倒是折煞了下官。转送大理寺之事怎敢劳郡王大驾?洪丰洪少卿已经遣人来接,定会‘严加看管’,不容有失。”
齐阳郡王未再纠结此事,转移了话题道:“魏司农一离京城数载,只每年述职回京小住,晚上不若由本郡王做东,到***小酌一杯如何?”
魏知行淡然一笑道:“郡王与下官相识又不是一日两日,怎不知魏某从不踏烟花之地?不若哪日由下官做东,在一品居设宴宴请郡王?只是下官己回京城,若是不先一步晋见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难免又是一阵嗔责,容后两日,下官定将宴贴送至郡王府上。”
齐阳郡王谦和的回了礼,便调转了马头,与魏知行并驾齐驱,一起向大理寺而行,过不多时,又来一队人马,却是姗姗来迟的洪丰。
见洪丰的脸色,魏知行心头有些不安,碍于齐阳郡王在此,又不便多问,只眼色盯着洪丰。
洪丰回了一个让魏知行安心的笑容,命大理寺中人将两名人犯押解回大理寺大牢。
趁齐阳郡王先上马离开之际,魏知行落后一步,轻声道:“可有什么问题?”
洪丰笃定的点点头道:“有些小问题,无碍,定能保证人犯安全。”
魏知行轻舒了口气道:“先拖两日,我再确定一下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洪丰忙点了点头,努力压下心头的不安,心里盘算着用自己的残余势力摆布大理寺,以保证殷明月与成越在押期间的安全问题。
这个变化对全局来说影响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
就是在魏知行回京路上这一个月期间,原大理寺卿突染恶疾病殁,第二把交椅的大理寺少卿洪丰失棋一招,未能顺利接任,而是被礼部侍郎施大人抢了先,此人惯会阴奉阳违、阿谀奉承,与洪丰日常颇多不睦。
之所以说对全局影响可大可小,是因为此人不是魏知行的人,也不是泯王的人,对此时的战局没有太大影响。
此人之所以能被举荐上来,是因为原本此人是左相刘相爷的亲家,后来因小女儿被送进了后宫,得了两天宠,生了个皇子,从此以后娘家爹就跟着平步青云了。
有了洪丰的保证,魏知行匆匆回府,准备换一身衣裳再进宫晋见皇后娘娘。
大司农府府门门口,一人清孑独立,一动不动,形同石像。
见到魏知行,举步而起,却又抑制着缩了回去,举步不前,眼眸中的急色却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魏知行未理会于他,跳下马来,因一路骑马,双腿有些麻木伤痛难忍,魏炎忙上前搀住,脸上露出一丝不忍不色,轻声道:“大人,还是先上些疮伤药、冻伤药吧!”
魏知行未曾反驳,任由魏炎搀着迈步进得府门。
骆平一脸急色加怒色,终于迈起步子,跟着窜进府中,拦住了魏知行道:“乐阳郡距此数千里,你连平日里做的马车都不坐,快马加鞭,不足一月便到达京城,直接将明月投进了大理寺,你就这样急着将明月置之于死地?”
魏知行淡然看了一眼骆平,挑了挑眉道:“是。”
骆平气得脸色惨白,手指颤抖着指着魏知行道:“算是明月瞎了眼,看上你这个伪君子、胆小鬼、负心汉、薄凉人.......”
魏知行气定神闲,魏炎却心里气不公,瞪了一眼骆平,狠狠踏了一脚骆平的脚,气恼道:“骂人的词儿用完了就赶快让路,这里不是你的朝阳县珍味坊,也不是你骆叔叔的后宫地界,轮不到你来嚣张。”
骆平被踏得脚痛,脸色都胀得青紫,魏知行轻叱一声道:“一向宠辱不惊的骆东家,今日能为了明月爆跳如雷,不知该是明月的幸,还是本官的不幸。进来吧,京城中的事还要向你询问一二。”
骆平尽量压住心头的气焰,尾随二人进了府中。
大司农府占地极广,主殿气势辉宏,偏殿却简陋异常,看着竟如魏知行的人一般,无欲无求,冷淡偏执。
让进了会客厅,魏知行仍被魏炎坚持着先去抹了药,换了衣,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出现在骆平的视线里,此时的骆平,脸已经用冷若冰霜来形容了。
魏知行静静坐在太师椅里,较原来清减不少的面庞,让人看着有些可怜。
骆平轻吐了一口气,如同魏知行一般,静静坐在了客座,默然不语,婉如两个没有生气的木偶,谁也不想先行说话了。
良久,魏知行身上的气息暖了暖,才没头没尾的道:“这一路,冰雪交加,风餐露宿,坐在铺着兽皮、点着碳炉的马车内,定会很舒服、很暖和。”
听着魏知行没头没尾的一句话,骆平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到现在,他才知道魏知行为什么是骑马回京,而不是坐他惯坐的马车,只是因为,明月坐着囚车,吹着风雪,受着寒凉,忍着颠簸;所以,他也要骑着马,吹着风雪,受着寒凉,忍着颠簸,感同身受。
骆平抬起眼睑,充满了一线希望,喃喃半天才道:“是,是我误会你了,明月,还能救出来吗?”
魏知行轻扯着嘴角,轻眯着眼眸,盯着骆平半天沉吟不语,直看得骆平莫名的发慌,心脏莫名的下沉再下沉。
又过了良久,魏知行才轻吐了一口气道:“能救,看你,能不能舍弃一个人。”
“谁?”骆平讶然问道,实在不知道,自己的身边,舍弃哪个人,会救出惹了滔天大祸的殷明月。
魏知行看着坚定的骆平,吐出三个字道:“骆总管。”
骆平脸上登时现出一丝痛苦之情来,骆总管,他的亲叔叔,给骆家带来无限荣耀之人,也是掌控了自己一生害自己失去自由之人,与自己,亦师亦父,亦恩亦仇,诸多牵绊,理也理不清。
魏知行知道骆平与骆总管的情感,未加强求,而是继续循循善诱道:“骆总管将盐矿的消息通报给泯王,你认为陛下当真是毫无查觉吗?孰轻孰重,你自己心中自有分寸。”
骆平如失了魂的木偶般离开了大司农府,手里紧紧捏着一张发黄的纸,这是以叔父的名义给齐阳郡王写的一封密信,里面全部是先皇与皇帝陛下小时候的细枝末节,外人看不出什么来,可知情之人,定会触目惊心,尤其是皇帝,怕是第一个就要活剐了骆总管。
骆平的腿若被灌了铅水一般的沉重, 他虽不知道 这信的竟义,却知道以魏知行的善谋,这信只怕比催命的符还要致命。
心头,如那战局如火如荼的北疆,兵戎相见,胜负未分。
无庸置疑,明月,定是要救的;叔父,怎样才可留得一条命在?
“卖鱼啦!卖鱼啦!新打上来的河鱼,客官买些回去尝尝鲜?”一道清澈的童音响彻在耳边,吓了骆平一个激灵,怔怔的看着在篓子里欢脱鲜活的鱼。
见骆平怔然,卖鱼童以为遇到了诚心买家,将鱼篓倾斜了些,让骆平看清里面的鱼儿。
这一倾斜不打紧,其中一条巴掌大的小鱼一窜跃出了鱼篓,落在了地上欢脱了两下。
小鱼童气得一弯身,只一下就将小鱼儿抓起重新扔进了篓子里,讪笑的对骆平解释道:“客官勿怪,这人越老越精,鱼却越小越贼,小的给您捡条大的、愚笨些的?”
骆平眼眸中顿时现出一道精光来,人越老越精,鱼越小越贼,曾听明月说,有一种鱼叫乌贼,之所以叫乌贼,是因为它惯会装死,墨汁还会消失.......
骆平从怀中掏出一块银子来,直接扔给了小鱼童道:“这银子是赏给小鱼儿的,代我放生了吧!”
.......
魏炎看着骆平魂不守舍离开的身影,一脸担心道:“主子,骆东家即使对殷姑娘感情再深,也不至于出卖了从小将他养大的亲叔父吧,若是消息泄露出去了,这可如何是好......”
魏知行无所谓的摇摇头道:“你也说了,凭骆平对明月的、的感情,这个消息定不会传出去的。至于这封书信能不能传到齐阳郡王手里,能不能如期被新上任的大理寺卿施大人搜出来,能不能让陛下下定决心清理了泯王,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骆平,而是骆总管。我一会进宫时会见骆总管,他会乖乖就范,且心甘情愿。因盐矿、铁矿私通大周之事,再加陛下忌讳之事,泯王就是砧板上的鱼儿,等着陛下开刀吧。除掉泯王,救出明月的胜算会多达七成。”
魏炎绞动了半天脑汁,任他再聪明也想不明白,哪有人愿意自己去送死的,还是个位高权重、汲汲以求权势,终于爬上高位、享受了一辈子荣华的老太监骆总管?
魏知行没有多做说明,却有十足的把握劝得动骆总管自投罗网。
有一种人,活着,是为了情,为了色,为了赌,为了各种私利;
还有一种人,却是为了家族而活,骆总管,就是这样一种人。
在知道自己失势并有可能累及家族的时候,他宁愿自己的家族中,另一个人崛起,取自己而代之,甚至不惜以大义灭亲、建功立业的方式,替自己继续庇佑自己的家族辉煌,这个接替他的人,只能是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