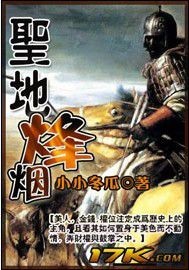凝望着残破的簪子,白羽唇角却勾起一色苦涩无奈的笑意。他倒希望着簪子真的是自己送给柴萱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也就意味着自己还留在她心里。而不是,从她口中听到那句冷冷的“相忘于江湖”。
剑眉微沉,却又缓缓的展开,随之漫开的却是无尽的无奈与伤情。“陛下,您知道柴萱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什么意思!”
面对白羽的问题,曹丕猛然一顿。自己和柴萱相识这么久,难道自己还算不算撩解她吗。白羽竟然问自己这样的话,简直是在鄙视自己。
却见白羽幽幽一笑,眼帘半垂摇摇头,道:“陛下可知,柴萱曾经为她的义弟挡下利斧,为他的朋友受了二十脊棍,为了无关紧要的人拼命的战斗。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她容不得任何人伤害她的兄弟,她亦不会无缘无故的去伤害任何一个人。陛下口口声声说喜欢她,那又了解她几成?”
白羽抬目而视,强硬的压抑着嗓子里的哽噎,“陛下,您是否记得柴萱为您拼命吸毒血的事情呢,如果她心里真的没有你,她不仅不会去冒险,反而会躲的远远的。她最惜命,如果不是为自己最在乎的人,断然不会如此。”
手心微颤,慢慢捡起摔在自己旁边的一截断簪,渐渐握紧掌心,“如果,她真的在乎这个簪子,当初就不会退还给臣了。”
白羽的话不禁令曹丕开始重新审视重新对自己的感情,心中的怒意渐渐被悔意取代,难道自己真的错怪了柴萱吗。
看着冷静下来若有所思的曹丕,白羽反倒满心伤感。凝望着手中的断簪,眸低竟渗出了一层雾气,模糊了视线,这一下他们真的一点回忆都不会再有了。
“如果这簪子不是你给的,那……究竟是谁要陷害柴萱?”回过神的曹丕这才恍然大悟,如果这簪子不是白羽给的柴萱,那就肯定是有人再这中间动了什么手脚。
凝视着断簪,白羽若有所思。这簪子是自己的那枚没有错,可如果真的是许蓉随意的丢掉,又怎会有人知道簪子与柴萱有关。除非这里有人知道当年的秘密,而知道这件事情的也就只有……
眸光微闪,白羽似乎知道了些什么,“陛下,这宫里谁最在意贵人的地位,谁又知晓当年之事,那谁就可能是陷害之人。陛下,还需问臣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曹丕猛然一惊,袖中的双手不由握紧。
“只是如今,证据毫无,要想洗脱臣与贵人的污名,不是易事。”白羽再拜言道。
“那就查,不管是谁,朕都要把他揪出来!”音色硬冷,曹丕的额宇间附上了一层少见的狠戾。“白羽,这件事情全权交给你,簪子是怎么来到宫里的,朕要你亲自给朕个交代!”
虽然自己对白羽仍旧心存芥蒂,但在这件事情上,最能信任的也只有白羽了。不管是谁,只要敢对柴萱出手,自己便绝对不容许他在这个世上在逍遥度日。
凝望着曹丕冰傲幽然的坚毅神色,白羽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也许,曹丕对柴萱的在乎同自己相较,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于自己的软弱,曹丕果决与坚定更能护的了柴萱。
入宫时是心乱如麻,出宫时亦是惶恐难安。银月如纱,轻轻的拢在白羽的身上,徘徊在月下的他久久难以安心。
抬眸仰望夜空,那朗朗圆月照的整个天际一片光明。或许,柴萱于她就如那水中月,镜中花,注定可望而不可及。掌心紧握,将手中的短暂捏的紧紧。即便老天要斩断他和柴萱之间的所有种种,他也决不会违背自己的承诺。
朗月清辉凭谁借,月华如水空负景;是非累累转头言,望将真心托此生。
八月的风,似裹了许多有无言的烦躁。满园的花团锦簇,却还是难以令赏景之人松开堆在额间的小山丘。
“陛下!”
一声宛如银铃般的娇声将周遭的寂静打破,被打断思绪的星眸微微一瞥,瞧见仇苓正俯身施礼,如雪的衣裳像一朵青莲一般徐徐绽放在地上。
“平身吧!”曹丕轻轻吐道。从语气中可以听出他此时的心情不是很佳。
望着矗立在凉亭中一动不动的曹丕,仇苓起身,柔目轻垂缓缓言道,“陛下,可是有何烦恼,能否讲予妾听呢?”
轻瞄眼身侧温婉柔情的女人,曹丕心里的烦躁感突然有了几分消减。他之所以觉的仇苓不错,倒不是因为她有多妩媚动人,而是这一份柔的似水的感觉,不骄不躁,不争不抢。在这宫里,她是很难得的能让自己愿意多讲两句话的人。
“也对,说与你,也可帮朕解解忧思。”曹丕间目光从仇苓身上收回,重新将目光投向远处。
仇苓微微福身,“陛下请将,妾自当洗耳恭听。”
沉顿半晌,曹丕还是开口言道,“今日一早,郭贵嫔便来寻朕,言明,想要认叡儿为义子,你认为此事如何?”
闻言,仇苓心中一惊,原来柴萱所讲的另一人竟是郭照,难怪让自己准备好去劝说曹叡。可宫中传言,是郭照代替曹丕下的毒死郭照的命令,如此一来曹叡必然会将杀母之仇记在郭照的身上,又怎会愿意相认。柴萱这步棋究竟所为何意。
“陛下,贵嫔娘娘自是贤惠端庄,宽以待人。若是认了叡公子,自然是处处关怀备至。可这认母也算大事,也得问问公子才好。”仇苓悠悠言道。
虽然柴萱说公子可以帮到曹叡,可仇苓心里还是有几分难以接受。谁人都知道郭照和甄宓是面和心不和,倘若那件事真与郭照有关,这么做,岂非是让曹叡“认贼作母”吗。
一提到曹叡,曹丕的面色明显难看了很多。父子反目亦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可他好歹是皇帝,当着众人之面让自己下不来台。就算是自己的儿子,也得给些教训才是。可当时的自己真的是连着甄宓的事情给气昏头了,才一怒之下将曹叡送进了大理寺。事后,别提自己有多后悔。
看着曹丕微紧的面色,仇苓亦不再说什么。这种事情,多说无益。曹丕从来不会去征求任何认的意见,说出来也只是让别人听听,让自己缓解缓解罢了。
“奴婢参见陛下,仇昭仪!”元瑞弯着九十度的腰,行礼跪地。曹丕颜色微动,整个人莫名的紧张了起来。一言不发的望着元瑞,等着他说话。
曹丕不发话,元瑞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更何况继续说呢。望眼面色严肃的曹丕,仇苓只好代替他开口问道:“元瑞,你来所谓何事啊?”
“回陛下,仇昭仪。柴贵人想问问陛下,今夜可否移驾长萱宫?”元瑞再拜道。
听到柴萱让他去,曹丕心里顿时五味陈杂。恨不得立刻掰开步子就去,可一想到自己对柴萱怀疑,心里就愧疚万分,不知该如何去面对了。
回望着曹丕时紧时松的额间,仇苓自然心知肚明。这位陛下想去是想去,可似乎是在害怕柴萱会因为他的禁闭步给他好脸色吧。
“陛下,有些话还是当面言明说清的好。”仇苓温温一言,欠身施个礼。“既然,陛下有事,那妾就先告退了。”
留在原地的曹丕默默的沉着,一言不发,元瑞只好怪怪的站在一边等着曹丕的回答。
在此之前,柴萱从来没有让人去请过曹丕。而这次却破了例,元瑞不禁有些担忧,难道这皇帝真的就这么无情无义,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就这么直接将你抛诸脑后了?
只见曹丕脚步微抬,仍旧未回答元瑞方才的问话,而是直接就朝着长萱宫的方向而去。元瑞傻呆呆站了半天,还是曹书一个巴掌在他脑壳上一拍,才将他喊回神儿来。
“还愣着干什么,再迟疑,陛下都要进了长萱宫了!”曹书一脸嫌弃的望眼元瑞。
“喏,奴婢,马上就回去禀告!”元瑞紧的玩玩腰,一路小跑的回长萱宫报信儿去了。
银月如雪孤凉勾,残火无神静独燃;珍馐易冷佳人坐,倾酒入腹心还寒。
“陛下,您都在着窗前站了许久了,为何不进去呢?”小满心疼的望着独自在屋里喝闷酒的柴萱,满含泪水的望着亦在窗外站了好久的曹丕,都快担心哭了。
她实在不懂,曹丕到底是怎么想的。明明早就过来了,却偏偏要站在这里呆呆的望着,既不进去也不说话,就和傻了一样。
见曹丕依旧闷着不说话,小满抬臂将眼角的泪滴一抹,也不管什么天子不天子了,赌气似的直接扭头就走。
“贵人,您不要喝了。说的是等陛下,您怎么一个人倒喝开了呀!”
小满气呼呼的将柴萱手中的酒杯一把夺过来,斜睨着窗外一直盯着柴萱的那个家伙,着实气的紧。
“他来了吗?”
柴萱单手支着脑袋,涨着泛红的脸颊抬眸望眼小满,却见她的视线并不是投向自己的,不禁有些失落的沉眸长叹。
以往都是曹丕往自己这里跑,自己是挡也挡不住。如今倒好,反而成了自己眼巴巴的盼着人家前来。果然,风水轮流转,该还的一点儿也落不下。
看着柴萱又倒了一杯酒,正要往嘴里送,小满又直接给强摁下来。引得柴萱眉间一皱,莫名气恼起来。
“小满,你干什么呀!”自己本就不舒心的很,如今连被酒都被别人控制着,怎么连一点儿自主的权利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