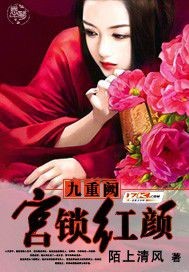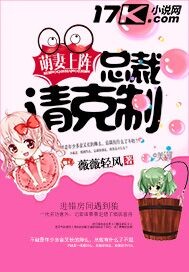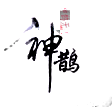和邻居聊天,偶然得知,他家保姆的小同乡——一个偏僻山区的十六岁女孩跳河死了。因为同班三个男生追求她,因为她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们,因为她没有人可以商量,因为她怕告诉别人,别人会以为是她轻浮才惹得男生追求……所以她只好用死来结束这个重大的“麻烦”。
这故事对于城市的少男少女,或许有几分原始和古典,或者有人会说:这种愚昧无知的事情当真发生在九十年代么?
亲爱的读者,我把这个事件作为本文的开头,并非要对女孩子的愚昧和无知进行分析,我只想说,也许我们与她的一切一切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不容置疑:我们都曾有过十六岁;十六岁的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麻烦。
十六岁的我们,分外地敏感,分外地自尊,分外地勇敢,分外地懦弱。我们不再愿意被人称为孩子,我们渴慕成年人面对社会那潇洒、从容的谈吐。如同我们兴趣盎然地关注着缤纷的世界,我们也迫切希望这世界给我们以应有的关注。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我们是新手,却跃跃欲试,急着领到自己的角色。当我们“进入角色”,成年人也乐意倾听我们的心意时,没准儿我们又封闭起自己。封闭是一种自信,自信旁人无法理解我们;封闭是一种畏惧,畏惧是由于我们不知该怎样准确地表达自己。有时,我们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同我们作对,有时我们又忽然要同整个世界作对。我们的心绪每每反复无常,我们的痛苦和欢乐也常常胜过饱经沧桑的大人。朦胧的初恋、淡淡的友谊、刻意的一次聚会、偶尔的一个秘密……都可能成全我们或带给我们伤害。但是,什么也别怕,毕竟我们已经十六岁。
我想起一个挪威男孩雅可夫,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在奥斯陆认识他那年,他十六岁,高中刚毕业。高中毕业的雅可夫高高的个子,一头柔软的披肩金发。他是决意要当一名爵士鼓手的,决心自己挣钱买一套爵士鼓,为此他在一所大学的幼儿园当了一年“阿姨”。最初这“阿姨”的工作令他有点儿难堪,也有点儿害羞。他不愿和从前的同学见面,也不愿同家人在一起聊天——直到有那么一天。那天是他的生日,当他按时来到幼儿园时,全班的孩子每人都为他带来了一件小礼物。他们出其不意地把礼物亮给他,使他感到意外而又激动。雅可夫捧着礼物回到家,骄傲地向家人讲述着幼儿园的一切。我见到了那些礼物,每一件都很小很小,最小的一件仅仅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只小瓷猴。可是,就是它们使十六岁的雅可夫不再觉得难堪和害羞了,幼儿园的孩子们给了他为自己骄傲的勇气。雅可夫坦然地在幼儿园工作下去。他终于攒钱买了鼓,和三个好友组成了一支乐队,到各地巡回演出。他们歌唱青春,也歌唱人类的相互信任。
我把这个故事作为本文的结尾,是想告诉你,亲爱的读者,假如你刚好十六岁,假如你正好有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一定别怕。
相信自己,也相信周围他人的处事能力,特别应该相信,十六岁的人其实和大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