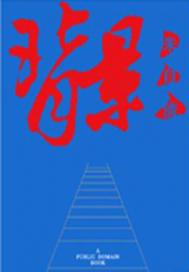我像从前一样,年底逼近了,就忙着去街上选购贺年片。
今年我们这里盛行外来的“卡”:港、澳、台的,美国设计大陆印刷的……我得说这些贺年卡精美、漂亮,内中都印着温柔和热烈的话。可我历来不习惯将机器里滚出来的句子送给我的朋友们,总觉得那实际上是种冷淡的周到。于是我就在各家店里乱跑乱找,希望找到给我留出空白的那么一种贺年卡,让我把我要讲的话写给朋友。最后我在邮电局卖邮票的柜台上发现了它。这不是地道的贺年卡,是一种明信片,一种恭贺蛇年新禧的明信片:正面是稚拙、喜庆的蛇的图案,形式和色彩像武强木版年画;背面还有容我说话的一方洁白天地。正面和背面我都喜欢,还喜欢它的便宜:一毛二分钱一张,连邮票也有了,这年月您上哪儿找去?
我当即买了一些,在路上边走边欣赏我的猎获。这时我才发现手中的明信片原来是两种——营业员在蛇年里头又掺进了几张龙年图案的旧货。平心而论,这“龙图”也非常好看,买时我高兴得花了眼,竟没认出它本不是蛇。也许这不是我的错,欧洲神话里龙原本是蛇的一种,一种大蛇。
然而我还是择出那几张旧货返回了邮局。我请营业员给我退掉“龙图”,口气很有几分恼火,神色中亦有几分因识破了她妄图滥竽充数的伎俩而生的自得。龙年尚未过去,我对龙已惟恐弃之不及了。曾几何时,我不也和众人一样,有过对龙的寻觅吗?
单就龙而言,我自幼就不喜欢它的样子。这并非是对中国神话的逆反心理,故意贬低这皇权象征的神异;也不是受了西方的传染,专门相信龙那邪恶的名声。祖先造就出来的龙形龙体总给我一种狰狞感,而龙头上那两枚鼓凸的眼睛又每每令我觉出狂暴。实在地说,面对各式各样的龙,我的内心从未生发过崇高的激情。这不可救药的心理又不愿轻易暴露,我于是对龙的寻觅便人云亦云了:龙年里寄龙的贺卡,买龙的邮票,看龙举国上下翻腾飞舞,给属龙者送红腰带以避邪……一一地去做。好像你不做、不买、不看就背时就赶不上潮流就不配在龙年里待着。龙年里不爱龙正如同过了龙年居然还有人弄龙那般可笑加傻帽儿,正如营业员在我的贺卡里掺的“假”。我相信换个对龙真心崇敬的买主,这当口儿也照样得把那“龙图”还给营业员的柜台。
回过头来再说手中这蛇的图像,代表十二地支而来的十二生肖里,惟有蛇难对付。蛇的滑腻、阴冷和那无可描写的条状软体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弄得美好。即使在著名的《拉奥孔》里,震撼人心的也是拉奥孔被毒蛇缠绕时那全身心对痛苦的高度控制,以及由这控制而生的骇人的美,却不是蛇的本身。也许您会提到《白蛇传》,可白娘子的美好恰恰在于她从未使我联想到白蛇,没准儿这正是该故事的失败之处呢。与蛇的滑腻、阴冷相比,我倒情愿接受龙的狰狞与暴烈。
可是,这帧有着装饰意味的“蛇图”居然给蛇创出了一个崭新的让你出其不意的形象。首先它色彩的基调就来自民间的原生色:红、黄、紫、绿、黑,蛇一下子有了平民气息。然后是蛇的造型:设计者将那可憎的尖头尖脑的蛇头画得浑圆可爱,细眉高挑着,两只红眼睛像是一副俏皮的红眼镜;而口中那咝咝作响、抖个不停的“毒信”竟变作一枝碧绿、纤细的嫩芽——春的征候;全身披的则是与人亲近的装饰花纹。这是蛇又不是蛇,分明是个你从未见过的蛇族中身着黑花旗袍,幽默、风趣的小老太太或曰蛇的顽童。它的四周有天上的日月、空中的飞鸟,尽是吉祥,它与人类相安并存——蛇年多美好。
你不能不佩服设计者的聪慧与才情。
由此我想起有本书里对一群不辨黑白的顾曲家的形容,顾曲家是该书作者笔下那些欣赏声乐的“行家”。作者说那些顾曲家“顾曲”时是做好了准备在某位大歌唱家一开口便晕倒的。蛇年不是大歌唱家的演唱,迎蛇年是中国民俗之必然——十二年一轮。人可以在龙到来之前就起劲地做些晕倒准备,而面对蛇这个难对付的家伙,谁也不知会出现什么尴尬局面。因此“蛇卡”设计者不曾料到有谁会晕倒在这条软体动物面前,他只是用自己的才智将蛇迎进了民间,他成功地迎来了蛇年。我之所以想起顾曲家的晕倒,是觉得这种准备性太强的晕倒预谋得有趣。仅这一点,有点儿像我们对十二生肖中龙的奉迎。
我们有时会在各个领域看见些许忙着做晕倒准备的预谋者,我们得承认这些人能够在没听清他们的晕倒对象开口说些什么时就晕倒,这本身就是一种本领。这晕倒又分为高级与初级,我以为我随着龙年说龙而内心毫无感受便是初级晕倒;高级晕倒者在晕倒之后还会创出些晕头晕脑的文字,如那些顾曲家对大歌唱家不着边际的云山雾罩。歌唱家唱了什么并不重要,也许他根本不在歌唱,只是一声咳嗽;也许他唱的正是那晕倒者感到的费解之处;也许他未等开口自己也先晕了过去。
我不敢口出狂言说我们都做过那样的顾曲家,我想说面对龙我们是不是都曾做过晕倒的准备。
龙作为一种自身有着极大不确定性的文化物,你尽可以随意揣测、评说;你尽可以去琢磨那龙的四种:披着鳞的蛟龙,生着翼的应龙,长着角的虬龙,没有角的螭龙。你可以沿着西方类书注重事物本身特点的宗旨,将龙划归为古生物类;也可按照中国古代类书注重事物象征意义的习性,用平行分类法把龙划为皇族类,如同古类书不把蝗虫归虫类,却归入灾害类那样。对于龙的想像是没有穷尽的,有时我觉得龙也许就是一条黄花鱼,相声里有个小伙子就属黄花鱼。
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十二生肖的迎送和顾曲家对于大歌唱家的晕倒,终归有着本质的不同。面对新的一年,“蛇卡”设计者预先的激情能使他造就出一条全新的蛇;而顾曲家预先的晕倒却是一种慌张得近似于上蹿下跳的投机与懒惰,这晕倒对歌唱家自身的造就毫无意义。懒惰也是一种激情。不是吗,当你面对一片晕过去的人,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跟着一块儿晕。虽然这晕倒对歌唱家自身的造就毫无意义,但晕倒者越多歌唱家则越大,于是在晕倒者那懒惰的激情之中凸现出来的大歌唱家像是诞生于他们的眼力他们的耳朵。
云如潮时,便有龙在空中腾云驾雾地运行;当晴空万里的苍天将一张耐下性子的真切的脸与大地对视时,龙呢?
我走在薄雪融化、蓝天朗朗的大街上,怀揣我的“蛇图”想着应该寄谁。因了天的纯净,我才隐约地感悟到那纯净的深邃与不可估测的绚丽丰富。而一个人面对一支歌、一首诗、一篇小说、一个人物,总如顾曲家那般预先地晕倒时,他认为最深邃的世界莫过于他那晕倒的本身吧。天上是不是有云如潮?
云晴龙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