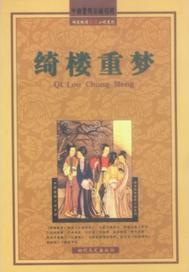有一年六月,我在挪威参加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我的朋友、挪威汉学家易德波在这期间一直做我的翻译并照顾我。易德波是一位诚实的中年女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学习汉语。她和她的丈夫——一位妇科医生以及三个儿子,住在奥斯陆近郊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我曾经几次在易德波家吃饭,临近回国,我想我应该对这好客的一家表示感谢。倘若请他们全家去餐馆、酒店吃饭,未免过于客气,而且也太贵。
我窃想,最重要的是那些地方仍旧是他们习惯了的口味,并不新奇。要是在她家做一次中餐呢,当然会大受欢迎。可是我观察过易德波家厨房的器皿和灶具,她的平底锅和电炉盘都不适合中国菜的烹饪。再说,奥斯陆也没有为我特意准备中国菜的原料和调料。这时我忽然想起我家夏天常吃的一种饺子。
每年夏季,西红柿最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做西红柿馅儿饺子,可以说,这是我的发明,西红柿饺子的主料是西红柿、鲜猪肉、鸡蛋、葱头。这些东西也是西菜烹制中常用的,不必担心超级市场没有。假使要做北方人吃惯了的猪肉白菜馅儿饺子,不但白菜没有,就是中国大葱我又能到哪儿去找呢?于是,我决定为易德波全家做一次西红柿馅儿饺子。
饺子这种中国北方的大众食品,一直令外国人不可思议。不必说各种馅儿的调制,单是擀饺子皮的过程就令他们感到美妙。而中国人感到美妙的,则是包饺子本身所体现出的家庭亲情,一种琐碎、舒缓的温暖。我愿意把这种情绪带给易德波全家,我愿意我们共同享受东方这古老的热闹。当易德波九岁的小儿子听了我要包饺子的宣布之后,一天拒绝吃饭,耐心等待着晚餐的中国饺子。
我从超级市场买回原料,如我猜测的那样,主料都有,只差海米没买到。但易德波及时向我提供了鲜虾仁,这岂不更好?
我开始了我的制作:先把西红柿洗净,放在盆内用开水烫过(便于剥皮),剥掉皮,挤出汁和籽,再把西红柿剁碎。当我刚刚拿起一个西红柿,把汁和籽挤进洗碗池,手下就飞速地伸过一只小碗,是易德波站在了我的身后,好让我把西红柿汁挤进这小碗,她说这是好东西啊,扔进洗碗池太可惜了。结果我挤了多半碗西红柿汁,易德波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藏进了冰箱。她没有因为当着一个外国人表现得如此“抠门儿”而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不禁问自己:假使一个外国人在我家厨房烧菜,我能够无顾忌地面对她去表现我的“抠门儿”吗?
半碗西红柿汁并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它却是北欧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节俭品德的体现。节约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习以为常的,因此易德波才十分坦然。有了这碗储进冰箱的西红柿汁,我的包饺子过程似乎才完整起来,才真正有了一种家庭的亲情。那时我指挥着易德波和她的丈夫,他们摊鸡蛋、剥葱头,虔诚地为我打着下手。那时厨房里似乎不存在外国人和客人,我已加入了这个家庭,与他们一道过着真实的日子。
我成功地制作了西红柿馅儿饺子,易德波全家吃得满面是汗。她的小儿子一边吃一边数数儿,最后告诉我说,他吃了三十六个。
易德波的节俭给我留下了比饺子本身更深的印象,但我仍然没有忘记请读者也来试一试西红柿馅儿饺子。饺子的形式万变不离其宗,但它的内容却可以不断丰富。丰富你的菜谱,便是丰富你生活的情致吧。此外,当你偶然地主持过一个家庭的烹饪,你还会获得一个了解这家庭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