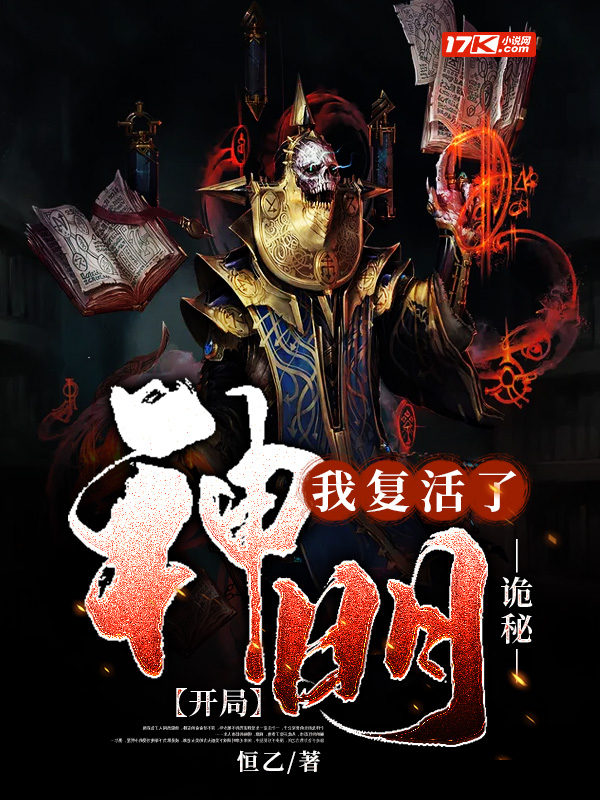三年前路过武汉,是同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去麻城的一个乡村制作节目。正是春天。在汉口下车后,便有麻城市委宣传部的同志驱车从麻城赶来迎接。已近中午,好客的主人领我们去“老通城”吃豆皮,当然还吃了很多别的——因为在主人看来,豆皮不过是点缀席间的小吃吧!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豆皮,以及迎门的一块匾额上毛**那句随意而又不容置疑的话:“这家的豆皮最好吃。”至今我仍然觉得,若以广告而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语中,几十年前毛**这句语录那不加修饰的理直气壮和质朴之至的口语感,实在是独领风骚,与美国总统曾为雀巢咖啡说过的那句著名的“味道好极了”各有千秋。
当年的冬天,武汉话剧院的一位阿姨——父亲少年的女友,后来的大学同学,乘火车去北京探亲时,便特意拍来电报告知我们,她将带来我爱吃的豆皮,车过石家庄时,希望我们进站去取。这阿姨乘坐的火车到达石家庄时正是深夜,那夜父亲准时进站迎接了豆皮。阿姨虽离故乡已久,却仍保留着冀中人的憨实——她竟为我们装了满满一锅豆皮。这锅是那种已不时髦的中型钢精锅,四周还残存着烧饭、煮汤久了而形成的焦垢,使沉甸甸的豆皮格外地富有暖洋洋的家庭味儿。我珍惜阿姨这远来的心意,学着冷冻比萨饼的方式把豆皮们做了小包装,储进冰箱的冷冻室,吃了许多天。
从没有问过这豆皮是否是在“老通城”买的,只想把“老通城”匾额上毛**的评价稍加改动,变成“阿姨家的豆皮最好吃”,似乎就因为,它们被装在一只活生生的生活中的锅里。
又记起从武汉返回北方时,坐在汽车里看街边那一对一对卖米粑的夫妻,也不知为什么这米粑尽是由夫妻们一道来卖。或许因为米粑需要边制作边出卖,类似我们北方的摊煎饼,而制作出卖是少不了双人配合的;或许这样的生计需要夫妻做伴,这样的夫妻也乐意在做伴的生计中向大街展示他们的婚姻:忽而女人向男人做出“茶壶式”——一手叉腰,伸出另一只手指责男人;忽而男人又向女人做出“剪刀式”——双手叉腰不买女人的账;忽而夫妻双双笑逐颜开:一群学生拥上来买米粑,生意好起来了。春天的细雨使他们面盆中那发酵的米粉浆发出特别湿润的香气,这大街上的婚姻就是如此简单、明了。
去年十月又来武汉,是在第六届全国书市参加“布老虎丛书”的签名售书活动。原以为在时代的物欲和功利色彩愈来愈强烈的背景之下,买书的人不会很多,却意外地发现武汉的读者对阅读抱有那么高的热情。我们被安排在书市二楼迎门大厅的入口处,连续两天为读者签名卖我们自己的书。我已熟悉这套丛书中我的那两本:《无雨之城》《河之女》,它们的封面也不知被我的手摩挲了多少遍。后来在拥挤的读者和拥挤的书中,忽然有一本封面陌生的书被举到我眼前,这书的主人——一个腼腆的女孩子要我为她在这本书上签名。我仔细看书,方知这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的一本小说集《甜蜜的拍打》。看到一个陌生人拿着一本自己尚不知道的自己的新书,的确会有几分惊喜之感。我在这新书上签名之后,问女孩子这书是她在哪里买的,女孩子说就在一楼大厅。我半开玩笑地说一会儿我也要下楼买一本我自己的书。女孩子听后挤出人群走了。过了一会儿,我眼前又出现了一本《甜蜜的拍打》,想是又有人从楼下买了上楼来让我签名吧,我便头也不抬地打开了书。扉页上已经有几个稚气的钢笔字了:“赠铁凝……”落款是徐立。
这徐立便是刚才那个女孩子了。她是听了我刚才的玩笑话,特意下楼再买一本我的书,送给尚无书的我的。我抬头找徐立,排队的人中已无徐立。即使有,我想我也是认不出她的,这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普通到我根本不记得她的模样,普通到她可以随时被淹没在人群里。
身边的崔京生告诉我,他记得这个徐立的样子,因为徐立在把书悄悄放到我手边时,看了他一眼。崔京生说那是叮嘱的一眼,用眼睛叮嘱他把书送到我的手上。
又在武汉一天,书市仍旧熙熙攘攘,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徐立,我甚至觉得她是有意躲开了这里。她没有夸张自己对小说的热情,也没有刻意寻求与作家交往的机会。在偌大的展览大厅里,她只是用心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又在武汉一天,没有来得及去吃豆皮,也没有来得及再看街边卖米粑的夫妻。见到明亮的黄鹤楼址,宏伟的长江大桥,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武汉的许多好东西。回到家来,不断记起的却还是那盛在钢精锅里的豆皮、街边卖米粑的喜怒无常的夫妻,还有那个不知模样的徐立。
他们不是一座城市的骨架,却肯定是这城市的血肉。没有血肉,城市的温暖又从何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