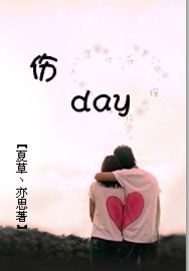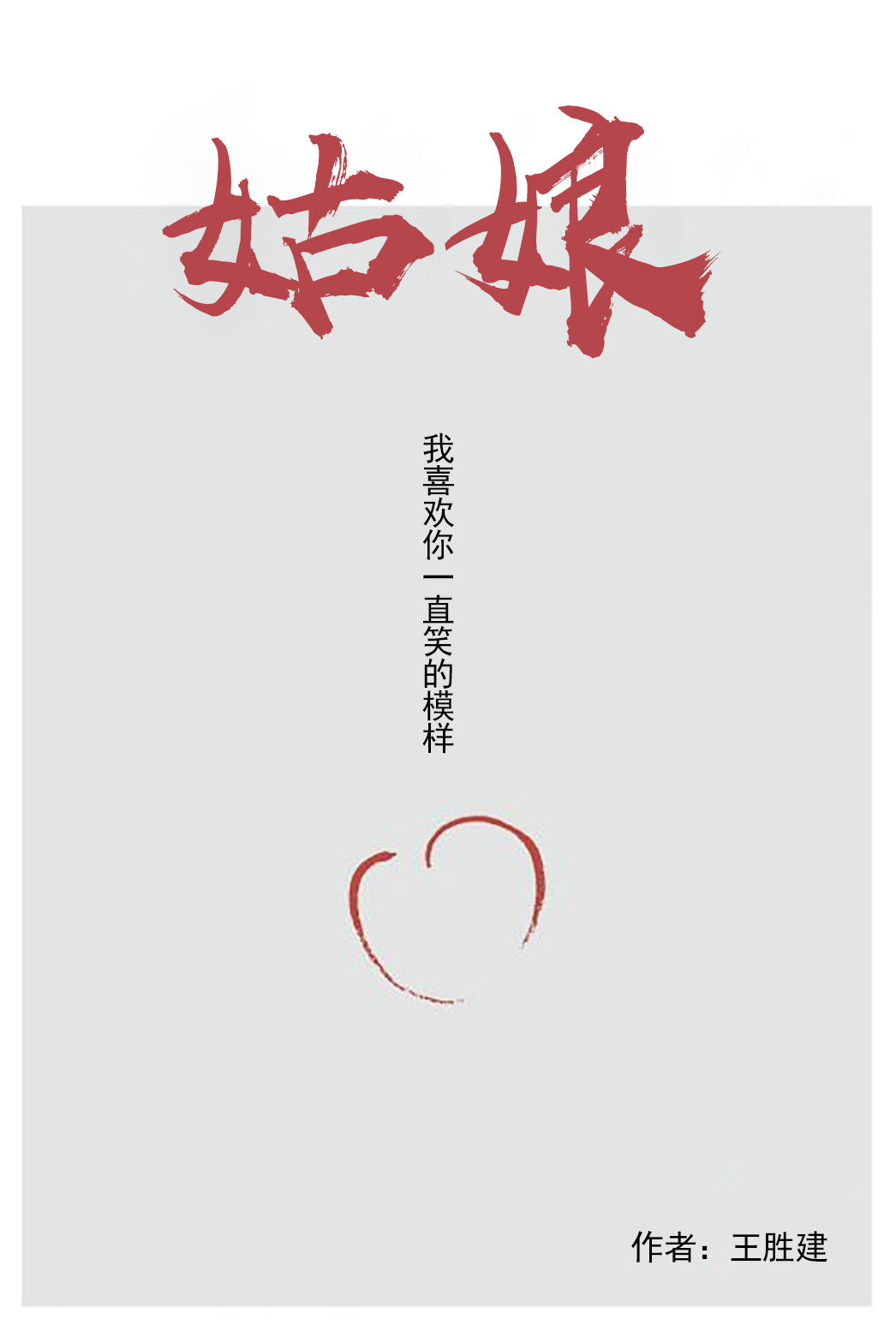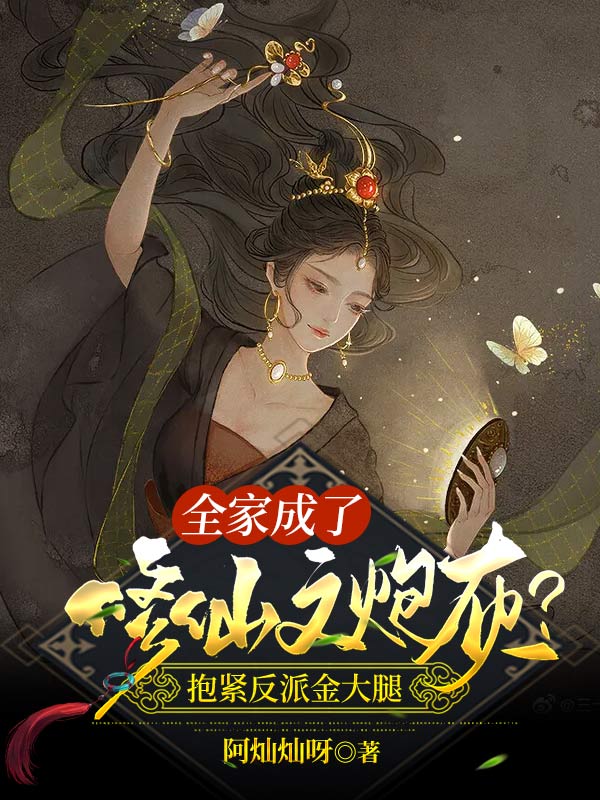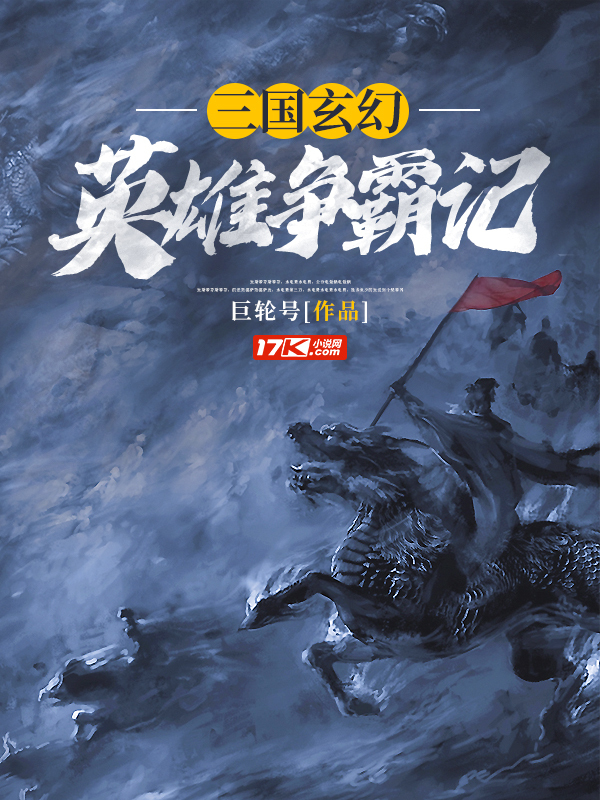一九九○年冬天,我曾经在一个名叫娄村的乡里住过一些时间。
娄村乡地处保定西部山区和平原的接壤处,属于丘陵地带。安静的公路时有舒缓的起伏。公路两旁,是土质肥厚的麦地和错落有致的青石板铺顶的砖房。这些农民的房子大都很新,有些房主刻意在门面上做些“雕梁画栋”般的装饰,显示着这里的富裕,也给冬天沉寂的原野平添了许多颜色。
我被安排在乡政府,占了乡文化站的一间屋子。屋的主人是个年轻女孩,因为我的到来,她暂回家去住了。幸好她家离乡政府不远,只有一里地。我走进我的临时小屋时,那女孩子显然刚刚离开:桌椅都很明亮,打扫过的砖地上还散布着泼洒均匀的水痕,使这陈设简单的小屋充满湿润的馨香。我想那女孩子定是用香皂洗了脸,又就势将洗脸水洒到地面上的。在乡下,很多勤快、利索的女性喜欢用这种方法保持房间的干净和空气的清新。我把随身带来的行李解开,铺在女孩子为我腾空的铺板上。这时院里响起钟声,晚饭时间到了。
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领我去食堂吃晚饭,我就势将这院子看了个大概:几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院子正中有一个水管,厕所在东南角,墙外便是大片的野地了。房子不新,大约建于五六十年代,每排房子前都有些落尽了叶子的杨树、榆树,像许多北方乡间的院子一样。
食堂在院子的西南角,由一名姓姜的师傅主持。我被领进食堂,书记微微猫下腰,把脸凑在打饭的小窗口,将我介绍给正在里间卖饭的姜师傅,我也招呼了姜师傅。
姜师傅是一位高个子、长脸的老头,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裤军褂,头上是一顶耷拉着帽檐的旧军帽。对于我的招呼,姜师傅并没有过于热烈的反应,只说:“闺女,有馒头,有糖包,你吃什么?”我说什么都行。姜师傅说:“吃个糖包吧,把碗伸进来,闺女们都爱吃甜的。”他把一个热气腾腾的糖包放进我的碗,又为我的另一只碗盛上同样热气腾腾的粉条豆腐菜。
人不论在哪里,肚子里有了甜的热的东西,心就会踏实下来。我吃着糖包和热菜,院子也跟着黑了。入冬以后,天黑得很快,黑得很透。我打着手电和书记、乡长回我的小屋。在门口,书记指着一堆煤面和一堆黄土说,每晚睡觉前我都应该和些煤泥封火。这时我才想起,我的屋里有一个红砖盘就的自来风煤灶,那么,我还得学会封火。乡长绰起铁锹,为我示范了和泥要领,并告诉我说,煤面和黄土的比例是三比一。
书记和乡长走了,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坐在我的铺上,望着因年头久远而发黄发脆的顶棚,顶棚是用报纸糊的,报纸上罗列着七十年代末的一些新闻。看了顶棚我又环顾四壁,四壁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电影明星剧照和生活照,照片也因时间久远而褪去了许多颜色,比如那些本来涂着口红的唇们都一律地苍白着,使主人公看上去睡眠不足,精神委顿。我端详着明星们,猜测着哪一位是这房间的主人最崇拜的。我无法说清为什么我会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长时间地东瞅西看,似是排遣这突然到来的寂寞,又似是为了消除这近在眼前的陌生——这确是一种陌生,尽管四周有一大群公众熟识的电影明星相伴。
也许陌生感最容易调动起人的警觉吧?我想起挎包里的手枪。这手枪是行前一位友人借我的,他告诉我这是防身用的电击手枪,不会致命,充其量也就是壮胆。真有用时,一定要等歹徒靠近,将枪口抵住他的皮肤,才能把对方击倒。友人的介绍反倒更让我害怕,试想,当一名歹徒真的出现在眼前,我怎么可能有时间等他靠近呢?等待歹徒靠近,需要耐心和胆量,我自信自己缺乏这样的耐心和胆量,因此手枪于我,或许就真是个壮胆的摆设了。我从挎包里掏出枪来,模仿着某些电影里的场面,将枪压在枕下,开始了我在娄村第一夜的睡眠。
半夜里我要去厕所,于是穿衣起床,把自己武装起来:披上军大衣,衣兜里放好手枪,手中再亮起手电,推门出来,走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从我的屋子到厕所要穿过整座院子,想到厕所与野地只有一墙之隔,我甚至觉得歹徒说不定就潜伏在墙根暗处。我一边用想象出来的危险恐吓自己,一边又攥住大衣兜里的枪柄壮自己的胆,盘算着当意外发生时我应该先闭手电还是先掏手枪。
除了寒冷和寂静,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我走出厕所,发现这院子不像刚才那么黑暗了。西南角有灯光,那便是姜师傅主持的食堂了。大半夜他在食堂干什么呢?
我没有再回屋睡觉,打着手电拐进食堂。厨房里暖烘烘的,有热气从焐着的锅里冒出来,姜师傅正坐在灶前抽烟。他告诉我说,他正等人回来吃饭。
原来这季节税收工作正紧,乡里的干部们被编成十几个小组下去收税,常常早出晚归。这种晚,晚到了没有时间,有时一天要开二十几顿饭。为了让人们回来就能吃上热饭,姜师傅索性昼夜坐在灶前。我出主意让姜师傅回去睡觉,谁回来谁再去叫姜师傅。姜师傅却说,做饭的理应等着吃饭的,不能让吃饭的去叫做饭的。转悠一天,再遇见点儿不顺心,一顿热饭一吃,也就过去了。
税收是件麻烦事,大约顺心的时候不多。在以后的几天里,有时候我碰巧和收税干部同路归来,他们一边向我唠叨着这差事的艰辛,一边又说:“幸亏回去能吃上口热饭,姜师傅等着咱们呢。”
姜师傅坚持着他的等待,食堂的灯光彻夜长明。白天的时候他照旧做饭、洗菜、敲钟——这时我知道,挂在食堂前榆树上的那口招呼人吃饭的钟,一直由他亲自敲响。哪怕这院里的干部倾巢出动去收税,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等待吃饭,姜师傅也要单为我把那钟按时敲起来。他敲得有力,从不潦草。
有一天全体乡干部因事出门,我也要去附近的一个村子采访。这天的午饭,只有姜师傅一个人吃。中午,当我盘腿坐在那村里一个乡村医生的炕上吃饭时,却听见一阵钟声。钟声悠远,但听起来依然有力,且不潦草。这,当是姜师傅。
晚上回到乡政府,我问姜师傅,是不是中午又来了吃饭的人,姜师傅说只有他一个人。
我说您一个人吃饭还自个儿给自个儿敲钟?
姜师傅说我是敲给你听哩,虽在村外,也能听见,派饭也得按时吃。你们这种人爱和人聊天儿,别聊起来没完忘了吃饭。
我忽然觉出娄村的一切于我已经很亲切了,我甚至将手枪送回了挎包。半夜再穿过院子时,脚步也从容自如起来,有时连手电也扔在床上不拿。
在文化站我那临时的小屋里,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体味着被人惦念的幸福,品尝着惦念别人时内心的丰富。或许姜师傅不识太多的字,或许姜师傅终生不读我的小说,但作为写小说的我,每每提起笔来,却常惦念起姜师傅。
人类的生存是需要相互的惦念的。最高尚的文学也离不开最平凡的人类情感的滋润。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问清了姜师傅的简单历史。他是个复原军人,在乡里做了四十年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