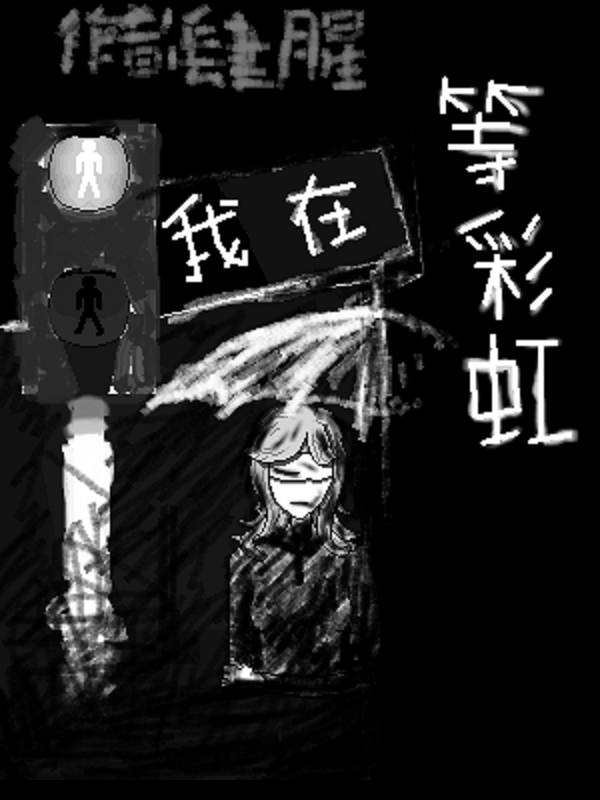那时我在《花山》做一名小说编辑。那时保定地区文联的文学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觉得《花山》这名字响亮又灿烂,但编辑部所在的小楼却是陈旧的。一层不断更换着单位,从机关到商店;二层属于我们。脚下的红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筑中虽不多见,但因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开始松动,就像老年人那些松动的挤不紧的牙。
楼房临街,盛夏时那些卖冰棍卖西瓜的叫卖声悠悠地飘进窗子,仿佛紧凑着你的耳朵引诱你。看稿看累了我们就下楼买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编辑部充满着一种热闹的人情味儿。西瓜就在办公桌上切开,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却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发或者待退的稿件。待发、待退,我们一样珍惜。
也许我说小小的编辑部并非过分:几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在外地的编辑的单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饭。于是家庭气味和办公气味混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产甜面酱,单人床下边就有了当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办公室结婚生子,于是婴儿的尿布如万国旗一样悬在了迎门。居住条件的窘迫造成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的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远离人间烟火。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小楼也有清静的时候——过麦了,过秋了,过春节了,我那些家在农村的同事便会骑车奔回家去。过后他们又会带着一身被太阳慷慨晒过的气息奔回小楼,付出双倍时间处理桌面上的积攒。那时一个人会干几个人的活儿。刊物按时和读者见面了。
在《花山》,我认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编辑,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要算是外出组稿了。从前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曾经对我说,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组稿,这意味着你要看作家家人(或专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脸色和由那脸色演变出来的一些动作,如清扫床铺做即将休息状,整装看表做因有急事要出门状。她的感触似乎使我受了惊吓,使我优先体味着编辑在某一瞬间的悲凉。幸好我的两次外出组稿都与主编郝建奇同行。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称他郝主任)给我讲述了他在农村被专政的种种遭遇。他的经历催人泪下,他的经历使我为他脸上额上那些纵横的皱纹找到了出处。也许那曾是欢乐开朗的一张脸,岁月在那脸上印下了无法抹掉的哀伤,于是乐观、开朗、哀伤便集于一脸了。加上他那朴素、随意,有时显出背时的服饰,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从县区来的基层干部。这一切使我的虚荣心不时闪烁。天津的无轨电车载着我们不分东西南北地行驶,我只是一叠声地唤他“郝主任”以表白我们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我恐怕车上的人将我们误猜成来天津卫串亲戚的乡下父女。他并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在拜访作家时,我也请郝主任一人先去登门。有一天,他在看过他的老战友、著名女作家柳溪后,回来气色很好地说,在柳溪家他吃了红烧鸡块。还说,柳溪知道我来了,一定让他和我再去她家,她要为我再做一次红烧鸡块。这意料之外的邀请使我特别高兴。我想也许我是幸运的,以当时我那普通编辑的身份,我没有领受名作家“清扫床铺”或者“整装看表”,我得到了一份平等相待的真诚。这使我对自己产生了信任。第二天,我们一同去看柳溪。一路上我回想着她小说中许多好听的句子,诸如“我们花着社里的钱不能像拔着不疼的牙”等等,在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摆着她那大三十二开本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可惜后来我和郝主任迷了路,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乱走。郝主任居然指示我狠敲两扇紧闭的大铁门说这就是柳溪的院子,我却怀疑那是两扇久已不开的大门。郝主任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那眼神分明在告诉我:敲吧,这门里定有平等待你的诚恳。我拼命敲起来,直到我扒着门缝看见紧贴大门堆积着十几个肮脏的垃圾桶时,才说服郝主任这门肯定许久不曾开过。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院子,柳溪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饭桌旁认真等待。小屋里弥漫着鸡肉的香味,桌子正中有一只沙锅,鸡块就盛在那里。
我对编辑工作渐渐认真起来,我不想说那纯粹是因为吃了一位女作家的红烧鸡块。我相信以诚相待的魅力,当年郝主任鼓励我拍门本身就是一种诚恳了。这使我对自己在电车上的那份虚荣觉出了不自在。
第二次外出组稿在次年初夏。这次的目标不是名家,是山西大同地区一个山野小县的两位作者。郝主任从来稿中发现了这小县里两位作者的潜力,于是便生出找到作者与他们面谈的愿望。我并不了解如今编辑们对于一般作者的组稿方法,只觉出郝主任的愿望委实有些崇高。《花山》虽小,却也不至于就缺外省两位不知名作者的稿。请他们前来改稿也不算不礼貌吧?我们却直奔他们而去了。
路不太顺畅。先乘火车到大同,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赶到长途汽车站买汽车票。票是买到了,但上车后才发现我的座位已被没有座位号的一个男人抢先占去,我知道我们要坐五个小时汽车才可到达那个小县,于是坚持要那男人让出我的座位,他却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这使我非常气愤,这气愤甚至令我想到了此行的多余。是谁使我站在人声嘈杂的汽车上同一个不讲道理的男人争吵?是郝主任和他的计划。当我看见郝主任对那男人的恼怒更甚于我,并且执意拉我坐在他的座位上时,我才停止争吵,硬挤在那男人的身边坐下来,这座位是汽车的最后一排。
这是一条漫长的乏味的大颠大簸的道路,那颠簸的剧烈使人觉得肝肠寸断。有一段崎岖的路曾使后排座位的全体旅客在座位上有节奏地不断蹦跳,而我们的头顶就险些与车顶相碰。这种古怪的形体变异却莫名其妙地缓解了我对那不讲理男人的憎恨,我们忽然笑起来。那原是一个欲哭的苦笑,仿佛胳膊肘被撞在桌角时那一瞬间的心理感受。而笑的本身却把被颠簸起来的怒火化为不期而至的幽默,这幽默就溶化了我那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我的心情好起来,在目的地我们见到了那两位憨厚的作者。
我记得作者请我们吃莜麦面“猫耳朵”,请我们吃一种很香的吃不黑嘴的葵瓜子。当我看见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深受感动时,当我看见郝主任同他们把稿子的修改意见谈得那么具体时,我才觉得此行并不多余。
并不是每一个被寻找的作者都能成为作家,并不是每一次寻找都能大见成效都能抓住刊物所需的头条。那两位作者如今还写吗?我不知道。他们还记得那年与我们的相聚吗?我不知道。但我从来也没后悔过那年夏天跟随郝主任对他们的寻找。刊物与作者的感情就是这样产生的吧!《花山》的小楼上有婴儿的尿布有本地的甜面酱,更重要的是那个编辑部里有编辑们热忱的愿望,有人们力所能及的一份认真。
如今《花山》已经离我们而去,代之而来的是《荷花淀》的诞生。《荷花淀》仍然在那座旧楼里,主编仍然是郝建奇。这使从前的一切突然近在眼前。虽然我早已离开那座小楼,虽然我已许久不做编辑,但我仿佛又要跟着郝主任外出组稿了。我还会站在天津的解放南路去拍那两扇永远也拍不开的大铁门么?我还会在外省的长途汽车上同不相识的男人吵得面红耳赤么?当我远离了从前的一切,才发现在《花山》的日子里我曾经收获的并不仅仅是一名编辑的职责和本分。
也许我不再能做一名好编辑,可我相信,崭新的《荷花淀》里的新人们将比我做得好。那满塘荷花该会在夏日里盛开吧?那娇而不媚的清秀该会令人耳目一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