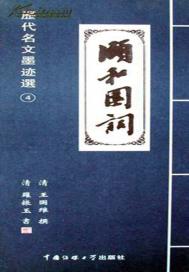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在台北访问,拜会了长久以来就敬慕的作家林海音先生。那是让我难忘的一天,先是在林海音家中与她聊天,然后她又请我们几位去一家德国馆子吃西餐,她特意为我们叫的香蒜明虾至今我还回味无穷。饭后,我们又去了林先生的纯文学出版社。当时的台北很闷热,七十三岁的林先生因为陪我们又不得午休,可是这位身着花色淡雅的中式套装的雍容端庄的小老太太,精神抖擞毫无倦意,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还穿着一双秀气的高跟鞋。林先生的行动和思维都是敏捷的,在她的出版社里,她签名送我几部她的著作,其中就有未经删节的原版《城南旧事》。接着她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随便挑选她这里的书带走。我选了这套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书诗的《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全套共六本,图文各四百五十幅。林海音在书前的序言里写道:“《护生画集》的流布,始自半个世纪前的民国十八年。丰子恺为他的老师弘一大师的五十岁画了五十幅护生画,每幅画都由弘一法师自己题词。十年后是弘一大师六十岁,丰子恺绘六十幅以祝,仍由弘一大师题字六十幅。自后他们师徒二人便相约以后每隔十年续绘一集,即:七十岁绘七十幅,八十岁绘八十幅,乃至九十、一百……以达功德圆满之愿。但是没有想到弘一大师在第二集印制后不久,便于民国三十一年六十三岁时在福建泉州去世了。这时正是对日抗战期间,虽然大家都在逃难,但是丰子恺并未因此停止已许的愿,在颠沛流离中仍继续作画……民国五十四年,即一九六五年,大陆上‘*****’起,文化人无一幸免,丰子恺当然也遭清算……即便如此,丰子恺一方面遭清算,一方面在暗地里,仍然继续画他的护生画,设法寄到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处,所以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都在海外由广洽法师募款为之印制。当初丰子恺也曾考虑过,如果每十年一集,画到第六集一百幅时,他已经八十二岁,是否能如此长寿呢?所以他便提前作画,果然第六集的出版,是弘一大师百岁冥寿的一九七九年。但是丰子恺却已于一九七五年七十八岁时去世了。他未及见到全集的完成。”
我一向喜欢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和漫画,一次在奥斯陆和一位丹麦汉学家闲聊,还得到他所赠的一册丰子恺散文集《缘缘堂集外遗文》,内中一篇名为《优待的虐待》的文章里那种丰子恺式的幽默真让人心生喜悦。他的画亦有他的散文的气质,那似是一种浑朴中的优美,散淡中的机智,纯正的童心里饱含着大的人生悲悯,看似平凡的小角落里处处可见温暖清新的爱意。《护生画集》顾名思义便是爱护生命,其中丰子恺又着重描绘了人类对动物的爱护或者轻视。他的命题是大的,落笔却别致有趣。比方这幅《生的扶持》,一只缺了足的蟹被它的两位同伴奋力抬着前行。弘一法师在旁有诗云:“一蟹失足,二蟹持扶。物知慈悲,人何不如。”丰子恺寥寥几笔,就把这三只团结向前的蟹画得充满了人情味儿,有那么一点悲凉,但你看那些舞蹈着一样的蟹爪们想要摆脱困境,这不是在齐心地做着最大的努力么。再来看这幅《暗杀》,这个人类最通俗、最多见的打苍蝇场景,因为丰子恺换了视角,便足可以被叫做暗杀了,暗杀都是要蹑手蹑脚的。今天的一个时髦词汇叫做“创意”,套用这个词,则类似《暗杀》这样醒人头脑的创意在《护生画集》里数不胜数。比方丰子恺画一穿棉袍者手拎一只蹄髈走在年关的街上,一只小猪跟在那蹄髈后边。画名曰“我的腿!”比方他画在厨房一角两只灶眼里扑出火苗的灶台前,一长凳上摆有一盆水和几条鱼,画名曰“刑场”;画面上有一盒刚打开的鱼罐头,他冠名为“开棺”;一头耕牛卧在柳树下,他把这称为“牛的星期日”;在一幅名为《盥漱避虫蚁》的漫画中,母亲嘱咐正站在院子里刷牙的孩子,不要让漱口水袭击了地上的小虫;还有一幅蚂蚁搬家的画,孩子看见蜿蜒曲折的蚂蚁队伍,便在这队伍的上方排起一溜板凳,说这是长廊,能为蚂蚁遮挡风雨;还有一幅画叫《游山》,画中一女子骑着一只狮子悠闲地在山路上走,画意是说,人如果对猛兽善,兽也会如此柔情,也会与人和平共处的。这真是丰子恺先生的美梦。好莱坞的电影《狮子王》比丰子恺先生这美妙的梦还晚了半个多世纪呢。
也许有人说,因为丰子恺是佛教徒,所以他对“护生”格外有兴趣。这是有道理的。但以此涵盖他生命哲学的全部,好像还是简单了些。也曾有人在读过《护生画集》后,说这是自相矛盾的画作,作者叫我们不要杀生和伤害动物,又叫我们不要损害植物和小草。人类的生存怎么办呢,难道让我们去吃沙土和石头么——就是沙土、石头里也可能有动物、植物啊。对此,丰子恺这样回答:“护生者,护心也。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之,残杀动物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而不是为动植物。”这就是前边我所说的他的大命题了,他的可贵在于用最“浅显”的形式将它表达出来,如同他的佛教观那样朴素易通,那样活泼生动。此外,《护生画集》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欣赏价值也值得读者注意。丰子恺以简洁、稚拙、不事雕琢的线条勾勒出了那些只属于他的形象,他的画风影响着中国的后辈漫画家,包括在今天已成前辈的那些大家。
幸好丰子恺先生没看见我在台北的德国馆子吃虾的吃相儿,那可是在吞食动物啊。也幸好我自以为读懂了《护生画集》,便不再为此心虚。游走在丰子恺为读者创造的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情境之中,我格外想要护好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