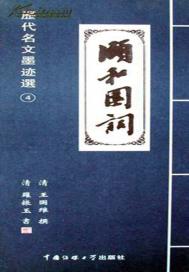那一年,同许多作家一起,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又在德国各地转了一大圈,等到顺访法国巴黎时,已是离家的第四个星期。
其实从下飞机吃过第一顿饭开始,浑身就有点儿不对劲,也说不上哪里不舒服,反正是不舒服。过了时差反应也没有晕机晕车,可就是身虚腿软的老打不起精神。老觉着饿却没有食欲还有点恶心。第四个星期,不适感愈发强烈,身心均空空荡荡。原以为自己适应性挺强,便不由怀疑脚下的地球究竟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
在巴黎,和舒婷一同住在一位法国朋友家里。
那朋友家的女主人去了罗马,朋友就宣布说,这一周的厨房可以由我们支配。厨房宽敞清洁,炉具、餐具、冰箱、洗碗机一应俱全。过了三周的旅馆生活,家庭厨房突然勾起一种遥远的亲切。我和舒婷东摸摸西瞧瞧,不约而同去开冰箱的门。
我们都有点失望。是的,我们两个人好像都在寻找同一种东西。我们谁也没有问谁,可我们关上了冰箱门又去开食品柜的门。
朋友走过来说:咖啡在这儿,牛奶在那儿,还有奶酪、果酱、鸡蛋、面包……
我们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继续东张西望。
朋友不解地说:我们只是在这儿做早饭,你们还需要什么?
我看舒婷,舒婷看我。
我说:我们想找一点儿米……
舒婷噗地笑出声来,连声说:是的是的,我们只想找一点儿米。
朋友就傻傻地愣在那儿。他的汉语很不错,可他还是问:什么,请你再说一遍。
我们就又重申了一遍对于米的渴望,还顺便描述了一下那种白色的大米的形象特征,最后尽可能简练地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朋友似乎是听懂了。然而他的表情却越发地困惑起来。
他说:“我已经说过,我们不会在家里吃午餐或晚餐,我们不需要大米。如果你们想吃米饭,我们可以去中国人开的餐馆,好吗?”
舒婷终于忍不住叫起来:“不,不是做米饭,我们要烧粥,粥,明白吗?”
我禁不住大笑:“是的,我们想喝粥,就是稀饭,我们早餐要吃稀饭,我们已经想了三个星期,我们忍无可忍啦!”
朋友恍然大悟,也许是更加困惑。但西方人尊重他人的习惯使他不得不对我们这一特殊要求表示理解。他嘟哝说:“好了好了,吃稀饭,可是我不知道夫人把米放在哪里……”
那时候舒婷已经奇迹一般地从食品柜角落里,拽出一袋包装精美的泰国大米。我们如遇救星,三呼万岁,兴奋程度绝不亚于非洲饥民望见空投食物。我们相视而乐,松一口长气。彼此的目光里都有些对于我们理想之共同和配合之默契的庆幸和惊讶。自然,身在异国,喝粥也得有个粥伴才是。
第二天两人早早起来,一本正经地淘米烧粥。锅开之后,缕缕热气在厨房升腾缭绕,如一双温柔的手,将满腹心思抚顺捋平;情绪就渐渐舒展起来。听着锅里的米咕嘟咕嘟地翻滚,觉得那个早晨无比美好。不时掀开锅盖观察,粥渐稠黏,才想起根本没有任何就粥的小菜——什么皮蛋香干酱菜花生米统统都远在天边。失望之余,彻底搜查行装,我居然还找出来一小包精制榨菜,(是临上飞机前,丈夫塞在我的包里的。这会儿不得不感谢他的深谋远虑。)不由欢欣鼓舞。于是匆匆将粥盛出,顾不得烫嘴,顾不得实际上的粥并未烂熟甚至可以说是清汤寡水,就迫不及待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稀里糊涂地喝了起来。喝得满头冒汗,竟还没忘了到客厅里去邀请那位成全了我们的法国朋友:
嗨,你也喝一点粥吧,怎么样?
朋友往我们的盘子里望了一眼,那里除了清汤和米粒还有几根榨菜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耸耸肩,摇摇头,宽容地笑了笑,继续喝他的咖啡去了。
一碗稀粥下肚,顿时精神焕发,五脏六腑和谐熨帖,周身通达舒畅,真是说不出的惬意。那一天漫游罗浮宫长廊,步伐矫健而扎实,情绪饱满而高昂。尤其是想到在巴黎的一周内,每日早晨都有自己炮制的稀粥垫底,便对法国之行充满信心。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自从喝过这其实并不太合格的稀粥之后,我和舒婷不约而同地体会到,前些时浑身的不适感,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们食欲大增,兴趣盎然,谈笑风生,精力充沛。我们避而不谈关于稀粥的话题,但我想我们都已彻底明白在德国时总觉得不对劲的真实原因。
廉价稀粥引发的彻悟,在事后给予我廉价的安慰。用泰国大米简易制作的稀粥,帮助我对本人的主体构造产生了新的了解。在那次出国访问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属于开放状态能够接受任何新生的或新鲜的事物。我甚至时刻警惕自己防范自己不要受“拿来主义”的影响和污染,以免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改换了自己的人种。但发生了巴黎公寓的稀粥事件后,我对自己不再有这类担心。我为自己拥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中国胃,以及由这个胃所决定的头脑、服饰和一切,而骄傲地屹立于香榭丽舍大街。
回国的飞机抵达机场,丈夫因出差恰恰在外,只好委托了一位亲戚来接我。我一眼便看见他手里提了一只蓝色的塑料筐,里头放着一只白色的保温杯,还有一只小小的玻璃瓶。坐上汽车,那杯子和瓶子便随着车的颠簸哗哗啦啦响动。我好奇地问他那是什么东西,来接我干吗带这个?
他回答说:这是给你的。
给我?什么好吃的?
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说:稀粥呗,还有你爱吃的老虎酱。
停一停,又补充:你老公临走时再三关照的,下了飞机,什么也不用给你做,说你就想喝粥。又怕到了家再做你等得心急,特意让你姐先做好了带着。
无语。心里直犯嘀咕,分别一月,真不知丈夫何以有如此突飞猛进的体贴入微。感动之余,想起自己在德国给家里的信中,定是流露过强烈的思粥情绪。其实,我在国内时并非是无粥不行的稀粥爱好者或是稀粥专业户,丈夫对我这种在异国他乡产生的反常粥恋,大概进行了深层的解析而后作出了某种判断。他到底是想鼓励我还是要借题发挥点儿什么?谢天谢地幸好他这会儿不在。
急急地拧开瓶盖,老虎酱的清香扑鼻而来。这种用香菜末、鲜黄瓜丁、青辣椒丝加盐、味精和香油拌成的北方夏季凉菜,就着稀粥、烙饼做晚餐,确实是勾人食欲而任何西式食物都不可替代的美味。
那天晚餐我喝粥。满满一大杯粥,独自一人可喝个痛快喝个踏实喝个过瘾,喝撑了就是喝趴下也没人妨碍你。但我却不知为什么,只喝了一小碗就再也喝不下了。
我重又觉得似乎哪儿不对劲,浑身不舒服心里空荡荡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干吗非要喝粥不可,喝得这么兴师动众这么积重难返这么深情这么悲壮。莫非稀粥已流入我的血液?如果我真的患有粥样动脉硬化,那我实际上已是不可救药。
想到自己原来竟是如此的不可改变,心里漾起一层粥样的泡沫,很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