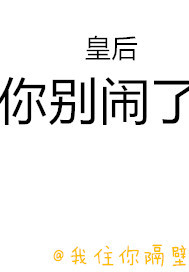伊斯兰堡(Islamabad)是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最年轻的城市,只有几十年历史。巴基斯坦决定为自己营造一个新首都,以便摆脱旧都城的各种负累,这便是伊斯兰堡的出现。
这样一座首都当然可以按照现代规划装扮得干净利落。我因为刚刚在这个国家的腹地走完两千多公里,见到这样一座首都总觉得有点抽象。它与自己管辖的国土差别实在太大了,连一点泥土星子、根根攀攀都没有带上来。突然产生一个想法,那些联合国官员和外国领导人如果到了几次伊斯兰堡就觉得已经大致了解了巴基斯坦,那实在是太幽默的误会。
伊斯兰堡周围倒有一些很值得寻访的地名,例如,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白沙瓦(Peshawar)、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以及小时候并不知道的塔克西拉(Taxila)。这几个地方离得很近,在古代区划中常常连在一起。我首选塔克西拉,主要是因为它是犍陀罗艺术的从伊斯兰堡向西北驱车半小时,就到了塔克西拉。
路牌上标有很多遗址的名称,我们先去了比较重要的塞卡普(SirKap)遗址。
这是两千多年前希腊人造的一个城市,现在连一堵墙也没有了,只有一方一方的墙基,颓然而又齐整地分割着茂树绿草。
在离希腊本土那么遥远的地方出现希腊城堡,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公元前四世纪东征亚洲的亚历山大。他的部队到这里还有八万多人,分两个地方驻扎,这儿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由一个老兵营的繁衍生息而扩充成一个都城,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情了。大概热闹了三四百年光景吧,在公元二世纪沦落。
作为一个遗迹挖掘出来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挖掘的指挥者是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
塞卡普遗址中有一个石质的佛教讲台。底座浮雕图案中刻了三种门,一种是希腊式的,一种是本地式的,一种是印度式的。门上栖息着双头鹰,据说象征着东、西方交汇于一体。
在这个佛教讲台边上,高高低低地排列着很多千年石块,大多是断残的,因此显得很乱。我和盂广美小姐一起坐在这乱石丛中想休息一会儿。广美问我:“亚历山大明明是千里侵略,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是用崇敬的口气谈起他呢?”
我想了想,说:“他攻占波斯后,带头与大流士三世的女儿结婚,与他同日结婚的马其顿军官和波斯女子多达一万对。这种远征很特别,先留驻人种,再留驻文明,也就是他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明。那婚礼,全都变敌为亲,使反抗失去了理由。”
亚历山大留下的希腊人的后代,不知经历过多少文明冲撞和融合的悲喜剧,可惜没有详细记载。只剩下这个佛教讲台上的雕刻,静静地歌颂着文化融合。
犍陀罗艺术,就是在这种融合中产生的。
犍陀罗(Gandhara)原来是塔克西拉一带的地名,公元一世纪曾为贵霜王国首都,也曾称为犍陀罗国。但在世界艺术史上所说的犍陀罗艺术,范围要大一点,除这一带之外,连同阿富汗南部方圆几百公里间所发现的公元一世纪后的佛像艺术,都可以算在里边。这是东方艺术研究中一个少不了的课题。我本人十几年前在研究东方美学时,也曾一再地搜集过与它有关的资料,因此到这里来深感亲切。
犍陀罗是划时代的。在它之前,佛教图像一直是象征性的动植物和其他纪念物。由犍陀罗开始,直接雕刻佛陀和菩萨像。这肯定是受了希腊人体雕塑艺术的影响,当初亚历山大远征军中就跟随着不少希腊艺术家。
犍陀罗的佛像从鼻梁、眼窝、嘴唇到下巴都带有欧洲人的特征,连衣纹都近似希腊雕塑。但在精神内质上,又不太像是欧洲。面颜慈润,双目微闭,宽容祥和,一种东方灵魂的高尚梦幻。
如果细细分析,犍陀罗综合的文化方位很多,不仅仅是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这儿当时是一个交通要冲,各方面的文化都有可能涡漩在一起。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先生告诉我,当地有学者认为,犍陀罗中所融合的蒙古成分,不比希腊成分少。我还没有看到这位学者的具体论据,因此暂时还不能发表意见,等读了他的论文再说吧。
离塞卡普遗址不远处,有一个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很小,其实只是分成三块小空间的一个大间房,但收藏的内容不错,其中最精彩的还是犍陀罗艺术。
我在一尊尊佛像前想,幸好有犍陀罗,使佛经可以直观。这里,尽管很多佛像已不完整,但完整的佛经却藏在它们的眉眼之间。
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广大信徒未必读得懂佛经,因此佛像便成为一种群体读解的“本”,信徒只须抬头瞻仰,就能在直观中悟得某种奥义。我曾把这种感受效应挪移到艺术理论上,在《艺术创造论》一书中提出过“负载哲理于直观中”的审美效应理论。我把这种审美效应,称之为“佛像效应”。
今天,我脚下的土地,正是最初雕塑佛像的地方。居然雕塑得那么出色,一旦面世,再也没有人能超越。
犍陀罗,我向你深深礼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