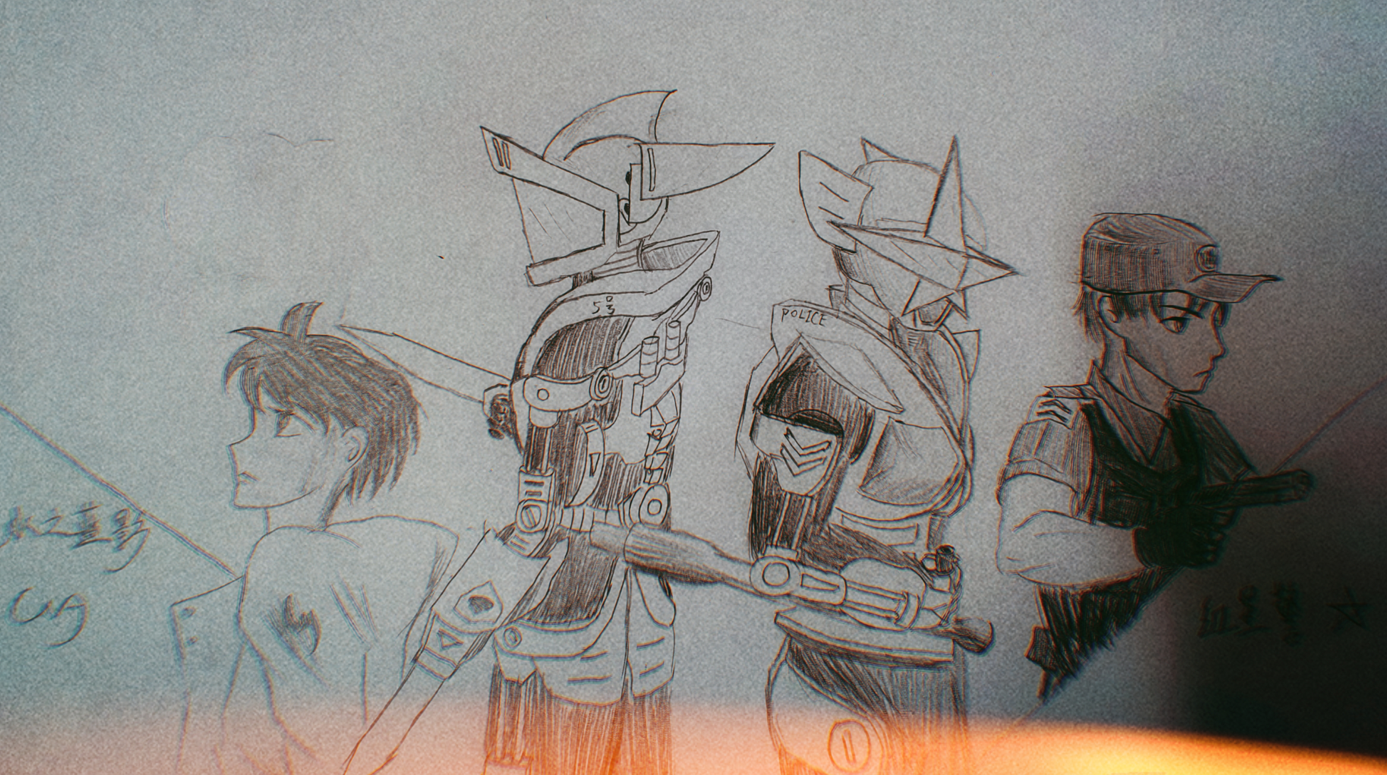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一脚踏进旧城,浓浓的一个中世纪。
阴暗恐怖的城门,开启出无数巷道,狭小拥挤,小铺如麻。所有的人都被警告要密切注意安全,使我们对每一个弯曲、每一扇小门都心存疑惧。
脚下的路石经过千年磨砺,溜滑而又不平,四周弥漫的气味,仿佛来自悠远的洞窟。
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一片敞亮。眼前一个广场,广场那端便是著名的哭墙(Wailing Wall),犹太教的最高圣地。
这堵墙曾是犹太王国第二圣殿围墙的一部分,罗马人在毁城之时为了保存证据,故意留下。以后千年流落的犹太人一想到这堵墙,就悲愤难言。直到现代战争中,犹太士兵抵达这堵墙时仍然是号啕一片,我见过那些感人的照片。
靠近哭墙,男女必须分于两端,中间有栅栏隔开。
在墙跟前,无数的犹太人以头抵着墙石,左手握经书,右手扪胸口,诵经祈祷,身子微微摆动。念完一段,便用嘴亲吻墙石,然后向石缝里塞进一张早就写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什么,别人不会知道,犹太人说这是寄给上帝的密信。于是我也学着他们,在祈祷之后寄了一封。
背后有歌声,扭头一看,是犹太人在给男孩子做“成人礼”,调子已经比较欢悦。于是,哭声、歌声、诵经声、叹息声全都汇于墙下,一个民族在这里倾吐一种压抑千年的心情。
哭墙的右侧有一条上坡路,刚攀登几步就见到了金光闪闪的巨大圆顶,这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叫金顶岩石清真寺,也简称为岩石圆顶(Dome of Rock)。它的对面,还有一座银顶清真寺。两寺均建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军队征服耶路撒冷之后。
我们在金顶岩石清真寺门口脱下鞋子,恭恭敬敬地赤脚进入。只见巨大的顶穹华美精致、金碧辉煌,地上铺着厚厚的毛毯。
中间一个深褐色的围栏很高,踮脚一看,围的是一块灰白色的巨石。相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由此升天。
巨石下有一个洞窟,有楼梯可下,虔诚的***在里边礼拜。
伊斯兰教对耶路撒冷十分重视,有一个时期这是他们每天礼拜的方向。直到现在,这里仍然是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圣地。走出金顶岩石清真寺我环顾四周,发觉伊斯兰教的这个圣地,开阔、高爽、明朗,在全城之中得天独厚,犹太教的哭墙只在它的脚下。
两个宗教圣地正紧紧地交缠着,第三个宗教——基督教的圣地也盘旋出来了。盘旋的方式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相传耶稣被当局处死之前,曾背着十字架在这条路上游街示众。
目前正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荆杰先生熟悉这条路,热情地带领我们走了一遍。
先是耶稣被鞭打并被戴上荆冠的地方,然后是他背负十字架游街时几次跌倒的处所,每处都有纪念标记。相传在他游街的半道上曾在一个小街口遇到母亲玛丽亚,现在这个小街口有一个浮雕,浮雕中两人的眼神坦然而悲怆,凝然直视,让人感动。
最后,到了一个山坡,当年的刑场。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这里建造了一个圣墓教堂。教堂入口处有一方耶稣的停尸石,赭白相间,被后人抚摸得如同檀木。两位年老的妇女跪在那里饮泣,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也都跪在两旁。
基督教把这条长长的小路称作悲哀之路(Via Dolorosa),也简称苦路。这条路在经历那么漫长的历史之后仍然不加任何现代修饰,老模老样地让人走一走,想一想。它平静而又强烈地告诉我们:无罪的耶稣被有罪的人们宣判为有罪,他就背起十字架,反替人们赎罪。
那么,这条路,几乎成了《圣经》的易读文本。
任何像样的宗教在创始之时总有一种清澈的悲剧意识,而在发展过程中又都因为民族问题而历尽艰辛,承受了巨大的委屈。
结果,谁都有千言万语,谁都又欲哭无声。
这种宗教悲情有多种走向。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狭窄的意气中陷于争斗。
但是,如果让狭窄的意气争斗与宗教感情伴随在一起,事情就严重了。宗教感情中必然包含着一种久远的使命,一种不假思索的奉献,一种集体投入的牺牲,因此最容易走向极端,无法控制。这就使宗教极端主义比其他种种极端主义都更加危险。从古到今,世界上最难化解的冲突,就是宗教极端主义。
走在耶路撒冷的任何角落我都在想,中华文明的长久延续,正与它拒绝了宗教极端主义有关。中华文明也常常走向极端,但是由于不是宗教极端主义,因此很难持续。
从哭墙攀登到清真寺的坡路上,看到一群阿拉伯女学生,聚集在高处的一个豁口上,俯看着哭墙前的犹太人。她们的眼神中没有任何仇恨和鄙视,只是一派清纯,好奇地想着什么。她们发觉背后有人,惊恐回头,怕受到长辈的指责,或受到犹太人的阻止。但看到的是一群中国人,她们放心地笑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