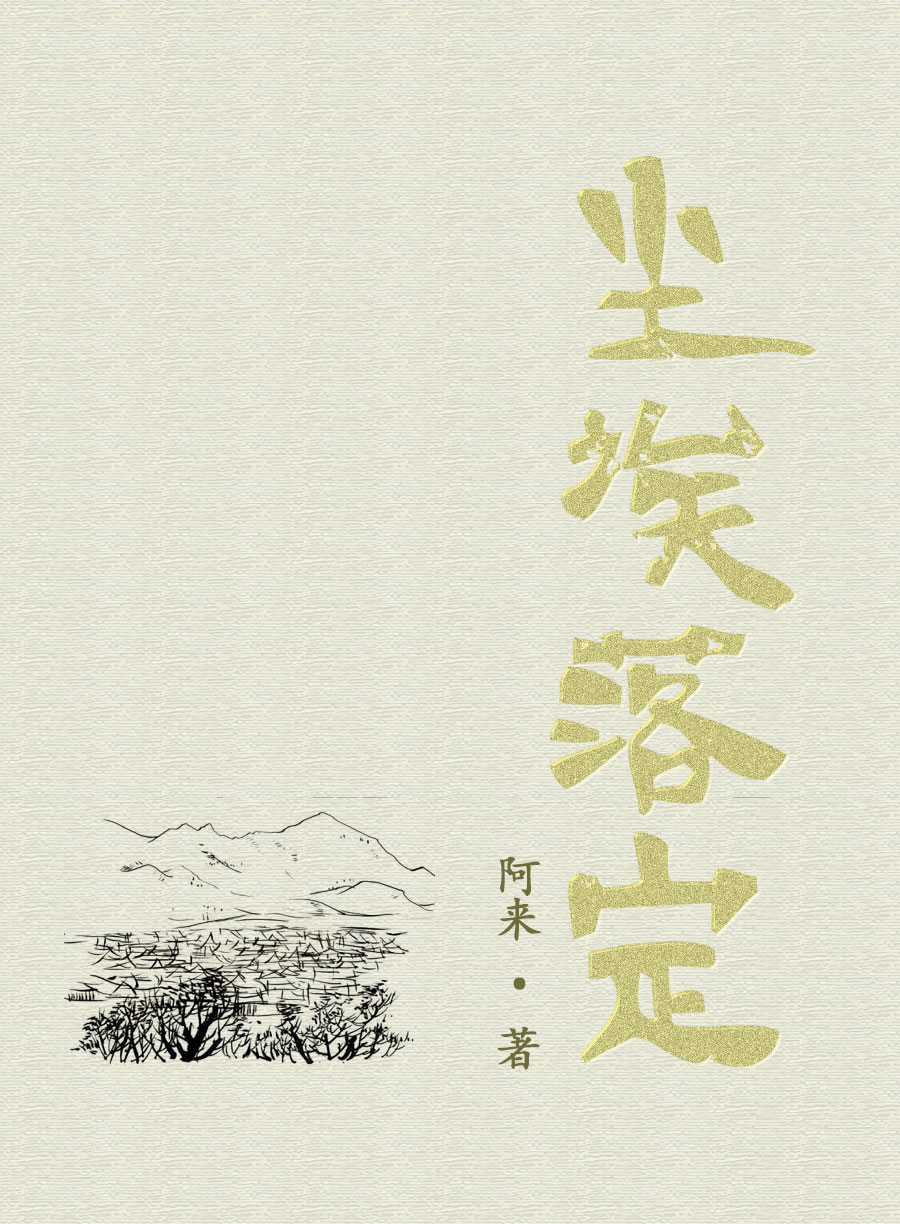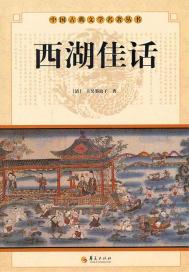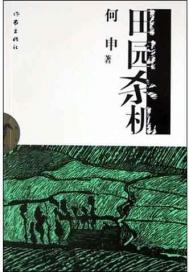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着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
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霎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蹠: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学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历史学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学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的一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地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预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介绍”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
“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的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和方时旭,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地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现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随、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的坚决的句子——
“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
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
“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枯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回,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衒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ofi Sandor)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后来是《京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介绍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地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如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地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软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动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糊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唯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新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深刻,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地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恼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
“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地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厮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
这和爱罗先珂(V.Eroshenko)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了。
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地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布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
“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騃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介绍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
“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个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地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
‘——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吧。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吧。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做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地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做《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它的叶是有刺的,它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它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厉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嬉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缥缈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地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介绍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
“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地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Sanin)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恶”的前途。
未名社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以敏锐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励,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地之子》的后记里自己说——
“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辛酸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
此后还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五
临末,是关于选辑的几句话——
一,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在这里,一九二六年后之作即不录,此后的作者的作风和思想等,也不论。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编的集子的,曾在期刊上发表过的初期的文章,集子里有时却不见,恐怕是自己不满,删去了。但我间或仍收在这里面,因为我以为就是圣贤豪杰,也不必自惭他的童年;自惭,倒是一个错误。
三,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
以上两点,是要请作者原谅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种期刊,真不知有多少,小说集当然也不少,但见闻有限,自不免有遗珠之憾。至于明明见了集子,却取舍失当,那就即使并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来勉强辩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