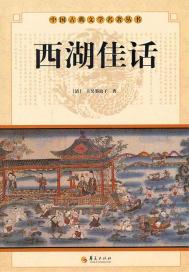流行病我们到达F城之后,事情才真相大白:F城时下确实正流行一种有关肝的疾病。
C君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她死死捂住肝区,止不住一阵恶心。背包撂在自己鞋面上,差点儿连眼神都没地方落。
她有洁癖。略略听人说起过。
据说到昨天为止,已达到多少多少万人了;全城的医院都住满了;病床都开上下层了;据说全城所有的公共汽车扶手,餐馆的桌椅板凳、电影院的空气,还有自来水管、煤气管道、电线或是下水道里,都密密麻麻布满了那专门同人的宝贝肝儿过不去的病毒了。以至于路上每一个迎面走过去的人,头发丝和呼吸里,都可能携带着这要命的东西了。F城已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被污染了。
C君决定立即离开这个城市。她从下车到现在滴水不沾。
我倒认为未必这样。起码F城在这之前,从来都是不同凡响的。这种不凡响难以用语言建构。它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声音、一种气氛、一种温度与湿度、时间与空间的总和。F城在我眼里永远那么精明那么细巧、那么敏感那么实惠,还那么绝俗那么时髦。F城的街道永远熙攘拥挤,迫不及待争分夺秒地流行的时尚,无论是流行时装流行发式流行家具流行首饰流行歌曲还是流行霹雳舞太空舞流行妻子加情人,在此都是应有尽有,无一遗漏。象F城那条流去又流来的护城河水,把所有的流行色都脏兮兮地搅拌到一起……
如果再加上现在这个流行性肝炎,它就十分完美了,我暗暗想。我对F城的好感竟由此有所增加。事实上,F城在这一片心怀叵测的非议与流言之下,倒显得格外轻松自在。街道依然拥挤不堪,商店依然生意兴隆,餐馆依然杯盘狼藉,行人依然风流倜傥……我拨了整整一天的电话寻找我的熟人,发现他们个个依然健在。没有什么可以表明甲肝同这个城市的关系,没有什么迹象,至少我看不出它在哪里。我甚至觉得F城比以往更显得精力旺盛,更汹涌澎湃。
何况,甲肝甲肝,听起来就像是最好的肝似的,容易使人唱起甲鱼。
“你们真是一点儿没听说流行……”听说是听说一点,不大相信,你晓得新闻的透明度……
“我说的是流行粗的金项链……”“我们是出来组稿的,等米下锅,没办法,现在流行武侠小说……”“我不看书。我是问你。你刚过了年就跑出来,手里一定有货。”“货?”“不要客气,尽管直说,汽车钢材、木料还是水泥,我都要。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板蓝根也行,一包换一包‘良友’……”“我不是……”“不是?不是你有介大的胆子,这种辰光跑到F城来?你讲价好了,成交一吨多少信息费……”C君再没有离开过宾馆。
她根本买不到近日内回E城的票。她从车站灰溜溜回来,说那儿挤得有点像二十年前知青下乡的时候。她后悔到F城来。她说整个F城看上去像一盒发了霉的饼干,长满了暗绿的苔毛。她前不久刚学过一点气功,说能测出城市上空的晦气。她毫不犹豫从街上买回一只电热杯,消毒杯子带消毒房间烧干了十三杯水烧得天下皆白。自从在F城搁浅以后她餐餐用电热杯煮面条煮面包煮苹果,不煮得稀巴烂决不进口;她只在楼下大厅的柜台上买这些东西。还买回三双尼龙手套和一瓶洗涤灵。她几乎终日戴着手套,只要一旦摸过除了她自己嘴以外的地方,她说把手套脱下来泡在卫生间的水池里。有一天她在洗手套时惊呼,说毛蚶只是替罪羊,一定是水源有了问题。兴许核电站溢漏造成核辐射或是由艾滋病毒诱发……她的嘴唇不安地哆嗦,命令我睁大眼睛观察那汩汩而流、看上去清洁透明而实际上充斥针机的水。她说她早就认为这个世界布满危险,早就预言这个世界再没有一处安全岛。现在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凿的证明而已。
从那会儿开始,她的电热杯终日电流水流不断。她信不过宾馆热水瓶里的开水。她用自己的电热杯烧的水洗头洗衣洗澡洗脚。她警告我必须用凉开水刷牙,否则只要有一滴生水的亿万分之一的那么一个病毒进入我的咽喉,我就会完蛋。我不得不服从,险些没把大牙烫掉几回。那些日子她就躲在宾馆里闭门不出,从早到晚烧开水。反正她从来就对一切流行的东西深恶痛绝。组稿约稿的事一股脑推到了我头上。而当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宾馆时,她那警惕而审视的目光,总使我怀疑她是否想把我也放在电热杯里煮一煮。“给你多少出差费?”“同平常一样。”“呆!这种辰光出来,补助费应当加三倍。回去向你们领导要保健津贴。没好处的事情,现在啥人肯做?”“哎呀呀,你怎么还穿这种大脚管裤子?老早不时兴了。”“我晓得,我不喜欢同别人穿一样的。我人长,穿细的不大好看。”“好看?时兴就好看!你看,我家的壁纸刚叫人来重做过,画线都拆掉了。现在时兴贴到顶,同宾馆一样。顶时兴的,是做护墙板,吊灯的顶灯也不时兴了。要做到天花板里去,只见光不见灯……说句实在话,你回去介绍朋友做这个生意,保证赚一笔……”“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路都是这首歌。
满城都是。
我回到宾馆房间时,C君正对着镜子翻看自己的眼白。她说她这几天尿有点发黄。我回答说莫非以前的尿是绿的?她把眼皮放下,揉了揉,一抬眼,看见了我买回的几只粽子和一盒奶油蛋糕。她如见了一枚定时**似地尖叫起来,叫我把它们扔出去。我说我吃腻了电热杯,这么吃下去我活不出F城去。粽子包着那么厚的壳,那肝炎还会像孙悟空一样钻进去不成?蛋糕是国营大食品公司里出的,即使有肝炎菌,烘也供熟了不是?她拼命摇头结结巴巴指着蛋糕上的奶油花说。那说不定浇奶油的工人手上带菌呢,还有盒子、还有……我说那怎么就偏让你摊上?你学过概率学没有?她说反正你得扔了去,不扔就别想进这个门儿。我说那我一个人吃还不行呀?我的肝儿馋得受不了了。她沉下脸说,你一个人吃也不行,我们同住一室,你吃了,就可能污染我,你得讲点儿公德。我回E城还得约会呢。说着就趁我不备把东西扔到了走廊里。
“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那盒蛋糕象一轮灿灿的满月,跌落进裂在猩红色地毯上,银白色的光泽洒射开去,散发出清肠润肺的芳香。眼前一片如玉如脂的雪地。我蹲下来,忍不住用手指去抠那白色的琼浆,然后放进嘴里慢慢吮吸。我不相信这样纯净的东西会有什么病毒。这该死的病毒,传得神乎其神、骇人听闻、无处不在的恶魔,实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它。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我知道人们总喜欢创造出一个什么来吓唬自己,否则他们就会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
也许你觉得它不存在,它便不存在!我饿极了,我的消化功能一向极好(这样的肝才是真正的“甲肝”)。我蹲在地毯上吃完了那沾在腈纶毛上的奶油,嘴唇舔得心满意足。当然后来C君看在自然灾害的面上还是让我进了门,只是从此我摸过的东西她决不再摸一下。她说她已创造了日洗手一百九十八次的纪录,她的手都快洗出茧子来了。
“你也去走,我也去走,才会有结果……”满城都是。
我组稿加采购,探亲访友加郊区旅游,在F城痛痛快快玩了个够。飞机票也总算弄到手。C君在煮最后一次方便面时,电热杯终于因疲劳过度肝胆俱裂而未能善终,C君只好空着肚子同我上车去民航。临走之前,她又对着镜子检查一遍自己的眼白,长长舒出一口气。我侧目看她,见她的脸苍茫如白脱蛋糕,连日来缭绕着电热杯的袅袅蒸汽使她眼圈下的黑晕格外明显,下巴颏竟缩小了一圈。看来伺候电热杯亦非易事。
假如这一天我和她顺利地在民航换乘班车,然后上飞机回到E城,那么,我对F城也许将永远留下一种充满玄虚夸张的美感,一种出污泥而愈秀的印象。但不幸的是,C君终于饿了。就在我们下电车迈进民航大厅之前,从左侧的屋檐下传来了一阵混合着葱花猪油芝麻辣椒油种种芳香无比的气息。诱人之极。
C君站下了。她的喉咙咕嘟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她的眼睛再也无法从那馄饨摊上挪开。她的可怜的没有油水的肝在呼唤她的心。它们彼此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人,也许说一座蜡像更合适。我从来没有见过肤色如此之黄的人黄得如秋天的树叶,如枯萎的腊梅瓣,晦暗粗糙干涩犹如生命中的血液已被抽吸殆尽。那一瞬间,在地面前我竟怀疑自己作为黄种人是否合格。他黄得死心塌地。
他似乎在掏钱要买馄饨,那摊主老头笑嘻嘻摇头;他将钱递过去,摊主后退一步只是摇头;他似乎提高了声音,摊主收了笑指指他飞扬的唾沫又指指他的脸;他的脸愈发黄得阴沉扭到一边去,将那钱扔在摊位上,自己伸手去抓碗;老头按住了碗,眉毛额头脖颈绯红;他嚷嚷起来,索性伸开巴掌在摊头摊尾乱摸一气;他嚷嚷说他难道不是人么,他病死也不能饿死……那老头急得去抓他的衣服,被他蜡黄的手推个趔趄……
没有人说话。围一圈人,呆呆地、痴痴地看。傻笑、哄笑。端着碗的,放下碗悄悄走开;正要掏钱的,将钱塞回衣袋,走远几步,没有人去推开他,包括我在内。
快走吧,车要开了。
C君招呼我。我回头。她平静而漠然。我想起那一次在一辆长途汽车上,一堆人拥在一起赌博,有个毛头小伙子说了一句应该把汽车开到公安局去,让那堆人摸得死去活来而全车无一人吭声,任其鲜血淋漓。我浑身冰凉。那次和这次,我同样是个麻木不仁的旁观者。
飞机升空后,我仍然想着馄饨摊的情形。那黄人使我一阵阵毛骨悚然。这么说,F城的肝是出了问题,F城是确实发生了流行病?我失望而扫兴。我低头俯瞰舷窗外的F城,发现渐渐缩小的F城居然是前所未有的破烂与衰老。可究竟是那黄人“流行”了F城,还是F城“流行”了黄人呢?金灿灿的龙年之疑。
C君从上飞机后就一扫愁云,对我悄悄耳语说,总算平安逃出虎口。回到E城,她将把亏损的营养统统补回。E城是全中国最干净的城市,那儿的天空永远阳光灿烂。
然而,我们回到了朝思暮想的E城,E城却在我们离开短短不到一个月中,变得十分陌生与莫名其妙。
首先是E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招贴画;电线杆电车车厢商店橱窗居委会的黑板报还有机关门口办公室墙上小吃店公共厕所,到处是些关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饭前洗手预防为主的口号惊叹号。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街上突然变得冷冷清清,菜馆门可罗雀。原先人挨人站在餐桌边上等候座位,现在居然变成了一张张光溜溜的桌子等人。卖羊肉串儿的任凭撕破了嗓子喊也无人光顾,所有的药店门口倒排起了长队。幼儿园铁门紧闭,终日围着些男人女人,愁眉苦脸地从门缝往里张望……
我似乎感悟到、发现出一点什么。我止不住打了一串寒噤。尽管我并不愿意做这样的推测,却已有人来通知我和C君立即去医院验血。我记得已差不多近十年没验血了,我求之不得。“万一……很可能休假两个月。”那样的闪念令人兴奋。C君却很愤慨地拒绝了,她认为去医院有可能染上白血病什么的。化验单第二天就出来了:我的澳抗的阴性,转氨180。
这个180便十分的不伦不类。
有人说十几年前我就能开出病假条,现在医院规定140也算正常。
何况大医院小医院单位医院疗养院各有各的指标,各有各的肝。他说你没病你就没病他说你快不行了你就不行了。你揣着这180的肝还得揣上个灭火器。没人让我休假,我的阴谋没得逞不说,还让我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能感觉到人们怀疑与警惕的目光从我的肝区迅速穿过;他们诡秘狡黠地冲我笑着,躲躲闪闪,不怀好意;他们假惺惺向我伸出手来,我却弄不清楚那手里究竟有没有手,我不知道握住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握住。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衣;后来我恍然大悟,干脆双手抱拳,行拱手礼。但那也仍然不能够使我变得安全,不要说碰一下,好像看我一眼都会染上什么。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位朋友托我从F城带来的一只原装的日本进口相机,我遵嘱将东西送交他的岳父家,他岳父的秘书如同见到一只刚屠宰的猪用鞋尖指指它对司机说:马上送医院检疫。
不必再怀疑,一切都明白无误了:那个黄人,那座蜡像,已与我们同乘一架航班,悄悄走进了E城。也许它早就来了,它不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它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它们有多少。谁也没有看见它们,但谁都相信它已侵入E城,它们像一个个隐身的幽灵开始骚扰E城人的肝区。如一片巨大的阴影,徘徊在E城上空,遮去了E城昔日明媚的阳光……
E城草木皆兵。E城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抵御这个如洪水,如瘟疫涌来的魔鬼,E城是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它对时髦的流行性“那个”,如此诚惶诚恐,我以为完全可以理解:好在本人自我感觉良好,日啖肥肉三两,无忧无虑,没心没肺。从F城回来后,我的兴趣有所转移。F城的经历使我顿开茅塞。
“不要客气,尽管直说。汽车钢材水泥木料,我都要。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有板蓝根当然最好,一包换一包‘万宝路’……”“新簧片”是厦门中药厂生产的肝炎特效药。几箱?二十箱?没问题,你开价好了。成交一箱多少好处费?补助费不加倍?起码应该给点儿保健津贴什么的。我和C君从S城跑到G城再跑F城,你们不想想是什么时候,我们是冒生命危险去组稿的。没好处的事,现在谁肯干?你们书库里还有没有预防肝炎的书?只要是同肝炎搭着边就成。你积压不也是积压?卖给我,八折,怎么样?九折就九折。九折我也能赚一笔。告诉你,这三个月内决不流行什么三毛四毛;只流行肝儿书,如今个体户全卖这玩意儿。畅销着呢。怎么样,给多少信息费?我忙得终日不着家,上班也是装模作样。我心里充满激情与冲动。我发现挣钱这念头叫人上瘾,叫人想入非非。
有一日早上我被人从梦中推醒,醒来时只见一片白雾缭绕,渐渐从白雾中出现一只电热杯。不过更确切地说,是C君的脸。多日不见,那股愈发地苍茫,眼圈愈发地深黑,下巴愈发地狭窄,眼皮还有些红肿。
我说C群体没翻自个儿眼皮吗?你好像得了猩红热。C君掏出一块手绢,站在地中央就呼嘘起来。她说她回到E城后就盼那位助工打电话来。等了两礼拜,电话总算来了。她说今晚见见面吧或者一块儿吃晚饭,他说不必了就在电话里谈吧,省得走路还省时间。她摔下电话就跑到他单位去找他,他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正在灯下画图纸。见她进去,放下笔就说,我们还是到楼下去谈。你刚从F城回来恕不奉茶了。实在要握手等我去拿一块消毒皂来。我自己倒没什么。刚离婚儿子星期六要来万一传染不大对得起他娘。就这样没进门没让座没喝水没拉手活活在走廊里站了一个半钟头谈的全部是关于儿子如何预防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没有叫我一声心肝说老实话上次是叫过的我不会听错。我连猪肝都不吃怎么会得肝炎这该死的肝炎活活拆散一对姻缘我还没得上他就对我这样还有什么恋爱好谈你说呢?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睡眼惺忪。我只觉得这流行性甲肝对于C君倒是非常及时。我还想诚诚恳恳安慰她一番。她手绢一拧,抬头望着天花板说,那么难道你不觉得你应该付给我一笔赔偿费吗?是你叫我陪你到F城去的……
我瞠目结舌。我实在没有料到,曾对一切流行的东西深恶痛绝的C君,从F城回来后居然令人刮目相看。看来F城真是不凡的地方。你就是不染上流行病也能染上点儿别的什么。不过,关于赔偿费嘛,我建议她应该去找单位的头儿,毕竟是他让我到F城去出差的。
这不公平。C君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皱着鼻子哼哼。我们在F城担惊受怕,我们是受害者;可回到E城,我们倒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又是个受害者!
这很公平。我慢慢吞吞穿衣服,我相信我已完全清醒。我对C君说,我们在F城受污染,再回E城污染别人;我们在F城傲视别人,回E城后别人又疏远我们,正如人人都恐惧甲肝,又偏偏都参与了传播。
C君无言地走了。我觉得她的洁癖与自尊受到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与伤害。但我不知道是谁伤害了她。
“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从F城到E城满城皆是。
越过大洋,越过崇山。从世界的另一极从国土的那一端,如风、如水、如种籽、如羽翼、如光电、如细菌、无边无际、无遮无拦,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流行、没有什么不可以携带它流行,只要是这个星球上的人们由于乏味、由于厌倦、由于渴望、由于欲念而在一个瞬间一个机遇里偶然地或是处心积虑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玩具,便就这样盲目地疯狂地开始了它的国际大循环。
E城由此变得面目全非。
我走遍全城,到处都听见人们在说:洗手去!
洗消净脱销,洗洁净脱销,洗涤灵脱销。洗衣粉洗衣皂洗头粉爽脚粉白猫牌金鱼牌鹿牌船牌舵牌桨牌……E城的自来水流得前所未有的软弱无力。几十年来,我第一次在机关厕所的水龙头下,发现一块肥皂。有人告诉我说那是免费的。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亲眼看见食堂里戴白帽子的大师傅,擤了鼻涕之后,把手放在菜刀下刮了又刮。
E城的人成功地发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洗手运动。运动普及到每一只手指,十指连心,可想而知是深入人心了。
最意想不到的是有关方面三令五申了多少回的“分餐制”,也在这场洗手运动中,轻而易举地得以实施。过去我是最害怕开会吃圆桌饭的,即便每个人面前有一只空盘子,转台上有公筷公勺,那些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会友们,也决不肯把菜自到自己盘中用自己筷子来吃的。如果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唾液伸进别人的口腔这顿饭就算没吃。每次我把菜接搛进自己的盘子,便再不敢抬头,似乎满桌的眼光都在说:瞧这人,嫌乎我们哪?!
可是不知不觉,悄没声儿,如今就从厨房里端出来了有四个不规则凹槽的不锈钢菜盘,盛上了荤素搭配的四种小菜,每人一份。有一次宴会,居然换了十二次盘子……
有记者让我谈谈对分餐制的感想,尤其是改变那种千百年来的民族瘤疾的动力是什么,我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恐惧。
你能不能谈得再具体点儿?记者引导说。
恐惧是一种人性因素。所以它切中要害。比如说流行歌曲。总之流行起来就能冲垮一切……我语无伦次,不能自圆其说。我没心思同他啰嗦。我已经想到应该立即向发明那种四菜一汤的盘子的厂家大量订货,然后到全国各地去推销这种东西。要不了几个月,天上地下都将流行这亮晶晶的盘子。我给它起名为恐惧牌文明餐具。
我心里有一种恶狠狠的痛快之感,我觉得这流行性甲肝实有很有必要。
现在时兴住房宾馆化。壁纸时兴贴到顶、不用画线,天花板也要贴讲究一点,重新做过,旋出花纹来,顶时兴的是护墙板,刷奶油色,现在就是流行这种式样,吊灯吸顶灯也不时兴了。要镶嵌到天花板里去,只见光不见灯……说句实在话,你去做这个生意,包你赚一笔。F城现在刚刚开始流行,马上就会流到E城来……
“你也去走,我也去走,今天别错过。”从F城到E城,满城皆是。
终于有一天我想起了C君,我发现自从那天,她来向我索取赔偿费之后,已有许多天没看见她了。单位的人说她一直没有来上班。我有点心慌,也有点心虚。我担心,由于主编拒付赔偿费她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也担心由于助工的无情无义使她从此-蹶不振。我总得劝她去验一次血才好,必要时她可以把化验单给那位助工去看看嘛。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听说E城有一个人得上甲肝呢!
我抽了个空,专门到她家去了一次。我隐隐听说过,她妈是在药店里工作的,我想说不定弄好了可以同她妈接上个关系留做以后使用。
她家房门紧闭,敲了足有五分钟,才算开了条缝,缝上横挂一根铁链条,看来人是进不去的。我说我找C君,来给她送奖金。里面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说,C君进了传染病医院了。
我脑于轰然炸响。C君那样一天洗一百九十八次手的人也会进传染病院么?她传染什么了?
里面的声音不耐烦地说,反正是流行病。发烧呕吐,确诊不了还在观察,不是流行性脑膜炎就是流行性感冒,也说不定是流行性腮腺炎,还说不定是……我说那我得上医院去看看她。我同她一块儿去F城,她生了病我很不安……
那扇门哗地打开。一张愤怒而黄瘦的长脸竖立在我眼前。她说,好哇原来你同C君一块儿去的F城。那怎么她流行了你没流行?你搞的什么鬼你存的什么心你送些脏拉八叽的票来还想流行我?你说明白C君到底怎么流行上的,她可是从来不唱流行歌曲……
我看着自己的鞋尖。我想解释说自己大概平时大咧咧不在乎就有了免疫力,我想说大概是C君的电热杯抵抗力不够,我想说我吃毛蚶时喝了两斤白葡萄酒,现在流行“雷司令”,司令总还是管用的……
结果,我却笑笑说,哎,我没流行上大概是因为有一个潜伏期。我的潜伏期比C君长。你知道潜伏期吗?
门砰地关上了。从门缝里挤出更加嘶哑的声音:你可千万不能去医院看她。免得C君真的染上流行性甲肝!
我慢慢走下楼去。
C君就这样同我无声无息地断了联系。我不知道她究竟在哪里,究竟流行上了什么没有。其实真的要流行,莫不如得甲肝。甲肝毕竟是自愈型疾病,又没有后遗症。
过了几天才想起来,那日竟忘了同C君她妈洽谈药的生意,我莫不如不同她提什么潜伏期不潜伏期了。一个人身体里潜伏着什么病毒,自己是不会知道的。那个馄饨摊的黄人事先肯定不认为自己会变成黄人。比如说现在,我就吃不准自己到底潜伏了什么没有。这防不胜防,流来流去的家伙,也许还没等它发作出来,已经被另一种新玩意儿代替了。所以,对于流行病我其实并不害怕,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些沉淀于骨髓,无声地销蚀着人的东西。但我不知它们在哪里。
我得设法找到C君。
黄罂粟他听见自己重重地摔在床上的声音,他是被自己背后那一身冷汗惊醒的。黑暗中他睁开眼,几分钟以前梦里死死缠着他、追逐他、胁迫他的那些金光四溅的星星,依旧萦绕在他头顶。他闭眼、揉眼、试着摇晃自己的脑袋,都没法把那东西驱除掉。有时它们像一群金色的飞蝗,一条黄龙的鳞片,漫天漫地向他扑来。有时它们看上去像一阵黄土飞沙或是许多年前生产队场院上坟堆似的豆垛麦垛……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感觉到只是一片混沌而无尽的黄色烟云,吞没、掩埋了他。他被它们勒得喘不过气来。
接连许多天了,他总被这样的梦弄得无法入睡。似醒非醒的困倦中,他隐隐地觉得纳闷,又有些慌乱。他想知道这黄色究竟同他有什么关系,他似乎固执地想要弄明白那黄色究竟是什么东西。自从它们出现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正一日日陷入一种深重的苦恼,这种苦恼折磨他,使他梦中的黄色愈发显得神秘。这种不可知的由杏黄桔黄深黄浅黄淡黄金黄灰黄搅和在一起的奇怪的黄色,在夜阑人静时鬼鬼祟祟地闪烁,如同一个斑斓的诱惑,简直要使他发疯。油菜花?黄花菜?黄山?黄河?他仍拼命地想要看清它。他记得自己故乡的春天有灿烂的油菜花黄;他想起他后来远走高飞,落在八千里外黑龙江边的一个小村庄,那儿夏天的原野上有绚丽的金针菜铺地,金色的麦浪摇摇滚滚通到天边……
然而梦中的情形仍是一片模糊。他暗暗苦笑。谁想到命运竟把他抛在这远离江南油菜花又没有黄花菜飘香的小城里,如一颗半生半熟的落地毛桃,无声无息,无人问津……
卖,还是不卖呢?
一个念头,忽如草丛中的萤火虫,从他迷茫昏沉的脑中掠过——他看见一座金色琉璃瓦屋顶的小楼,一扇小窗上露出他儿子胖胖的小手和妻的红纱巾。
他眼睛豁然大亮。莫非这就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东西么?黑暗中那似有似无的黄色云雾,在这瞬间竟不再朦胧,转眼翻身的雨,一张张哗哗响、簇簇新的十元大票,风助雨势,冲他纷纷飘落。
他需要钱,急需。他无须再回避、再否认了。他需要一大笔钱。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不再让妻儿挤住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八米小屋,他就可以购置一套厂方津贴三分之二的商品房,从此,扬眉吐气地做人。
他恍然大悟这一连多日在梦里诱惑他的黄色是什么。他从骨髓里渴望发一笔大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钱的重要。
卖,还是不卖呢?
他睡意全无。
其实作出决定是十分简单的。卖,那么一周内他就可以拿到一个五位数。买主不还价,开口就是一万,这样钱对于他,买下那套二居室的商品房是绰绰有余的了。他平生还从本摸过这么多钱。何况买主还付一部分港币,即使中间人扣去一半,剩下的那些,弄好了,还够买一套时兴的家具……
他把目光投向床头的那只五斗柜,它蹲在黑暗中,像一只镀金的小兽,浑身的皮毛散发着一层若隐若现的光亮,他从未想到过,他在十年前的一个雨夜放进柜中去的那个黑色的旧簿册,有一天会变得如此值钱,柜子因它而发光,他的梦也因它而生辉,他喂给它干草和清水,它却在三天早晨,投给他金豆豆和金蛋蛋,他撞上大运了!
兴奋中他轻轻拧亮床灯,欠起身拉开柜门。以往他常常在更深夜静时,独自一人默默欣赏它们,他有时对它们喃喃自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他眼里,它们是些无声的精灵,默契的友人,或是一条河流,一座庄园,一片谷仓,一顶平坦宽阔的桥梁……
他的手指触到那厚而硬的簿册的边角,手指顿时一阵**冰冷。卖,还是不卖呢?念头从指尖滑过,他的心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咬噬啃啄了一口,涌上一种酸楚的疼痛之感——他难道真要卖掉它们,他收集、珍藏了整整十二年的粮票样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