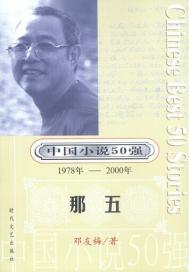260223致章廷谦矛尘兄:廿元〔1〕,四角,《唐人说荟》两函,俱收到。谢谢!
记得日前〔2〕面谈,我说《游仙窟》细注,盖日本人所为,无足道。昨见〔3〕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则以为亦唐人作,因其中所引用书,有非唐后所有者。但唐时日本人所作,亦未可知。然则倘要保存古董之全部,则不删亦无不可者也耳。奉闻备考。
迅二月廿三日
注释:
〔1〕《唐人说荟》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四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世熙(莲塘居士)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六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2〕《游仙窟》传奇小说,唐代张鷟作,当时即流入日本,国内失传。一九二六年章廷谦在鲁迅协助下,根据日本保存的通行本《游仙窟抄》、醍醐寺本《游仙窟》以及流行于朝鲜的另一日本刻本重新校定标点,一九二九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曾为作序。
〔3〕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湖北宜都人,清末学者。《日本访书志》是查访在日本流传的我国散佚古书的著作,共十六卷,是杨任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时作。该书卷八著录《游仙窟》一卷,关于所附注释,他说:"其注不知谁作,其于地理诸注,皆以唐十道证之,则亦唐人也。注中引陆法言之说,是犹及见《切韵》原书;又引范泰《鸾鸟诗序》、孙康《镜赋》、杨子云《秦王赋》(原注:此当有误),皆向所未闻者。又引何逊《拟班婕妤诗》,亦冯氏《诗纪》所不载。"260225致许寿裳季市兄:昨得洙邻〔1〕兄函,言:"案〔2〕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尚须两星期也"云云。特以奉闻,并希以电话告知幼渔兄为托。
树人二月二十五日〔1〕洙邻寿鹏飞(1873--1961),字洙邻,浙江绍兴人。鲁迅塾师寿镜吾次子。当时在平政院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
〔2〕指鲁迅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一事。
260227致陶元庆〔1〕璇卿兄:已收到寄来信的[和]画,感谢之至。
但这一幅我想〔2〕留作另外的书面之用,因为《莽原》书小价廉,用两色板的面子是力所不及的。我想这一幅,用于讲中国事情的书上最合宜。
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
鲁迅二月二十七日
注释:
〔1〕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先后在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鲁迅前期著译《苦闷的象征》、《彷徨》、《朝花夕拾》、《坟》等书均由他作封面画。
〔2〕指后来用作《唐宋传奇集》的封面画。
260310致翟永坤〔1〕永坤先生:二月份有稿费两元,应送至何处,请示知,以便送上。
鲁迅三月十日西四、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1〕翟永坤河南信阳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一九二六年转入北京大学。因投稿《国民新报》副刊认识鲁迅。
260409致章廷谦矛尘兄:承示甚感。
五十人案〔1〕,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曾面问陈任中〔2〕,而该陈任中一口否认,甚至于说并无其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
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至于现在之事端,则最〔3〕大者盖惟飞机抛掷炸弹,联军总攻击,国直议和三件,而此三件,大概皆不能归咎于五十人煽动之故也欤。
迅上四月九日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其实只有四十八人,未知是遗漏〔4〕,还是仿九六足串大钱例,以乂〨算8+也。
注释:
〔1〕五十人案指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名单(参看《而已集.大衍发微》)。四月九日,《京报》刊载《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了制定黑名单的经过情形,并列出了四十八人的姓名。
〔2〕陈任中字仲骞,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教育部参事,代理次长。据《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惨案发生后,章士钊等"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为此陈于四月十日、十六日先后在《京报》发表致编者信及刊登启事,予以否认。
〔3〕飞机抛掷炸弹一九二六年四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所部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曾多次飞临轰炸。联军总攻击,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奉系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对据守北京的国民军发动总攻击。国直议和,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张联奉讨冯,但其部分将领田维勤等则倾回联冯讨奉,因此冯曾与他们进行"国直议和"活动,但未成功。
〔4〕九六足串大钱以九十六文钱当作足串(百文)计算。旧时以制钱一百文为一串。
260501致韦素园〔1〕素园兄:日前得来函,在匆忙中,未即复。关于我的小说〔2〕,如能如来信所说,作一文,我甚愿意而且希望。此可先行发表,然后收入本子中。但倘如霁野所定律令,必须长至若干页,则是一[一]大苦事,我以为长短可以不拘也。
昨看见张凤举,他说Dostojewski〔3〕的《穷人》,不如译作"可怜人"之确切。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穷"与"可怜"二义。倘也如英文一样,则似乎可改,请与霁野一商,改定为荷。
迅五,一〔1〕韦素园(1902--1932)又名漱园,安徽霍丘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外套》和北欧诗歌小品《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2〕指小说集《呐喊》。当时台静农正在选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韦素园拟作文评论《呐喊》,后未成。
〔3〕Dostojewski陀思妥耶夫斯基(Ф.M.ДОСТОeВСкИЙ,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穷人》,韦丛芜译,鲁迅作序,一九二六年六月未名社出版。
260511致陶元庆璇卿兄:给我画的像,这几天才寄到,去取来了。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
那洋铁筒已经断作三段,因为外面有布,所以总算还相连,但都挤得很扁。现在在箱下压了几天,平直了,不过画面上略有磨损的地方,微微发白,如果用照相缩小,或者看不出来。
画面上有胶,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应该如何悬挂才好,便中请示知。
鲁迅五月十一日260527致翟永坤永坤兄:女师大今年听说要招考,但日期及招考那几班,我却不知,大概不远便可以在报上看见了。
旁听生也有的,但仍须有试验(大概只考几样),且须在开学两月以内才行。
迅五月廿七日260617致李秉中秉中兄:收到你的来信后,的确使我"出于意表之外"〔1〕地喜欢。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2〕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跑得如此之远,这事我确没有预先想到,但我希望你早早从休养室走出,"偷着到啤酒店去坐一坐我以为倒不妨多喝究竟不。。,但酒。",好。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没有听。
从去年以来,我因为喜欢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章士钊之来咬〔3〕,乃是报应之一端,出面的虽是章士钊,其实黑幕中大有人在。不过他们的计划,仍然于我无损,我还是这样,因为我目下可以用印书所得之版税钱,维持生活。今年春间,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但也没有什么效验。只是使我很觉得无聊,我虽然对于上等人向来并不十分尊敬,但尚不料其卑鄙阴险至于如此也。
多谢你的梦。新房子尚不十分旧,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约总该老了一点,这是自然的定律,无法可想,只好"就这样罢"。直到现在,文章还是做,与其说"文章",倒不如说是"骂"罢。但是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
"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我现在仍在印《莽原》,以及印些自己和别人的翻译及创作。可惜没有钱,印不多。我今天另封寄给你三本书,一是翻译,两本是我的杂感集,但也无甚可观。
我的住址是"西四,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你信面上写的并不大错,只是门牌多了五号罢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这里也可以,因为家眷在此,可以转寄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回国?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因为这能使自己受苦。第一着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这才能做一切事。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你如有工夫,望常给我消息。
迅六月十七日
注释:
〔1〕"出于意表之外"这是套用林纾文章中的不通的文言用语。
〔2〕东江珠江的东支,这里指广东东江梅县一带。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这里击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部队。李秉中为黄埔军校学生,曾参加这个战役;但这时李已到苏联留学,因此下文中有"已经跑得如此之远"的话。
〔3〕指章士钊罢免鲁迅职务一事。下文的"今年春间,......想加谋害",指段祺瑞政府列名通缉鲁迅事。参看260409信注〔1〕。
260621致韦素园、韦丛芜〔1〕沙滩新开路五号韦素园、韦丛芜先生:《穷人》如已出,请给我十二本。
这几天生小病,但今〔2〕日已渐愈,《莽原》稿就要做了。《关于鲁迅》已校了一点,至多,不过一百二十面罢。
二十一日后面还有来信顷已收到。《外套》〔3〕校后,即付印罢,社中有款,我以为印费亦不必自出。像不如在京华印,比较的好些。
巴特勒〔特4〕的谈话,不要等他了,我想,丛芜亦不必再去问他。序文我当修改一点,和目录一同交给北京书局,书面怎样,后来再商。
迅又言廿一日午后
注释:
〔1〕此信写于"周树人"名片的正反两面。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燕京大学毕业,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罪与罚》;著有诗集《君山》。
〔2〕指《无常》,后收入《朝花夕拾》。《关于鲁迅》,即台静农选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收有关《呐喊》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十四篇,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
〔3〕《外套》中篇小说,俄国果戈理著,韦素园译,一九二六年九月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下文的"像",指果戈理像;"京华",指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印刷厂京华印书局。
〔4〕巴特勒特(520yd.comt)美国人,曾在燕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六年复,由韦丛芜陪同访问鲁迅,拟写《与鲁迅先生的谈话》一文,后未成。下文的"序文",指台静农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写的序;"目录"也指该书目录。
260704致魏建功〔1〕建功兄:品青〔2〕兄来信,说兄允给我校《太平广记》〔3〕中的几篇文章,现在将要校的几篇寄上。其中抄出的和剪贴的几篇,卷数及原题都写在边上。其中的一篇《枕中记》〔4〕,是从《文苑英华》抄出的,不在校对之内。
我的底子是小版本,怕多错字,现在想用北大所藏的明刻大字本〔5〕来校正它。我想可以径用明刻本来改正,不必细标某字明本作某。
那一种大字本是何人所刻,并乞查示。
迅上七月四日
注释:
〔1〕魏建功(1901--1980)字天行,江苏如皋人,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
〔2〕品青王贵鉁,字品青,河南济源人,《语丝》投稿者。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3〕《太平广记》类书,宋代李昉等奉教纂辑,共五百卷。鲁迅曾将其中的《古镜记》、《离魂记》等篇辑入《唐宋传奇集》。
〔4〕《枕中记》传奇小说,唐沈既济作。《文苑英华》,诗文总集,宋代李昉等奉敕编纂,共一千卷。
〔5〕这里的"小版本"和"明刻大字本",指《太平广记》的清代黄晟刊本和明代长洲许自昌刻本。
260709致章廷谦矛尘兄:来信收到。但我近来午后几乎都不在家,非上午,或晚八时左右,便看不见也,如枉驾,请勿在十二至八时之间。
《游仙窟》上作一《痴华鬘》〔1〕似的短序,并不需时,当然可以急就。但要两部参考书,前些日向京师图书馆去借,竟没有,不知北大有否,名列下,请一查,并代借。如亦无,则颇难动手,须得后才行,前途颇为渺茫矣。
该《游仙窟》如已另抄,则敝抄当已无用,请便中带来为荷。
迅七,九计开一、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二、森立之《经籍访古志》〔2〕案以上二部当在史部目录类中。
注释:
〔1〕《痴华鬘》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古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僧求那毗地译,二卷。王品青曾删除其中有关佛教教诫的文字,留下寓言,于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曾为作《题记》,收入《集外集》。
〔2〕森立之日本人。《经籍访古志》由他与澁江完善合著而成,正文六卷,补遗一卷,内容系介绍他们所见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其中卷五子部小说类著录《游仙窟》钞本三种。全书约成于日本安政三年(1856),清光绪十一年(1885)徐承祖曾用聚珍版印行。
260713致韦素园〔1〕李稿已无用,陈稿当寄还,或从中选一篇短而较为妥当的登载亦可。
布宁小说〔2〕已取回,我以为可以登《莽原》。
《外套》已看过,其中有数处疑问,用?号标在上面。
我因〔3〕无暇作文,只译了六页。
《关于鲁迅......》已出版否?
迅七,一三
注释:
〔1〕此信第一页已遗失。
〔2〕布宁(И.A.ЪyНИН,1870--1953)通译蒲宁,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这里说的小说,指《轻微的欷歔》,韦丛芜译。译稿曾投寄商务印书馆,未印,后由鲁迅索回。
〔3〕指翻译童话《小约翰》。
260714致章廷谦矛尘兄:来信已到。《唐人说荟》如可退还,我想大可以不必买,编者"山阴莲塘居士"虽是同乡,然而实在有点"仰东硕杀",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近来商务馆所印的《顾氏文房小说》〔1〕,大概比他好得多。
《唐人说〔2〕荟》里的《义山杂纂》,也很不好。我〔3有从明抄本《说郛》刻本《说郛》,〕也是假的。抄出的一卷,好得多,内有唐人俗语,明人不解,将他改正,可是改错了。如要印,不如用我的一本。后面有宋人续的两种,可惜我没有抄,如也印入,我以为可以从刻本《说郛》抄来,因为宋人的话,易懂,明人或者不至于大改。
迅七,十四龚颐正《续释常谈》〔4〕:"李商隐《杂纂.七不称意》内云'少(去声)阿妳'。"
注释:
〔1〕《顾氏文房小说》明代顾元庆辑,内收汉至宋代小说、笔记等共四十种。一九二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夷白斋宋版重雕本影印发行。
〔2〕《义山杂纂》唐代李商隐(字义山)撰,鲁迅认为也可能是唐代李就今(字衮求,号义山)作,一卷。内容杂集俚俗常谈鄙事,每题自为一类。以后又有宋代王君玉《杂纂续》、苏轼《二续》和明代黄允交的《三续》各一卷。章廷谦根据鲁迅从明抄本《说郛》抄出的《义山杂纂》和刻本《说郛》所收续书三种编为一册,题为《杂纂四种》,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3〕《说郛》笔记丛书,明代陶宗仪编,是辑录汉魏至宋元笔记小说而成,共一百卷。通行本为清代陶婾重编刊印,一二○卷。鲁迅这里所说的"明抄本"指前者;"刻本"指后者。
〔4〕龚颐正字养正,宋代浙江遂昌人。所著《续释常谈》共二十卷。《说郛》卷三十五收入该书文字八十条。这里所举李商隐《杂纂.七不称意》"少阿蓱"条,是现存《杂纂》的佚文。
260719致魏建功建功兄:给我校对过的《太平广记》,都收到齐了,这样的热天做这样的麻烦事,实在不胜感谢。
到厦门,我总想拖延到八月中旬才动身,其实很有些琐事须小收束,也非拖到那时不可。不过如那边来催,非早去不可,便只好早走。
迅上七月十九日260727①致章廷谦矛尘兄:书目〔1〕中可用之处,已经抄出,今奉还,可以还给图书馆了。
迅七,二七〔1〕书目指鲁迅为《游仙窟》作序而托章廷谦借来的《日本访书志》和《经籍访古志》。
260727②致陶元庆璇卿兄:《沈钟》〔1〕的大小,是和附上的这一张纸一样。他们想于八月十日出版,不知道可以先给一画否?
迅上七月二十七日〔1〕《沉钟》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共出十期。次年八月起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陶元庆曾为它绘制封面。
260730致章廷谦矛尘兄:得廿八日信,知道你又摔坏了脚,这真是出于我的"意表之外",赶紧医,而且小心不再摔坏罢。
我的薪水送来了,钱以外是一张收条,自己签名。这样看来,似乎并非代领,而是会计科送来的。但无论如何,总之已经收到了,是谁送来的,都不成其为问题。
至于你写给北新小板〔1〕的收书条,我至今没有见。
迅七,卅〔1〕小板老板的戏称,指李小峰。
260731致陶冶公〔1〕冶公兄:兄拟去之地,近觅得两人可作介绍,较为切实。但此等书信,邮寄能否达到,殊不可必,除自往投递外,殊无善法也。未知兄之计画是否如此,待示进行。此布,即颂时绥弟树人上七月卅一日〔1〕陶冶公(1886--1962)名铸,字冶公,号望潮,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同习俄文。一九二六年十月他去汉口任市政府委员兼卫生局局长,信中所说"拟去之地"或指武汉。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等。
260808致韦素园素园兄:《关于〔1〕鲁迅......》须送冯文炳君二本(内有他的文字),希即令人送去。但他的住址,我不大记得清楚,大概是北大东斋,否则,是西斋也。
下一事乞转告丛芜兄:《博徒别传》是《RodneyStone》的译名,但是520yd.com做的。《阿Q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2〕我误记,英译中可改正;或者照原误译出,加注说明亦可。
迅八月八日
注释:
〔1〕冯文炳(1901--1967)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作家。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曾收有他的论文《<呐喊>》。
〔2〕指《阿Q正传》的英译本,梁社乾译。题名为《TheTrueStoryofAhQ》,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60810致陶元庆璇卿兄:《彷徨》书面的锌版已制成,今寄上草底,请将写"书名""人名"的位置指出,仍寄敝寓,以便写入,令排成整版。
鲁迅八月十日260815致许广平〔1〕景宋"女士"学席:程门飞雪〔2〕,贻误多时。愧循循之无方,幸骏才之易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或下问之不易。言念及此,不禁泪下四条。吾生倘能赦兹愚劣,使师得备薄馔,于月十六日午十二时,假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周宅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顺颂时绥。
师鲁迅谨订八月十五日早
注释:
〔1〕此信原无标点。在《鲁迅书简》(一九四六年十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发表时,收信人曾附有说明如下:"这封信没有收入《两地书》内,大约编辑时此信散存他处,一时未及检出。现出《书简》,正可乘便加入。这信的文笔颇与《书简》体例不同,原因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自从被章士钊杨荫榆之流毁灭了之后,又经师长们以及社会正义人士之助而把它恢复过来了。我们这一班国文系的同学,又得举行毕业,而被开除了之后的我,也能够恢复学籍滥竽其间。到了快要学业结束的时候,我国文系师长们如马幼渔先生,沈士远、尹默、兼士先生,许寿裳先生,鲁迅先生等,俱使人于学业将了,请益不易之际兴无穷感慨!良以学校久经波折,使师长们历尽艰辛,为我们学子仗义执言,在情在理,都不忍使人恝置,因此略表微意,由陆晶清、吕云章和我三人具名肃帖,请各师长,在某饭店略备酒馔,聊表敬意。其后复承许寿裳先生及鲁迅先生分别回请我们,而鲁迅先生的短简,却是模拟我写的原信,大意如下:××先生函丈程门立雪承训多时幸循循之有方愧驽才之难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或请益而不易言念及此不禁神伤吾师倘能赦兹愚鲁使生等得备薄馔于月×日午十二时假西长安街××饭店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肃请钧安陆晶清学生许广平谨启吕云章又'四条'一词乃鲁迅先生爱用以奚落女人的哭泣,两条眼泪,两条鼻涕,故云。有时简直呼之曰:四条胡同,使我们常常因之大窘。"〔2〕程门飞雪语出《宋史.杨时传》:"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旧时常用为尊师重道的故实。
260907致许寿裳季市兄:四日下午到厦门,即迁入校中,因未悉大略,故未发信,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玉堂〔1〕极被掣肘,校长有秘书姓孙,无锡人,可憎之至,鬼鬼似〔2〕皆此人所为,我与臤士等三人,虽已有聘书,而孙伏园等四人已到两星期,则校长尚未签字,与以切实之定议,是作态抑有中变,未可知也。
在国文系尚且如此,则于他系有所活动,自然更难。兄事〔3〕曾商量数次,皆不得要领,据我看去,是没有结果的。臤士于合同尚未签字,或者亦不久居,我之行止,临时再定。
此地风景极佳,但食物极劣,语言一字不懂,学生止四百人,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离市约十余里,消息极不灵通,上海报章,到此常须一礼拜。
迅上八〔九〕月七日之夜〔1〕玉堂即林语堂。参看330620①信注〔1〕。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下文的"校长",指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海澄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秘书",指孙贵定,字蔚深,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校长办公室秘书。
〔2〕臤士即沈兼士。参看261219信注〔1〕,当时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
〔3〕这里的"兄事",指为许寿裳谋职一事。
260916致韦素园素园兄:到厦后寄一明信片,想已到。昨得四日来信,此地邮递甚迟,因为从上海到厦门的邮件,每星期只有两三回,此地又是一离市极远之地,邮局只有代办所(并非分局),所以京,沪的信,往往要十来天。
收到寄野的信,说廿七动身,现在想已到了。
《莽原》请寄给我一本(厦门大学国学院),另外十本,仍寄西三条二十一号许羡苏先生收。
此地秋冬并不潮湿,所以还好,但五六天前遇到飓风,却很可怕(学校在海边),玉堂先生的家,连门和屋顶都吹破了,我却无损失。它吹破窗门时,能将粗如筷子的螺丝钉拔出,幸而听说这样的风,一年也不过一两回。
林先生太忙,我看不能做文章了。我自然想做,但二十开学,要忙起来,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或译或做,我总当寄稿。
迅九月十六日260920致韦素园素园兄:寄上稿子〔1〕四张,请察收。
《关于鲁迅......》及《出了象牙之塔》,请各寄三本来,用挂号为妥。
到此地也并不较闲,再谈罢。
迅九,二十〔1〕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收入《朝花夕拾》。
261003致章廷谦矛尘兄:来信早到,本应早复,但因未知究竟在南在北,所以迟迟。昨接乔〔1〕峰信,今天又见罗常培君,知道已由上〔2〕海向杭,然则确往道墟而去矣,故作答。
且夫厦大之事,很迟迟,虽云办妥,而往往又需数日,总而言之,有些散漫也。但今川资既以需时一周之电汇而到,则此事已无问题;而且聘请一端,亦已经校长签字,则一到即可取薪水矣,此总而言之,所望令夫人可以荣行之时,即行荣行者也。
若夫房子,确是问题,我初来时,即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要练脚力,甚合式也。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倘有夫人,则当住于一座特别的洋楼曰"兼爱楼",而可无高升生物院之虑矣。惟该兼爱楼现在是否有空,则殊不可知。总之既聘教员,当有住所,他们总该设法。即不配上兼爱楼如不佞,现亦已在图书馆楼上霸得一间房子,一上一下,只须走扶梯五十二级矣。
但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加工钱一元,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然而菜则依然难吃也,吃它半年,庶几能惯欤。又开水亦可疑,必须自有火酒灯之类,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否则,不安心者也。
夜深了,将来面谈罢。
迅上十,三,夜〔1〕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北京人,语言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讲师。
〔2〕道墟绍兴的一个集镇,章廷谦的故乡。
261004①致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丛芜素园兄:霁野前回寄上文稿一篇(《旧事重提》之六),想已早到。十九日的来信,今已收到了。别人的稿子,一篇也没有寄来。
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
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我初到时穿夏布衫,现在也还穿夏布衫,听说想脱下它,还得两礼拜。
在上海时看见章雪村,他说想专卖《未名丛刊》(大约只是上海方面),我没有答应他,说须得大家商量,以后就不提了。近来不知道他可曾又来信?他的书店,大概是比较的可靠的。但应否答应他,应仍由北京方面定夺。
迅十,四261004②致许寿裳季黻兄:十九日来函,于月底已到。思一别遂已匝月,为之怅然。此地虽是海滨,背山面水,而少住几日,即觉单调;天气则大抵夜即有风。
学校颇散漫,盖开创至今,无一贯计画也。学生止三百余人,因寄宿舍满,无可添招。此三百余人分为豫科及本科,本科有七门〔1〕,门又有系,每系又有年级,则一级之中,寥落可知。弟课堂中约有十余人,据说已为盛况云。
语堂亦不甚得法,自云与校长甚密,而据我看去,殊不尽然,被疑之迹昭著。国学院中,佩服陈源〔2〕之顾颉刚〔3〕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女师大旧职员之黄坚〔4〕,亦在此大跋扈,不知招之来此何为者也。
兄何日送家眷南行?闻中日学院〔5〕已成立,幼渔颇可说话,但未知有无教员位置,前数日已作函询之矣。兄可以自己便中面询之否?
此间功课并不多,只六小时,二小时须编讲义,但无人可谈,寂寞极矣。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或者在此至多不过一年可敷衍欤?上月因嫌黄坚,曾辞国学院兼职,后因玉堂为难,遂作罢论。
北京想已凉,此地尚可著夏衣,但较之一月前确已稍凉矣。专此顺颂曼福。
树上十月四日
注释:
〔1〕七门指文、理、教育、商、法、工、医七科。
〔2〕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3〕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
〔4〕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当时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5〕中日学院中国人与日本人合办,一九二五年在天津成立,一九三一年解散。马幼渔曾在该院任教。
261007致韦素园素园兄:寄来的书籍一包,收到了。承给我《外套》三本,谢谢。
今寄上《莽原》稿一篇〔1〕,请收入。到此仍无闲暇,做不出东西。
从《莽原》十九期起,每期请给我两本。我前。。。。回曾经通信声明,这信大约没有到。但以前的不必补奇,只要从十九期起就好了。
《旧事重提》我还想做四篇,尽今年登完,但能否如愿,也殊难说,因为在此琐事仍然多。
迅上十月七日夜
注释:
〔1〕指《父亲的病》,后收入《朝花夕拾》。
261010致章廷谦矛尘兄:侧闻大驾过沪之后,便奉一书于行素堂〔1〕,今得四日来信,略答于下----你同斐君太太将要担任什么一节,今天去打听,据云玉堂已自有详函去了,所以不好再问。记得前曾窃闻:太太教官话,老爷是一种干事。至于何事之干,则不得而知。
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但这些都无大关系,一听他们之便而已。至于住处,却已搬出生物之楼而入图书之馆,楼只两层,扶梯亦减为二十六级矣。饭菜仍不好。你们两位来此,倘不自做菜吃,怕有"食不下咽"之虞。
北京大捕之事,此间无消息。不知何日之事乎?今天接到钦文九月卅日从北京来之信,绝未提起也。
迅上十月十日
注释:
〔1〕行素堂章廷谦老家住所的名称。
261015致韦素园素园兄:九月卅日的信早收到了,看见《莽原》,早知道你改了号,而且推知是因为林素园〔1〕。但写惯了,一写就又写了素园,下回改正罢。
《莽原》我也总想维持下去。但不知近来销路何如?这几天做了两篇〔2〕,今寄上,可以用到十一月了,续稿缓几时再寄。这里虽然不欠薪,然而如在深山中,竟没有什么作文之意。因为太单调,而小琐事却仍有的,加以编讲义,弄得人如机器一般了。
《坟》的上面,我还想做一篇序并加目录,但序一时做不出来,想来一时未必印成,将来再说罢。
听说北新要迁移〔3〕了,不知迁了没有?寄小峰一笺,请即加封寄去为荷。
批评《彷徨》的两篇文章,已见过了,没有什么意思。
此后寄挂号信,用社名便当呢?还是用你的号便当?你的新号(漱园)的印章,已刻了么?
迅十,一五,夜。
注释:
〔1〕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曾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随教育总长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北京女师大,并于该校被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时出任学长。
〔2〕指《琐记》和《藤野先生》,后收入《朝花夕拾》。
〔3〕北新要迁移一九二六年十月北新书局因发行《语丝》被张作霖查封,同年底迁往上海。
261019致韦素园漱园兄:今天接十月十日信片,知已迁居〔1〕。
我于本月八日寄出稿子一篇,十六日又寄两篇(皆挂号),而皆系寄新开路,未知可不至于失落否?甚念,如收到,望即示知。
否则即很为难,因我无草稿也。
迅十,十九〔1〕挺未名社自新开路五号迁至西老胡同一号。
261023致章廷谦矛尘兄:十五日信收到了,知道斐君太太出版〔1〕延期,为之怃然。其实出版与否,与我无干,用"怃然"殊属不合,不过此外一时也想不出恰当的字。总而言之,是又少拿多少薪水,颇亦可惜之意也。至于瞿英乃〔2〕之说,那当然是靠不住的,她的名字我就讨厌,至于何以讨厌,却说不出来。
伏园"叫苦连天",我不知其何故也。"叫苦"还是情有可原,"连天"则大可不必。我看此处最不便的是饭食,然而凡有太太者却未闻叫苦之声。斐君太太虽学生出身,然而煎荷包蛋,燉牛肉,"做鸡蛋糕"〔3〕,当必在六十分以上,然则买牛肉而燉之,买鸡蛋而糕之,又何惧食不甘味也哉。
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但你既然"便是黄连也决计吞下去",则便没有问题。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你将来最好是随时预备走路,在此一日,则只要为"薪水",念兹在兹,得一文算一文,庶几无咎也。
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4〕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玉堂还太老实,我看他将来是要失败的。
兼士星期三要往北京去了。有几个人也在排斥我。但他们很愚,不知道我一走,他们是站不住的。
这里的情形,我近来想到了很适当的形容了,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学校的精神似乎很像南开〔5〕,但压迫学生却没有那么利害。
我现在寄居在图书馆的楼上,本有三人,一个〔6〕搬走了,伏园又去旅行,所以很大的洋楼上,只剩了我一个了,喝了一瓶啤酒,遂不免说酒话,幸祈恕之。
迅上十月二十三日灯下斐君太太尊前即此请安不另,如已出版,则请在少爷前问候。
注释:
〔1〕出版这里戏指分娩。
〔2〕瞿英乃当时北京妇产科大夫。
〔3〕"做鸡蛋糕"《新女性》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载有孙伏园的《蛋糕制造方法的灌输与妇女根本问题的讨论》。同刊第八号又载有岂明的《论做鸡蛋糕》。这里是随手引用。
〔4〕某君指顾颉刚。
〔5〕南开指当时私立的天津南开大学。
〔6〕指张颐,字真如,四川叙永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文科哲学系教授。
261029①致陶元庆璇卿兄:今天收到二十四日来信,知道又给我画了书面,感谢之至。惟我临走时,曾将一个武者小路作品的别的书面交给小峰,嘱他制板印刷,作为《青年的梦》〔1〕的封面。现在不知可已印成,如已印成,则你给我画的那一个能否用于别的书上,请告诉我。小峰那边,我也写信问去了。
《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板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但第二版我还未见过,这是从通信里知道的。
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但一面想,兄如可以画,我自然也很希望。现在就都开列于下:一《卷葹》这是王品青所希望的。乃是淦女士〔2〕的小说集,《乌合丛书》之一。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品青希望将书名"卷葹"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此稿大约日内即付印,如给他画,请直寄钦文转交小峰。
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的安特来夫戏剧,内容大概是一个公爵举行假面跳舞会,连爱人也认不出了,因为都戴着面具,后来便发狂,疑心一切人永远都戴着假面,以至于死。这并不忙,现在尚未付印。
三《坟》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字是这鲁迅样写:墳(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所作)请1907--25你组织进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
以上两种是〔3〕未名社的,《黑假面人》不妨从缓,因为还未付印。《坟》如画成,请寄厦门,或寄钦文托其转交未名社均可。
还有一点,董秋芳〔4〕译了一本俄国小说革命以前的,叫作《争自由的波浪》,稿在我这里,将收入《未名丛刊》中了,可否也给他一点装饰。
一开就是这许多,实在连自己也觉得太多了。
鲁迅十月二十九日
注释:
〔1〕《青年的梦》即《一个青年的梦》,剧本,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鲁迅译并作序,一九二二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一九二七年七月北新书局再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再版本封面改用武者小路实笃自己作的一幅画。
〔2〕淦女士即冯沅君(1900--1974),原名淑兰,河南唐河人,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卷葹》,一九二七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
〔3〕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东欧文学,曾出版《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结束。
〔4〕董秋芳(1897--1977)笔名冬芬,浙江绍兴人,翻译工作者。《争自由的波浪》,由英译本转译的俄国小说和散文集,高尔基等作,鲁迅校订并作《小引》,一九二七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261029②致李霁野霁野兄:十四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走了十五天。《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黑假面人》的也一同托了他。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为《莽原》,我本月中又寄了三篇稿子,想已收到。我在这里所担的事情太繁,而且编讲义和作文是不能并立的,所以作文时和作了以后,都觉无聊与苦痛。稿子既然〔1〕这样少,长虹又在捣乱见上海出版的《狂飙》〔2〕我想:不如至廿四期止,就停刊,未名社就,专印书籍。一点广告,大约《语丝》还不至于拒绝罢。据长虹说,似乎《莽原》便是《狂飙》的化身,这事我却到他说后才知道。我并不希罕"莽原"这两个字,此后就废弃它。《坟》也不要称《莽原丛刊》〔3〕之一了。至于期刊,则我以为有两法,一,从明年一月起,多约些做的人,改名另出,以免什么历史关系的牵扯,倘做的人少,就改为月刊,但稿须精选,至于名目,我想,"未名"就可以。二,索性暂时不出,待大家有兴致做的时候再说。《君山》〔4〕单行本也可以印了。
这里就是不愁薪水不发。别的呢,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上海信的往来也需两星期,书是无论新旧,无处可买。我到此未及两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
《小约翰》还未动手整理,今年总没工夫了,但陶元庆来信,却云已准备给我画封面。
总之,薪水与创作,是势不两立的。要创作,还是要薪水呢?我现在一时还决不定。
此信不要发表。
迅上十,二九,夜《坟》的序言,将来当做一点寄上。
(此信的下面,自己拆过了重封的。)
注释:
〔1〕长虹捣乱指高长虹攻击韦素园等事。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一文,就《莽原》半月刊未载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和高歌的小说《剃刀》,对韦素园横加指摘,并对鲁迅进行攻击。文中还说:"它(指《莽原》)的发生,与《狂飙》周刊的停刊,显有关连,或者还可以说是主要原因,......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等。鲁迅在下文中说"似乎《莽原》就是《狂飙》的化身",即据此。
〔2〕《狂飙》文艺周刊,高长虹主编,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附于《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复刊,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
〔3〕《莽原丛刊》莽原社计划出版的一种丛书,后改名《未名新集》。
〔4〕《君山》诗集,韦丛芜作,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新集》之一。
261104致韦素园漱园兄:杨先生的文〔1〕,我想可以给他登载,文章是絮烦点,但这也无法,自然由作者负责,现在要十分合意的稿,也很难。
寄上《坟》的序和目录,又第一页上的一点小画,〔2〕请做锌板,至于那封面,就只好专等陶元庆寄来。序已另抄拟送登《语丝》,请不必在《莽原》发表。这种广告性的东西,登《莽原》不大好。
附上寄小峰的一函,是要紧的,请即叫一个可靠的人送去。
注释:
〔1〕指杨丙辰所译德国席勒的《<强盗>初版原序》,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
〔2〕指鲁迅为《坟》内封所绘的图案画。
261107致韦素园漱园兄:十月廿八及卅日信,今日俱收到。长虹的事,我想这个广告〔1〕也无聊,索性完全置之不理。
关于《莽原》封面,我想最好是请司徒君〔2〕再画一个,或就近另设法,因为我刚寄陶元庆一信,托他画许多书面,实在难于再开口了。
丛书〔3〕及《莽原》事,最好是在京的几位全权办理。书籍销售似不坏,当然无须悲观。但大小事务,似不必等我决定,因为我太远。
此地现只能穿夹衣。薪水不愁,而衣食均不便,一一须自经理,又极不便,话也一句不懂,连买东西都难。又无刺戟,思想都停滞了,毫无做文章之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心思颇活动,想走到别处去。
注释:
〔1〕广告指《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一九二六年八月)所载的《狂飙社广告》。高长虹等人在《广告》中冒称与鲁迅合办《莽原》,共编《乌合丛书》,暗示读者,似乎鲁迅也参与了他们的所谓"狂飙运动"。
〔2〕司徒君即司徒乔(1902--1958),广东开平人,画家。
〔3〕丛书指《乌合丛书》。
261109致韦素园漱园兄:昨才寄一信,下午即得廿九之信片。我想《莽原》只要稿,款两样不缺,便管自己办下去。对于长虹,印一张夹在里面也好,索性置之不理也好,不成什么问题。他的种种话,也不足与辩,《莽原》收不到,也不能算一种罪状的。
要鸣不平,我比长虹可鸣的要多得多多;他说以"生命赴《莽原》"了,我也并没有从《莽原》延年益寿,现在之还在生存,乃是自己寿命未尽之故也。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1〕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将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这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
《狂飙》已经看到四期,逐渐单调起来了。较可注意的倒是《幻洲》〔2〕《莽原》在上海减少百份,也许是受它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但第二期已不及第一期,未卜后来如何。《莽原》如作者多几个,大概是不足虑的,最后的决定究竟是在实质上。
注释:
〔1〕尚钺字宗武,或作钟吾,河南罗山人,历史学家。曾参加莽原社,后又为狂飙社成员。他的小说稿,指《斧背》,共十九篇,后于一九二八年五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列为《狂飙丛书》之一。
〔2〕《幻洲》文艺性半月刊,叶灵风、潘汉年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出至第二卷第八期停刊。
261111致韦素园漱园兄:饶超华的《致母》,〔1〕我以为并不坏,可以给他登上,今寄回;其余的已直接寄还他了。
小酩〔2〕的一篇太断片似的,描写也有不足,以不揭载为是,今亦寄回。
《莽原》背上可以无须写何人所编,我想,只要空写一"莽原合本就够了格1"。
我本想旅行一回,〔3〕后来中止了,因为一请假,则荒废的事情太多。
迅十一月十一日
注释:
〔1〕饶超华广东梅县人。当时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莽原》投稿者。所作小品文《致母》,载《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2〕小酩即李小酩,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莽原》的投稿者。
〔3〕旅行一回鲁迅曾拟应中山大学之约前往"议定学制",后未成行。参看《两地书.五六》。
261113①致韦素园漱园兄:前天写了一点东西,拟放在《坟》之后面,还想在《语丝》上先发表一回(本来《莽原》亦可,但怕太迟,离本书的发行已近,而纸面亦可惜),今附上致小峰一笺,请并稿送去,印后仍收回,交与排《坟》之印局。倘《坟》之出版期已近,则不登《语丝》亦可,请酌定。
首尾的式样,写一另纸,附上。
目录上也须将题目添上,但应与以上之本文的题目离开一行。
迅十一,十三另页起上空四格〔1〕写在坟后面空一行5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结尾的样子。作结----空一行空一行5一九二下空六,十一,十一,夜。四格5鲁迅下空八格〔1〕此处及下面排在铅字左上角的阿拉伯数字,系指铅字的大小号数。
261113②致李小峰〔1〕小峰兄:有一篇《坟》的跋,不知《语丝》要一印否?如要,请即发表。排后并请将原稿交还漱园兄,并嘱手民〔2〕,勿将原稿弄脏。
迅十一,十三〔1〕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北新书局主持人。
〔2〕手民排字工人。
261116致章廷谦矛尘兄:十一日的信,今天收到了。令夫人尚未将成绩发表,殊令局外人如不佞者亦有"企予望之"〔1〕之意矣。所愿此信到时,早已诞育麟儿,为颂为祝也。敝厦一切如常,鼓浪屿亦毫不鼓浪,兄之所闻,无一的确;家眷分居,亦无其事,岂陈源已到绍兴,遂至"流言"如此之多乎哉?伏园已回,下月初或将复往。小峰已寄来《杂纂》〔2〕一册,但非精装本耳。此地天气渐凉,可穿两件夹衣。今日又收到小峰七日所发信,皆闲谈也,并闻。
迅上十一月十六日之夜〔1〕"企予望之"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2〕《杂纂》参看260714信注〔2〕。
261120致韦素园漱园兄:《旧事重提》又做了一篇〔1〕,今寄上。这书是完结了。明年如何?如撰者尚多,仍可出版,我当另寻题目作文,或登《小约翰》,因另行整理《小约翰》的工夫,看来是没有的了。
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后,便对人说:我编《莽原》,《未名》,《乌合》三种,俱与所谓什么狂飙运动无干,投稿者多互不相识,长虹作如此广告,未免过于利用别人了。此语他似乎今已知道,在《狂飙》上骂我〔2〕。我作了一个启事〔3〕,给开一个小玩笑。今附上,请登入《莽原》。又登《语丝》者一封,请即叫人送去为托。
迅十一月二十日
注释:
〔1〕指《范爱农》。
〔2〕在《狂飙》上骂我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攻击鲁迅是"世故老人"。"戴其纸糊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等等。
〔3〕启事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261121①致韦素园漱园兄:十三日来信收到了。《坟》的序,跋;《旧事重提》第十(已完),俱已寄出,想必先此信而到了。
《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亦不妥。我想不如用《未名新集》〔1〕,即以《君山》为第一本。《坟》独立,如《小说史略》一样。
未名社的事,我以为有两途:(1)专印译,著书;(2)兼出期刊。《莽原》则停刊。
如出期刊,当名《未名》〔2〕,系另出,而非《莽原》改名。但稿子是一问题,当有在京之新进作者作中坚,否则靠不住。刘〔3〕,张〔4〕未必有稿,沅君一人亦难支持,我此后未必能静下,每月恐怕至多只能做一回。与其临时困难,不如索性不出,专印书,一点广告,大约《语丝》上还肯登的。
我在此也静不下,琐事太多,心绪很乱,即写回信,每星期须费去两天。周围是像死海一样,实在住不下去,也不能用功,至迟到阴历年底,我决计要走了。
迅十一,廿一日
注释:
〔1〕《未名新集》丛书,专收未名社成员的创作,一九二七年三月起由未名社陆续出书。
〔2〕《未名》文学半月刊,未名社编辑,一九二八年一月《莽原》半月刊停刊后于北京创刊,一九三○年四月停刊。
〔3〕指刘复(1891--1934),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参看《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4〕指张凤举。
261121②致章廷谦矛尘兄:前得十日信后,即于十七日奉上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日来信了,路上走了十天,真奇。你所闻北京传来的话〔1〕,都是真的,伏将于下日初动身,我则至多敷衍到本学期末,广大〔2〕的聘书,我已接收了。玉堂对你,毫无恶意,他且对伏园说过几次,深以不能为你的薪水争至二百为歉。某公之阴险,他亦已知,这一层不成问题,所虑者只在玉堂自己可以敷衍至何时之问题耳,盖因他亦常受掣肘,不能如志也。所以你愈早到即愈便宜,因为无论如何,川资总可挣到手,一因谣言〔3〕,一因京信,又迟迟不行,真可惜也。
某公之阴谋,我想现在已可以暂不对你了。盖彼辈谋略,无非欲多拉彼辈一流人,而无位置,则攻击别人。今则在厦者且欲相率而去,大小饭碗,当空出三四个,他们只要有本领,拿去就是。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4〕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5〕来厦,欲以代替,而终于无法,现住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兼差〔6〕(伏曾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郑某现仍在,据说是在研究"唯物史观之中国哲学史"云。试思于自己不吃之饭碗,顾公尚不能移赠别人,而况并不声明不吃之川岛之饭碗乎?他们自己近来似乎也不大得意,大约未必再有什么积极的进攻。他们的战将也太不出色,陈万里〔7〕已经专在学生会上唱昆腔,被大家"优伶蓄之"〔8〕我的意见是: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来。倘令夫人已生产,你们一同来,倘尚无消息,你就赶紧先来,夫人满月后,可托人送至沪,又送上船,发一电,你去接就是了。但两人须少带笨重器具,准备随时可走。总而言之,勿作久长之计,只要目前有钱可拿,便快快来拿,拿一月算一月,能拿至明年六月,固好,即不然,从速拿,盘川即决不会折本,若河翔审慎,则现在的情形时时变化,要一动也不能动了。
其实呢,这里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校中的教员,谋为"永久教员"者且大有其人。我的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
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上勿下要\来带者!〔9〕其实这种"活得弗靠活",亦不足为训,所以因我要走而以为厦大不可一日居,也并非很好的例证。至于"糟不可言",则诚然不能为讳,然他们所送聘书上,何尝声明要我们来改良厦大乎?薪水不糟,亦可谓责任已尽也矣。
迅上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释:
〔1〕北京传来的话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收到北京周作人信,言及鲁迅、孙伏园将离开厦门大学,劝他不必再去就职。
〔2〕广大即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十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中山大学。
〔3〕谣言据收信人回忆,当时听说如到厦门大学,因住房紧张,可能要夫妇分居。
〔4〕陈乃乾浙江海宁人。当时受聘为厦门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和国学院图书部干事、文科国文系讲师,后未到职。
〔5〕郑某指程憬,字仰之,安徽绩溪人。原为胡适的书记员,曾托顾颉刚代谋教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到厦门,住南普陀寺候职。
〔6〕伏园兼差当时孙伏园曾在南普陀寺附设的闽南佛学院兼课。
〔7〕陈万里(1891--1969)江苏吴县人。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考古学导师、造型部干事、国文系名誉讲师,讲授曲选及曲史课程。
〔8〕"优伶蓄之"语出《汉书.严助传》,优伶,原作俳优。
〔9〕\(上勿下要\来带者绍兴方言,不要呆在这里的意思。
261122致陶元庆璇卿兄:给我的信昨天收到了。画尚未到,大概因为挂号的,照例比信迟。收到后当寄给钦文去。
《争自由的波浪》我才将原稿看好付邮,或者这几天才到北京,即使即刻付印,也不必这么急。秋芳着急,是因为他性急的缘故。
未名社以社的名义托画,又须于几日内画成,我觉得实在不应该,他们是研究文艺的,应当知道这道理,而做出来的事还是这样,真可叹。《卷葹》的封面,他们先前托我转托,我没有十分答应,后来终于写上了。近闻他们托司徒乔画了一张。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
我只是一批一批的索画,实在抱歉而且感激。
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Ecke〔1〕,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故乡》是剑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椅背和坐上的图线,和全部的直线有些不调和。太阳画得极好。
迅上十一月二十二日
注释:
〔1〕Ecke即GustavEcke,德国人,曾用中国名艾谔风。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讲授德文、希腊文及希腊哲学等。
261123致李霁野霁野兄:十四日发出的快信,今天收到了,比普通的信要迟一天。因为这里只有一个邮政代办处,不分送,要我们自己去留心。一批信到,他就将刊物和平常信塞在玻璃柜内,给各人自己拿去。这才慢慢地将宝贵的----包裹,挂号信,快信----一批在房里打开,一张一张写通知票,将票又塞在玻璃柜内,我们见票,取了印章去取信,所以凡是快信,一定更慢,外边不知道这情形,时常上当的。
《莽原丛刊》,我想改作《未名新集》;《坟》不在内,独立,如《中国小说史略》一般。该集以《君山》为第一部。至于半月刊,我想,应以你们为中坚,如大家都有兴趣,或译或作,就办下去,半侬,沅君们的帮忙,都不能作为基本的。至于我,却很难说,因为仍不能用功,我确拟于年底离开这里。这里是死海一样,不愁没饭吃,而令人头痛之事常有,往往反而不想吃饭,宁可走开。此后之生活状态如何,此时实难豫测,大约总是仍不能关起门来用功的。我现在想,一月一回,该可以作,因为倘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如近来这几月,就是如此。
你们青年且上一年阵试试看,卖不去也不要紧,就印千五百,倘再卖不去,就印一千,五百,再卖不去,关门未迟。如果以为如此不妥,那就停刊罢。
倘不停,我想名目也不必改了,还是《莽原》。《莽原》究竟不是长虹家的。我看他《狂飙》第五期上的文章,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我已作了一个启事,寄《北新》〔1〕,《新女性》〔2〕,《语丝》,《莽原》,和他开一个小玩笑。
《莽原》的合本,我以为最好至廿四期出全了,一齐发卖。
"圣经"两字,使人见了易生反感,我想就分作两份,称"旧约"及"新约"的故事〔3〕,何如?
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记得七斤曾说用了若干钱,将钱数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钉。倘其中没有七斤口述的钱数(手头无书,记不清了),则都改十六或十八均可。
关于《创世纪》的作者,随他错去罢,因为是旧稿〔4〕。人猿间确没有深知道连锁,这位Haeckel〔5〕博士一向是常不免"以意为之"的。
陶元庆君来信言《坟》的封面已寄出但未到,嘱我看后寄给钦文。用三色版印,钦文于校三色板多有经验,我想就托他帮忙罢。只要知道这书大约多少厚,便可以付京华印书面。
迅十一月二十三日
注释:
〔1〕《北新》综合性期刊,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孙福熙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潘梓年等编辑,一九三○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2〕《新女性》月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创刊,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卷。上海新女性社发行。
〔3〕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拟将美国房龙(520yd.com)的儿童读物插图本《<圣经>的故事》译成中文,为此征求鲁迅意见,后未译成。
〔4〕旧稿指鲁迅作于一九○七年的《人之历史》。该文有摩西为《旧约全书》中《创世记》的作者的说法。
〔5〕Haeckel海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主要著作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等。
261128致韦素园漱园兄:十六日来信,今天收到了。我后又续寄《坟》跋一,《旧事重提》一,想已到。《狂飙》第五期已见过,但未细看,其中说诳挑拨之处似颇多,单是记我的谈话之处,就是改头换面的记述,当此文未出之前,我还想不到长虹至于如此下劣。这真是不足道了。关于我在京从五六年前起所遇的事,我或者也要做一篇记述发表,但未一定,因为实在没有工夫。
明年的半月刊,我恐怕一月只能有一篇,深望你们努力。我曾有信给季野,你大约也当看见罢。我觉得你,丛芜,霁野,均可于文艺界有所贡献,缺点只是疏懒一点,将此点改掉,一定可以有为。但我以为丛芜现在应该静养。
《莽原》改名,我本为息事宁人起见。现在既然破脸,也不必一定改掉了,《莽原》究竟不是长虹的。这一点请与霁野商定。
迅十一月廿八日《坟》的封面画,陶元庆君已寄来,嘱我看后转寄钦文,托他印时校对颜色,我已寄出,并附一名片,绍介他见你,接洽。这画是三色的,他于印颜色版较有经验,我想此画即可托他与京华接洽,并校对。因为是石印,大约价钱也不贵的。
261130致章廷谦矛尘兄:廿六信今天到。斐君太太已发表其蕴蓄,甚善甚善。绍兴东西,并不想吃,请无须"带奉",但欲得木版有图之《玉历钞传》〔1〕一本,未知有法访求否?此系善书〔2〕,书坊店不出售,或好善之家尚有存者。我因欲看其中之"无常"画像〔3〕,故欲得之。如无此像者,则不要也。
伏园复往,确系上任;我暂不走,〔4〕拟敷衍至本学期之末,而后滚耳,其实此地最讨厌者,却是饭菜不好。
小峰在北京,何以能"直接闻之于厦大",殊不可解。兄行期当转告玉堂。
迅上十一月卅日
注释:
〔1〕《玉历钞传》即《玉历至宝钞传》,共八章,是一部宣传封建迷信的书,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内容系讲述"地狱十殿"的情况,宣扬因果报应。
〔2〕善书宣传因果报应的书。旧时常由善男信女捐资刻印,免费赠送。
〔3〕"无常"画像无常,佛家语,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关于无常画像,可参看《朝花夕拾.后记》。
〔4〕伏园上任当时孙伏园到广州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
261205致韦素园漱园兄:十一月二十八日信已到。《写在<坟>后面》登《莽原》,也可以的。《坟》能多校一回,自然较好;封面画我已寄给许钦文了,想必已经接洽过。
《君山》多加插画,很好。我想:凡在《莽原》上登过而印成单行本的书,对于定《莽原》全年的人,似应给以特别权利。倘预定者不满百人,则简直各送一本,倘是几百,就附送折价(对折?)券(或不送而只送券亦可),请由你们在京的几位酌定。我的《旧事重提》(还要改一个名字)出版时,也一样办理。
《黑假面人》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也不合算,倘自己出版,则以《往星中》为例,半年中想亦可售出六七百本。未名社之立脚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所以此书仍不如自己印。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当于一月十日以前将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为借给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卖去,除掉付印之本钱后,然后再以收来的钱还我就好了。这样,则未名社多了一本书,且亦不至于为别的书店去作苦工,因为我想剧本卖钱是不会多的。
对于《莽原》的意见,已经回答霁野,但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致,就办下去罢。当初我说改名,原为避免纠纷,现长虹既挑战,无须改了,陶君的画,或者可作别用。明年还是叫《莽原》,用旧画。退步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但这仍请你与霁野酌定,我并不固执。至于内容,照来信所说就好。我的译作,现在还说不定什么题目,因为正编讲义,须十日后才有暇,那时再想。我不料这里竟新书旧书都无处买,所以得材料就很难,或者头几期只好随便或做或译一点,待离开此地后,倘环境尚可,再来好好地选译。我到此以后,琐事太多,客也多,工夫都耗去了,一无成绩,真是困苦。将来我想躲起来,每星期只定出日期见一两回客,以便有自己用功的时间,倘这样下去,将要毫无长进。
留学自然很好,但既然对于出版事业有兴趣,何妨再办若干时。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1〕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2〕而外,一无所有。所以偶然作一点格言式的小文,似乎还可观,一到长篇,便不行了,如那一篇《论杂交》〔3〕,直是笑话。他说那利益,是可以没有家庭之累,竟不想到男人杂交后虽然毫无后患,而女人是要受孕的。
在未名社的你们几位,是小心有余,泼辣不足。所以作文,办事,都太小心,遇见一点事,精神上即很受影响,其实是小小是非,成什么问题,不足介意的。但我也并非说小心不好,中国人的眼睛倘此后渐渐亮起来,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
长虹的骂我,据上海来信,说是除投稿的纠葛之外,还因为他与开明书店商量,要出期刊,遭开明拒绝,疑我说了坏话之故。我以为这是不对的,由我看来,是别有两种原因。一,我曾在上海对人说,长虹不该擅登广告,将《乌合》《未名》都拉入什么"狂飙运动"去,我不能将这些作者都暗暗卖给他。大约后来传到他耳朵里去了。二,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将来当面再谈罢,我想,大约暑假时总要回一躺[趟]北京。
前得静农信,说起《菤葹》,我为之叹息,他所听来的事,和我所经历的是全不对的。这稿子,是品青来说,说愿出在《乌合》中,已由小峰允印,将来托我编定,只四篇。我说四篇太少;他说这是一时期的,正是一段落,够了。我即心知其意,这四篇是都登在《创造》上的,现创造社〔4〕不与作者商量,即翻印出售,所以要用《乌合》去抵制他们,至于未落创造社之手的以后的几篇,却不欲轻轻送入《乌合》之内。但我虽这样想,却答应了。不料不到半年,却变了此事全由我作主,真是万想不到。我想他们那里会这样信托我呢?你不记得公园里饯行那一回的事吗?静农太老实了,所以我无话可答。不过此事也无须对人说,只要几个人(丛,霁,静)心里知道就好了。
迅十二月五日
注释:
〔1〕《绥惠略夫》即《工人绥惠略夫》,中篇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一九二二年五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2〕郭译的尼采小半部指郭沫若所译尼采著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第一部,曾连载于《创造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3〕《论杂交》高长虹作,载《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文中有"家庭和婚姻的束缚尤其是女子的致命伤","杂交对于女子解放是有可惊的帮助","是解放的唯一途径"等语。
〔4〕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七年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261208致韦素园漱园兄:十二月一日的快信,今天收到了。关于《莽原》的事,我于廿九,本月五日所发两信,均经说及,现在不必重说。总之:能办下去,就很好了。我前信主张不必改名,也就因为长虹之骂,商之霁野,以为何如?
《范爱农》一篇,自然还是登在24期上,作一结束。来年第一期,创作大约没有了,拟译一篇《说"幽默"》〔1〕,是日本鹤见祐辅作的,虽浅,却颇清楚明白,约有十面,十五以前可寄出。此后,则或作译,殊难定,因为此间百事须自己经营,繁琐极了,无暇思索;译呢,买不到一本新书,没有材料。这样下去,是要淹死在死海里了,薪水虽不欠,又有何用?我决计于学期末离开,或者可以较有活气。那时再看。倘万不得已,就用《小约翰》充数。
我对于你们几位,毫无什么意见;只有对于目寒〔2〕是不满的,因为他有时确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但他不在京了,不成问题。至于长虹,则我看了他近出的《狂飙》,才深知道他很卑劣,不但挑拨,而且于我的话也都改头换面,不像一个男子所为。他近来又在称赞周建人〔3〕了,大约又是在京时来访我那时的故技。
《莽原》印处改换也好。既然销到二千,我想何妨增点页数,每期五十面,纸张可以略坏一点(如《穷人》那样),而不加价。因为我觉得今年似乎薄一点。
迅十二月八日
注释:
〔1〕《说"幽默"》日本鹤见祐辅作,译文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思想.山水.人物》、《欧美名士之印象》等。
〔2〕目寒即张目寒(1903--1980),安徽霍丘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时的学生。
〔3〕称赞周建人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发表的《关于性》中说:"最近科学的还是周建人的文字,他可以给人一些关于性的科学的常识,这在目前是很难得到的。"又在同刊第八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张竞生可以休矣》一文中说:"我更希望周建人先生更勇敢地为科学作战!"261219致沈兼士〔1〕兼士兄:十四日奉一函,系寄至天津,想已达。顷得十四日手书,具悉种种。厦校本系削减经费,经语堂以辞职力争后,已复原,但仍难信,可减可复,既复亦仍可减耳。语堂恐终不能久居,近亦颇思他往,然一时亦难定,因有家室之累。亮公〔2〕则甚适,悠悠然。弟仍定于学期末离去;此校国文科第一年级生,因见沪报而来者,恐亦多将相率转学,留者至多一人而已。季黻多日无信,弟亦不知其何往,殊奇。孙公于今日上船;程某〔3〕(前函误作郑)渴欲补缺,顾公语语堂,谓得兄信,如此主张,而不出信相示,弟颇疑之。黄坚到厦,向语堂言兄当于阴历新年复来,而告孙公则云不来,其说颇不可究诘。语堂究竟忠厚,似乎不甚有所知,然亦无法救之,但冀其一旦大悟,速离此间,乃幸耳。文学史稿〔4〕编制太草率,至正月末约可至汉末,挂漏滋多,可否免其献丑,稍积岁月,倘得修正,当奉览也。丁公〔5〕亦大有去志;而矛尘大约将到矣;陈石遗〔6〕忽来,居于镇南关〔7〕,国学院中人纷纷往拜之。专此,敬颂禔福弟迅十二月十九日上午
注释:
〔1〕沈兼士(1887--1947)又作"坚士"、"臤士",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六年,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十月底离职。
〔2〕亮公即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历史学家。留学美国和德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继沈兼士之后,任厦门大学国学院主任。
〔3〕程某即程憬。
〔4〕文学史稿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文学史课程的讲义,即后来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
〔5〕丁公即丁丁山(1901--1952),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助教。
〔6〕陈石遗(1856--1937)名衍,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清末学部主事。一九二三年九月任厦门大学教授。一九二六年三月辞职。
〔7〕镇南关在厦门大学校内,明末郑成功抗清时所建。
261228致许寿裳〔1〕季芾兄:今日得廿一日来信,谨悉一一,前得北京信,言兄南旋,未携眷属,故信亦未寄嘉兴,曾以一笺托诗荃转寄,今味来书,似未到也。
此间多谣言,日前盛传公侠〔2〕下野,亦未知其确否〔3〕,故此函仍由禾转,希即与一确示。
厦大虽不欠薪,而甚无味,兼士早走,弟亦决于本学期结束后赴广大,大约居此不过尚有一月耳,盼复,余容续陈。
树人上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释:
〔1〕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公侠陈仪(1883--1960),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孙传芳所属浙江军第一师师长、徐州镇守使兼津浦南段警备总司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通电宣布浙江"自治",自任"自治"政府民政长,同月下旬即被孙解除武装和免去本兼各职。
〔3〕禾指浙江嘉兴。
261229①致韦素园漱园兄:二十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莽原》第二十三期,至今没有到,似已遗失,望补寄两本。
霁野学费的事〔1〕,就这样办罢。这是我先说的,何必客气。我并非"从井救人"〔2〕的仁人,决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正不必不安于心。此款大约至迟于明年(阳历)一月十日以前必可寄出,惟邮寄抑汇寄则未定。
《阶级与鲁迅》〔3〕那一篇,你误解了。这稿是我到厦门不久,从上海先寄给我的;作者姓张,住中国大学,似是一个女生(倘给长虹知道,又要生气),问我可否发表。我答以评论一个人,无须征求本人同意,如登《语丝》,也可以。因给写了一张信给小峰作绍介。其时还在《莽原》投稿发生纠葛之前,但寄来寄去,登出时却在这事之后了。况且你也未曾和我"捣乱",原文所指,我想也许是《明珠》〔4〕上的人们罢。但文中所谓H.M.女校,我至今终于想不出是什么学校。
至于关于《给----》〔5〕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
厦门有北新之书出售,而无未名的。校内有一人朴社的书,是他代卖的很可靠,我想大可以每种各寄五本不够,则由他函索,托他代售,折扣之例等等,可直接函知他,寄书时只要说系我绍介就是了。明年的《莽原》,亦可按期寄五本。人名地址是----福建厦门大学毛简先生(他号瑞章,但寄书籍等,以写名为宜。他是图书馆的办事员,和我很熟识)。
迅十二,二九。
注释:
〔1〕霁野学费的事参看261205信。
〔2〕"从井救人"语出马中锡《中山狼传》:"从井以救人"。
〔3〕《阶级与鲁迅》载《语丝》周刊第一○八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署名"一萼"(即曹轶欧)。
〔4〕《明珠》北京《世界日报》的文艺专栏张,恨水主编。当时该刊曾发表过一些讥刺鲁迅的作品,如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所载署名蝤的作者说:"对于周先生,我也常挖苦过。"〔5〕《给----》短诗,高长虹作,载《狂飙》周刊第七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诗中他自比为太阳,以月亮喻许广平,以黑夜影射鲁迅。
261229②致许寿裳〔1〕季芾兄:昨寄一函,已达否?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亟。聘书且是正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即颂曼福。
树人上十二月廿九日
注释:
〔1〕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