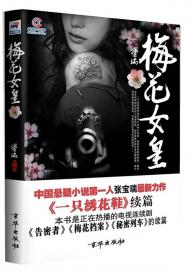尹福、马贵凑在窗前,听那老者自言自语,细听那些话是:“姬龙峰,名际可,龙峰乃其字,人号为神枪。明万历三十年生于山西蒲州诸冯里北义平村。姬龙峰家小康,地两顷,院十座,陕西数处有营业。龙峰自幼村中苦读,文成秀才,鹤立鸡群。然尊村地处闭塞,时有强人出没,尤为河西流寇所掠,村民如坠深渊。姬龙峰少负壮志,河滨练武功,南观中山习虎踞,西望黄河仿龙腾,酷暑严寒,未曾间断。一日月夜,正在村西练功,偶遇一叟,相指点并试手,返其形,退其影,纵横往来,目不及瞬。结果,姬败北,遂恳切求教。叟言:‘后生,力法尚佳,唯眼神不及,去河边洗之即可。’姬从之,走近河边水中洗眼,顿觉清亮,回首欲谢,叟已远去无踪。姬大悟,及后练功,首重二日,技遂大进。”
老者咳嗽一声,又接着背道:“世乱御敌,姬龙峰率众挥戈退群寇,搏杀在前。为精御敌本领,素日苦练大枪不辍,巧以檐椽为凭托,精习飞马点椽功。尊村街巷宽正,房舍高大,每间前后檐下搭椽十五根。龙峰在巷道上练点椽功时,握大枪,乘战马,打之飞奔,就在从椽旁疾驰而过之瞬间,要刺何椽,必是举枪即得,枪枪点中椽头心。龙峰家多座院落的房椽,经他无数次点练,扎得根根见深痕。战时浴血,平日挥汗,浇注出他的神枪技艺……”
马贵小声对尹福说:“他是在背形意拳的家谱呢。”
尹福掩住他的口,说:“听听也长教益,形意拳始祖姬际可是一位奇人。”
老者仍在聚精会神地背着:“龙峰于世之最大贡献六合拳,后称形意拳,正源于此神枪绝技。他常言:‘身处乱世,出可操兵执枪以自卫可也,若太平之日,刀兵销状,倘遇不测,将何以御之。’于是将枪理作拳理,融拳枪于一理,概为‘智勇’二字,六合、五行、阴阳、动静、进退、起落变化无穷是其智也;英气过人,是其勇也。他将此理贯诸散招之中,创世多势短拳绝艺;其势貌似鸡腿、龙身、熊膀、鹰捉、虎抱头,妙合诸生灵之绝。共十二大势,前六势为:夜马奔槽,熊膀,真形实相等;后六势为:虎捕兔、燕子取水、鹞子钻林等。前者形显力刚,后者势微劲柔。此乃姬氏初期创之拳势。在尊村称之‘际可拳’或‘龙峰拳’。龙峰二十余岁始奔少林寺,当时为访天下豪杰,出诸冯,过解州,翻中条山,渡黄河,抵达嵩山少林寺。从武僧把守的古刹山门处三进三出,安然无恙,一时远近震惊。龙峰多次往返少林寺与尊村之间。一日在翻越中条山时,突然马失前蹄,直坠深渊,险些丧生,只凭一身绝艺,攀挂悬崖树枝,陡壁攀登,才得脱险。而后,龙峰因其神勇,被聘为少林高师,精传其技。直至清兵入关,方归尊村。龙峰在寺内累计达十余年,长期以来清人严禁民间习武,遇者格杀,但龙峰所授之形意拳却在该寺秘传下来。龙峰德高艺绝。一年隆冬,前往陕西赤水筹款过年,南行百里到达风陵渡时,已近傍晚。忽闻船上老幼呼唤,妇婴泣啼。他疾步向前,只见几名船工无理欺人。但此船已离岸丈余,龙峰急唤停船,船工不从,反相辱骂。此时,已过天命之年的龙峰怒火中烧,不顾船岸已间隔三丈余远和黄河激流之险,飞身一纵,疾落船舷,众皆愕然。船客中有人辨出龙峰者,惊呼:‘这不是县北龙峰公吗?’言罢,艄公船工跪地赔罪,龙峰命其赔礼妇老,众皆称快。时有陕西匪盗东渡黄河,伙同晋南流寇,掠劫蒲州诸冯,铁骑突冲,刀枪劲鸣。时已年迈的龙峰不负众望,率众截敌于村西战场,神枪展威,银蛇吐信,所向披靡,亲挑寇魁,一时神枪震四方。康熙二十二年,龙峰谢世,享年八十二岁,实乃古之武寿星。龙峰虽怀绝技,然而一直在野为民,授艺以强民众,挥戈以保家园。去世后,葬于尊村祖墓中。”
老者背到此时,忽然大喝一声:“着!”轻捷如燕,双拳直贯屋顶,竟把屋顶戳出一个大窟窿,一个瘦小枯槁的人被他硬拽了下来。
尹福和马贵惊得后退几步。
尹福凑到窗前一看,那人正是江南飞鼠乔摘星。
乔摘星战战兢兢地说:“宋师爷,饶命!”
老者问道:“你是不是想盗《形意拳谱》?”
“不,不,我听说吉安堂气势恢弘,高手如云,想进来见识见识。”乔摘星想往后退,无奈,后脊梁被老者抓住,欲动不得。
老者怒气未消,说:“你这个惯偷,看我剁掉你的手指头!”
“别,别……大师,我有好东西进献给您。”说着,乔摘星从怀里摸出一个印信,递给老者。
老者将印信握在手中,一会儿五指分开,一股粉末儿飘散开来。
“我以为是什么稀奇玩意儿,原来是颗印信。”老者淡淡地说。
乔摘星声嘶力竭地喊:“那可是军机处的印信,能调动千军万马啊!”
“我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须千军万马。”老者冷冷地瞧着乔摘星。
乔摘星望望老者,心虚地说:“您老还剁我的手指头吗?”
“剁!”老者斩钉截铁地说。
“哎哟,我家有八十岁的老母呀!”乔摘星哭出声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你老母难道吃你盗来之食吗?”老者问。
乔摘星点点头。
“那你老母的肠子应当拉出来,有这等不仁不义的母亲,就会有这以盗窃为生的儿子。”老者的话语,比刀子还锋利。
“我还有传世之宝……”说着,乔摘星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盒子。
尹福的眼睛一亮,那正是光绪皇帝用来装玉玺的那个小盒子。
老者接过小盒子,一吹气,盒盖开了,露出玉玺。尹福发现里面没有光绪讲的包玉玺的香汗巾。
“原来是玉玺,我一个平民百姓,要这种东西有何用?”说着,老者就要用手握那玉玺。尹福一见,急得想冲进去,却被马贵拦住。
乔摘星一把夺过小盒子,哭道:“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老者微微一笑,拉过乔摘星的右手,轻轻一扳,乔摘星惨叫一声,三个断指落于地面,血淌了下来。
“滚吧,不要再来吉安堂!”老者微闭双眼,生气地说。
乔摘星将小盒子放进怀里,将身一纵,从屋顶窟窿处跃出,高声叫道:“宋世荣,咱们后会有期!”
尹福小声对马贵说:“我去追玉玺!”
话音未落,老者在屋内说:“屋外的壮士莫走,陪老夫玩玩儿。”说着,身形一闪,已拦住尹福、马贵。
“你就是宋世荣先生?”尹福问。
老者点点头,问道:“你是什么人?”
尹福不愿暴露身份,没有作声。
马贵一推尹福,说:“师父,你去追玉玺,我来应付他。”
尹福眼看乔摘星要溜掉,生怕他逃回浙江,也顾不上许多,说了句:“你要小心。”纵身跳到圈外,一人去追乔摘星。
马贵拦住宋世荣,一作揖,道:“久闻宋大师的名字,今日倒要请教一番。”
“你是何人?”宋世荣问。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马,名贵,江湖上叫我‘螃蟹马’。”
“原来是八卦门的英杰,好,方才那位老先生必是董海川的高徒、‘瘦尹’尹福了。”宋世荣的声音里有几分沉重。
马贵说:“你既已说出,我也不隐瞒,正是我们师徒俩。”
“尹老先生为皇族护驾,众人皆晓,为何跑到我们太谷来了?难道是为了观看我师兄车毅斋和师弟郭云深的比武?还是想观看《形意拳谱》?”宋世荣呵呵笑出声来。
马贵道:“一言难尽,还是请大师过招吧。”
宋世荣行如狸猫,身似蛟龙,手似蛇行,蜿蜒曲折,气似游云,动如翻浪,采用形意拳中的化劲,向马贵扑来。
马贵一招“脱身幻影”,两腿屈膝微蹲,走起八卦掌,就像蹦泥蹦水一般。突然间,将五指分开,拇指外侧向上,小指外侧向下,掌指向前,由上向下直劈,用力朝宋世荣左肩劈来。
宋世荣惊道:“好厉害的八卦掌!”他将身一纵,将五指微屈,自然分开,形似瓦垅,劲藏神门,使出形意拳中的虎形掌。这种掌的劲力由指梢,手掌的外沿,最终聚集在掌根,能爆发出抖绝之寸劲,达到震伤对方内脏之目的。
马贵见宋世荣这一掌呼呼带风,不敢轻视,猛地一招“叶底藏花”,使出八卦掌中的螺旋掌,正与宋世荣的掌打个正着,两掌相撞,铿锵有声,二人同时被震出一尺多远。
这时从院外奔进一个中年人。此人宽肩膀,粗脖子,头几乎是四方的,一双剑眉,身体结实有力,穿一身青布马褂。
他一进来,见到这般情景,叫道:“师兄,让我来对付这个雏儿!”
“‘神腿’贺永恒!还是与我比试一下吧。”话音未落,从房上跃下一个青年,他一双明亮的眸子,闪着精明的光泽。
“原来是‘神腿’杜心武到了!”贺永恒笑着朝杜心武作一个揖:“想不到我俩人的雅号一般响亮。”
杜心武笑道:“未必一般响亮。”话未说完,一招“娇鹰探爪”,右脚落成仆步,两手经胸前下插,手心向上,直扑贺永恒。
贺永恒见杜心武来势凶猛,一招“蛇滚绣球”,退了几步,然后一招“金蛇狂舞”,将重心落于左腿,右腿去挑对方的腹部。
杜心武一招“青蛇摆尾”,两臂屈收胸前,护住腹部,又一招“老虎蹬山”,飞起右脚朝贺永恒踢来。
贺永恒一招“虎伏荒丘”,右脚赶紧后撤,身体后坐,重心落于右脚,同时两臂左右张开,按于身体两侧,迅速轻灵。
这两人一连斗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
宋世荣起初并没有把马贵放在眼里,他见马贵年轻,以为他作战经验不足,可打了二十多个回合,马贵不但没有力怯,反而愈战愈勇。宋世荣只见马贵身体极其瘦弱,没想到他体内蓄积如此大的力量,一时惊叹不已。
马贵见与宋世荣搏打多时也未取胜,又不知师父尹福究竟如何,不便久战,于是猛地出手去点对方的鬼门穴。
宋世荣一见有些吃惊,没想到马贵如此通晓点穴功夫,不由得后退几步。
就在这时,他发现房上不知何时立着三个大汉,他们一动不动,就像三个凶神。看来今晚吉安堂凶多吉少。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暗暗捏了一把汗。
那三个人立在房上,已观看宋世荣、马贵、贺永恒、杜心武作战多时,就像看热闹一般袖手旁观。
宋世荣想探探房上三位壮士的虚实,手一扬,一个乾坤圈飞了出去。这乾坤圈大小约半尺,厚度如一枚钱币,圈里外全部开刃。宋世荣的乾坤圈一发,劲力强厚,呼呼生风。只见房上中间那位壮士不慌不忙,伸出手掌,轻轻一旋,便把乾坤圈削到一边。
宋世荣见了,暗暗吃惊,心想:这壮士功夫不可小瞧。如若没有功力,我这乾坤圈一抛,会齐齐削掉三个人的脑袋,没想到他却轻轻削到一边,真是神奇。
房上中间那个壮士用洪钟般的声音问:“车毅斋在哪里?”
宋世荣回答:“远游去了。”
“不对,他就在这里!”壮士坚定地说,好像没有人能说服他。
“请问你是何人?”宋世荣问。
此时,马贵也停止了进攻,贺永恒和杜心武也收了势,只望着房上出现的三个人。
“我是张策。”房上那汉子平静地说。
“噢,原来是通臂门到了!”宋世荣惊喜地说。
张策责问道:“比武为何还不开始?害得我们等了多时。”
宋世荣支吾道:“车老先生……不知到哪里去了,郭云深……至今未到……”
“不对!”张策纠正道,“车毅斋就在家中,郭云深也已到了太谷!”
却说尹福去追乔摘星,翻过院墙,拐进小巷,追来追去,追到一座妓楼前,乔摘星一闪就没了踪影。
尹福想:乔摘星可能一直藏身这座妓楼里。
他见楼内烛火辉煌,门口有个牌子,上写“沉香楼”三个字,两旁有一副对联,写道:“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门口高挑一个大红灯笼,金黄穗子飘来荡去。
尹福正在门口徘徊,这时,两个恶奴拥着鸨娘走了出来。
鸨娘道:“你这个瘦老头,不进来热闹热闹吗?”
尹福心里涌起一股厌恶,抽身走开。
他悄悄绕到妓楼后面,正见乔摘星往墙外爬,他一把揪住乔摘星,喝道:“我看你往哪里逃?!”
乔摘星一见是尹福,慌得浑身哆嗦,叫道:“尹爷,对不住了。”
尹福一把拽下乔摘星,问道:“皇上的玉玺呢?”
乔摘星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用右手乱晃,他右手上包着一块白布,血从里面渗出来。
尹福摸他怀里,没有那个小盒子。
“那小盒子呢?”尹福着急地问。
“丢了。”乔摘星回答,两只贼眼仍在打着转。
“玉玺和香汗巾呢?”尹福又急急地问,汗珠子淌了下来。
“汗巾让我揩腚了,玉玺刚才丢了……”乔摘星说着,身子一歪,没了气息。
尹福大惊,急忙仔细端详。只见他手上全是鲜血,原来乔摘星的后背中了一枚铁鸳鸯,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裳。
尹福抬头一看,只见妓楼的二层楼有个窗户开了,可是没有人迹。
一定是有人暗杀了乔摘星。想到这里,他放下乔摘星,跃过高墙,顺着一棵枣树,攀到二楼那个窗前,原来是走廊。但听一个个屋内传出****,走廊上空无一人。尹福不好一屋屋搜查,只好扫兴而归。
尹福回到教堂的铁栅前,忽见教堂的小洋楼内烛火昏暗,他以为马贵已回到教堂,心中感到一阵安慰。
尹福轻轻攀过铁栅,穿过硕大的梧桐叶,忽见洋楼窗前晃动着一个西洋女人的身影,飞飘飘的长发,雍容潇洒的拖地西裙,袅娜的身材,多么熟悉的身影……
是黛娜,那个瓦德西统帅派来的女杀手,那个狡黠的洋女人。
尹福的心跳着,血液沸腾着,他恨透了这个女人,他要杀掉她!
黛娜好像正喝着什么,有些如饥似渴的样子。
尹福迅疾来到窗前,黛娜却不见了。一会儿,烛也熄了。
尹福冲进门,大声喝道:“你这个洋女人,我看你往哪里逃?!”
没有任何动静,他只闻到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儿。
他见教堂洋楼的后窗敞开着,来到窗口,可溶溶月下,树影婆娑,却没有人迹。他设法点燃了蜡烛,发现地上有烟灰,面包被人吃了一些。
他打开浴室的门,看到池内湿漉漉的,有女人的胭脂味儿。
他又查看了附近几个房间,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迹象。
这时门“哐啷”一声开了,马贵闯了进来。
马贵的突然出现,把尹福吓了一跳,他迅速抽出判官笔,当定睛看清是马贵,才长嘘了一口气。
“师父,发生了什么事?你脸色不好。”马贵关切地问。
“真是见鬼了!”尹福放松地坐到沙发上,把见到黛娜的情形叙了一遍。
“这个黛娜是什么人?”马贵问。
“她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助手,是瓦德西派来刺杀皇族的杀手,一路上一直跟着我们。在忻州附近,我们抓到了她,可是后来让她溜了。”
“这个黛娜来太谷干什么?”
尹福双目炯炯,紧锁着眉头,说:“我也在想,她远离皇家行列,跑到太谷来做什么?这里面定有文章。”
“你没有看错吗?”马贵问。
“我虽然已有六十岁,但眼不瞎不花,耳不聋不斜,没有错,肯定是黛娜。”尹福充满了自信,肯定地说。
马贵把刚才在吉安堂发生的激战叙了一回。
尹福吃惊地说:“这个张策也到了太谷,各门派的人几乎都齐了。他和他的两个徒弟一路上跟踪我们,后来在恒山脚下一家酒楼上,遭一个叫岚松的女贼暗算,喝了蒙汗药,人事不省,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
马贵问:“各个屋你都看了吗?”
尹福回答:“看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现象。”
马贵不放心,自己到各个房间巡看。
尹福肚子有些饿了,于是抓起一片面包嚼着。
“师父,你快来看!”西边传出马贵的叫声。
尹福赶紧来到马贵发出声音的房间,这是主教的卧房。
高台上,一盆素雅的兰草,一盆秀气的文竹;五斗橱的顶板上摆了座维纳斯的石膏像;一张大的沙发床,床头柜的花瓶里插着几株野玫瑰。有一个立地的古瓶,足有三尺高,斜插着几尺高的孔雀尾翎。床旁有一个大理石面的小方桌,方桌上有厚厚一摞《圣经》。窗前半挂着绛红色锦缎帐子,墙是淡淡的黄褐色,稍微带点儿粉红色。床罩绿得刺眼。中央有个铺着桃心形坐垫的大安乐椅,白得能照出人影。
马贵举着一根蜡烛,凝神望着主教的油画像。画像足有四尺高,画中主教的头发十分显眼,带着火红的颜色。颊须有些长,像火红的羊毛似的,在耳边卷做一团。他苍老然而有力的眼睛,泛出蓝幽幽的光泽;高挺的鹰钩鼻子,纤细而白皙;颧骨又高又宽;穿着火红的袍子,胸前挂着一个银镀的十字架。
“马贵,你发现了什么?”尹福来到马贵面前。
“师父,你仔细看。”马贵俯下身,用手指着紫色的地毯。
尹福仔细一看,油画前的地毯上有一片湿迹。
“这是泪水。”马贵肯定地说。
“这么说,黛娜刚才曾来到主教像前,她流了泪,莫非她与主教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尹福暗暗寻思。
“这个主教叫什么名字?”尹福仔细端详着主教的画像,问马贵。
“布朗,美国人。”马贵回答。
尹福在京城见过许多洋人,他们在参拜皇帝时,有的拘谨,有的傲慢,有的谄笑,有的典雅。但是他还没有见过类似画上这个洋人的模样,他的脸上充满了征服欲,布满了杀机,是如此狰狞、凶恶、不可一世。
“他怎么没有被义和团杀死?”尹福松了一口气,气浪吹得蜡烛晃动着。
“义和团没有找到他,他逃走了,这只老狐狸。”马贵的话语中有几分遗憾。
师徒二人重又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尹福对马贵讲了沉香楼发生的事情。
马贵说:“乔摘星很明显是在妓楼上被人杀的,玉玺或许就在那个人手里,他是杀人灭口。白天不便行动,明晚我再去探吉安堂,你去沉香楼打听玉玺的下落。”
尹福忽然说:“马贵,你听,地下好像有‘嚓嚓’的声音。”
马贵仔细一听,说:“好像不在咱们待的地方的地下,是在远处。”
尹福伏在地毯上,把耳朵贴在地上,仔细谛听,然后爬起身来,说:“不是这地下,离咱们这里应该有一段距离。”
“不会是谁家挖菜窖吧?”尹福像是问马贵,又像是自言自语。
“师父,时候不早了,咱们先睡觉吧,一切明天再说了。”马贵说着滚到沙发上,一会儿便轻轻打起鼾声。
尹福将两个短沙发并到一起,也蜷缩着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照得窗帘刺眼,师徒二人才醒来。
吃过饭,尹福在屋里待不住,还是想到街上转转,马贵见劝不住他,只好陪他来到街上。
他二人正在街上走着,尹福觉得有人扯他的衣角。回头一看,却是那家客店的店主。
店主嚷道:“客官,你刚住了一天,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一拍屁股走了,快拿一天的店钱来!”
尹福连忙赔着笑,说:“对不住,对不住,只因一时追人,忘记了。”说着朝怀里一摸,身上已无分文,银两不知何时遗落。
他有些不好意思,对店主说:“银两嘛,到时一定还你,我忘记带了。”
马贵见师父犯难,赶忙去摸兜内,可是他也没有带银子。
就在此时,尹福猛觉背后风响,顺手一接,是枚铜钱;又听风响,又一接,又是一枚铜钱……一连接了一大捧,尹福感到纳闷,抬头一看,是旁边一家酒楼上扔下来的。
“你这手里不是有钱吗?”店主睁大了眼睛问。
“这,这不是我的呀!”尹福不知所措地说。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快还我钱吧。”店主的眼里露出贪婪的目光。
尹福把手里的一半铜钱塞到店主的手里,然后对马贵说:“走,我请你喝酒,这些钱足够了。”
二人进了路旁那家酒楼,店主把他们带到二楼。二楼非常清静,只有五六个人。尹福和马贵在靠近窗户的座位坐下。店主端来两瓶汾酒、一盘牛肉、一盘阳春豆,两个人对酌起来。
尹福是个细心人,他一边喝一边在寻找方才掷铜钱的人。他们的左面是两个中年汉子,已经喝得醉乏;后面有一个老妇,一边饮酒,一边自言自语。前头有两个和尚,一老一少,不喝酒也不吃肉,桌上摆着五盘花生米,花生皮散了一桌一地,可能是借这个地方叙话。
这时,他看见二楼西北角有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穿一件土黄布主腰儿,套一件青哦噔绸马褂子,褡包系在马褂子上头,挽着粗壮的辫子,背上斜背一口宝剑。
尹福见这后生背影熟悉,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