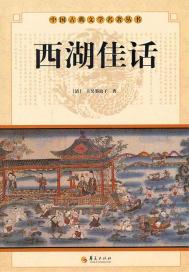狼狗高桥歪斜着身子依在竹凉椅上吃刨冰,铁勺把搪瓷茶缸里的刨冰屑搅得沙沙响。两个日本兵没吃他们电线杆似的立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对着弟兄们的胸脯子。高桥瘦弱的身子完全浸在高墙投下来的一片阴影中,他脸上、脖子上没有一丝汗。两个日本兵也站在阴影的边缘,只有头顶微微晒了些太阳。
是中午一点多钟的光景,太阳正毒。
六号大屋的弟兄全在火毒的太阳下罚站,仿佛一群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黑鬼。他们回到阎王堂,连脸也没捞着洗,就被高桥太君瞄上了。
高桥太君不相信张麻子死于煤顶的冒落,认定这其中必有阴谋。
在高桥太君的眼里,这个被高墙电网围住的世界里充满了阴谋,每个战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带有某种阴谋的意味。而他的责任,就是通过皮鞭、刺刀、狼狗等等一切暴力手段,把这些阴谋撕碎、捅穿、消灭!
张麻子昨日向他告密,今日就被砸死了,这不是阴谋还会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告密者是张麻子呢?谁告诉他们的?他要找到这个人,除掉这个人,他怀疑战俘中有一个严密的地下组织,而且在和外面的游击队联系,随时有可能进行一场反抗帝国皇军的暴动。
这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四月里,西严炭矿的**库炸了,战俘中间便传开了一些有关游击队的神奇故事,一些战俘变得不那么听话了。这迫使他不得不当众处决一个狂妄的家伙。那家伙临死前还狂呼:“你们这些日本强盗迟早得完蛋!乔锦程、何化岩的游击队饶不了你们!”他们竟知道矿区周围有游击队,竟能叫出乔锦程和何化岩的名字!这都是谁告诉他们的?!
吃完了刨冰,身子依在凉椅上换了个姿势,阴阴的脸孔正对着那群全身乌黑,衣衫褴褛的阴谋家们,高桥太君脸上的皮肉抽动了一下,极轻松地规劝道:
“说嘛!唼?统统地说出来,我的,大皇军的既往不咎!说出来,你们的,通通回去睡觉!”
没人应。
站立在暴烈阳光下的仿佛不是一个个有生命的人,而是一根根被大火烧焦了的黑木桩。
高桥太君从凉椅上欠起了身子,按着凉椅的扶手,定定地盯着众人看。看了一会儿,慢慢站了起来,驼着背,抄着手,向阳光下走。
他在王绍恒排长面前站住了:
“你的,你的说,张麻子的不是被冒顶砸死的,是有人害他,嗯?是不是?你的,大胆说!”
王绍恒垂着脑袋,两眼盯着自己的脚背,喃喃道:
“太君,我的不知道!窝子里出事时,我的不在现场,跟班矿警可以作证!”
“你的,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吗?你的不知道有谁向你们通风报信吗?唼?”
王绍恒艰难地摇了摇头:
“我的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太君明白。井下冒顶,经常发生。昨夜,是张麻子放顶,想必是他自己不小心……”
“八格呀噜!”
高桥太君一声怪叫,一拳打到王绍恒的脸上,王绍恒身子晃了晃,栽倒在地上,鼻孔里出了血。
高桥两只拳头在空中挥舞着,一阵歇斯底里的咆哮:
“你们的阴谋,我的通通的明白,你们的不说,我的晒死你们!饿死你们!困死你们!”
高桥太君又回到凉椅上躺下了。
一场意志力的较量开始了。高桥太君要用胜利者的意志粉碎战俘们的阴谋。战俘们则要用他们集体的顽强挫败高桥的妄想。
战争在他们中间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着。
他们作了战俘却依然没有退出战争。
刘子平排长希望这一切早些结束。
当高桥走到王绍恒面前,逼问王绍恒时,他的心骤然发出一阵狂乱的跳荡。他忘记了悬在头上火炉般的太阳,忘记了身边众多弟兄的存在。他觉着自己是俯在一间密室的门口,窃听着一场有关自己生死存亡问题的密谈。王绍恒站在孟新泽后面,距他只有不到一大步。他斜着眼睛能瞥到王绍恒半边脸膛上的汗珠,能看到王绍恒小山一样的鼻梁,他甚至能听到王绍恒狗一样可怜的喘息。高桥的脚步声在王绍恒身边停下时,他侧过脸,偷偷地去瞧高桥脚下乌亮的皮靴,他希望这皮靴突然飞起,一脚将王绍恒踢倒,然后,再唤过凶恶的狼狗,那么,今日的一切便结束了,他的一桩买卖就可以开张了。
他知道王绍恒的怯弱,断定王绍恒斗不过高桥太君和他的狼狗。他佩服高桥太君的眼力。高桥这王八别人不找,偏偏一下子就瞄上了王绍恒,便足以证明他窥测人心的独到本事。
他不恨王绍恒,一点也不恨。他和王绍恒没有冤隙,没有成见,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他甚至可怜他。他决不想借日本人的手来折磨一个怯弱无能的弟兄。当那个恶毒的念头突然出现在脑际的时候,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其实,按照他的心愿,他是极希望高桥太君好好教训一下田德胜的。田德胜那畜生不是玩意,依仗着力气和拳头经常欺辱他。可他很清楚,田德胜是个不怕死的硬汉子,高桥太君和他的狼狗无法粉碎他顽蛮的意志!高桥太君从那畜生嘴里掏不出一句实话!
突破口在王绍恒身上!
王绍恒应该把那个通风报信者讲出来!
他揣摸王绍恒是知道那个通风报信者的。王绍恒和孟新泽都是一九三团炮营的,素常关系很好,孟新泽的一些谋划和消息来源必然会多多少少暴露在王绍恒面前的,他只要把这个人供出来了,事情就好办了……
王绍恒竟不讲。
愚蠢的高桥竟用一个拳头结束了这场有希望的讯问。
王绍恒混账!
高桥更混账!
这一对混账的东西把本应该结束的事情又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了,他被迫继续站在这杀人的烈日下,进行这场徒劳无益的意志战。
身上那件沾满煤灰的破褂子已被汗水浸透了,黑糊糊的脸上,汗珠子雨似的流。汗珠流过的地方露出了白白的皮肉,像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沟。脚下干燥的土地湿了一片。头上暴虐的烈日继续烘烤着他可怜的身躯,仿佛要把他躯体内的所有水分全部榨干,使他变成一条又臭又硬的干咸鱼。那种生了黑虫的干咸鱼他们常吃,有时会连着吃一两个月呢。
够了!
他早就受够了!
他不愿做干咸鱼,也不愿吃干咸鱼!他要做一个人,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以人的权利,享受生活中应有尽有的一切。
咽了口唾沫。
身后“扑通”响了一声,闷闷的。
他判定,是一个弟兄栽倒了。
响起了皮鞭咆哮的声音。他大胆地扭头一看,栽倒的弟兄被皮鞭逼着摇摇晃晃立了起来。
那弟兄没有开口的意思。
看来,高桥太君今日要输。高桥太君知道有阴谋,却不知道阴谋藏在哪里。他为高桥太君惋惜,也为自己惋惜。
逃亡计划刘子平是知道的,他认定不能成功。在地面逃,有日本人的电网、机枪、狼狗。在井下逃,更属荒唐,竖井口,风并口,斜井口,日夜有矿警和日本人把守,连个耗子也甭想出去。说是有游击队,他更不相信。共产党乔锦程的游击队不会冒着覆灭的风险来营救国军战俘的——尽管国共合作了,他们也不会下这种本钱。何化岩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前来营救,也须打个问号。高桥不是一再说游击队全被消灭了么?!五月之后,不是再没听说过游击队的事情么?退一步讲,即使有游击队,有他们的配合,弟兄们也未必都通逃出去。倘或双方打起来,最吃亏的必是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弟兄!如果他吃了一颗流弹,送了命,这场逃亡的成功与否,便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世界对他刘子平来说,就是他自己。他活着,呼吸着,行动着,这个世界就存在着,他死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这是个极明确极简单的道理。
得知大逃亡的秘密,他心中就萌发了和日本人做一笔买卖的念头。他认为做这笔买卖担的风险,要比逃亡所担的风险小得多。他只要向日本人告发了这一重大秘密,日本人就会把他原有的自由还给他,他的生命就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升值。
这念头使他激动不已。
希望像一缕诱人的晨曦,飘荡在他眼前。
然而,他是谨慎的,他要做的是一笔大买卖,买卖成交,他能赚回宝贵的自由;买卖做砸了,他就要输掉身家性命。他不能急,他要把一切都搞清楚,把一切都想好了,在利箭上弦的一瞬间折断箭弓,这才能在日本人面前显出自己的价值。
张麻子竞走到了他前面,竞把耗子老祁告了。他感到震惊:原来,想和日本人做这笔人肉买卖的并不是他一个!他拿别人的性命做资本,别人也拿他的性命做资本哩!
张麻子该死。他参加了处死张麻子的行动。在田德胜砸死张麻子之前,他和两个弟兄死死压在张麻子身上。他用一双手捂着张麻子的嘴。他对张麻子没有一点怜悯之情,——事情很清楚,张麻子是他的竞争对手。
过后想想,却觉出了张麻子的可怜。张麻子是替他死的。如若他刘子平在张麻子前面先走了一步,那么,死在田德胜铁锨下的就该是他了。
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做这笔大买卖也和逃亡一样要担很大的风险哩!一时间,他打消了向日本人告密的念头。他不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自然,也不愿死在自己弟兄的铁锨下。
任何形式的死,对生命本身来说都是相同的。
他原以为日本人对张麻子的死不会过问,不料,日本人竟过问了。站到了烈日下,那死去了几个小时的告密念头又顽强的浮出了脑海,他希望日本人找到那个通风报信者,为他的买卖扫清障碍。
这个通风报信的家伙会是谁呢?矿警孙四?监工刘八?送饭的老高头?井口大勾老驼背?都像,又都不像。其实,送饭的老高头,井口的老驼背,与他都没有关系。他告密也不会去找他们。他要知道的,是矿警孙四和监工刘八是不是靠得住?他没有机会向日本人直接告密,却有机会向孙四和刘八告密。只要这两个人靠得住,他的买卖就能做成功……
脑袋被纷乱的念头搅得昏沉沉的。
这时,西严炭矿的汽笛吼了起来,吼声由小到大,持续了好长时间。炽热的空气在汽笛声中震颤着,身边的弟兄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太阳。太阳偏到了西方的天际上,是下午四点钟了。这不会错,西严炭矿的汽笛历来是准确的。西严炭矿的窑工们是八小时劳作制,每日的早晨八点,下午四点,深夜零点放三次响,这三次放响,唯有深夜零点的那次与他们有关。他们是十二小时劳作制,深夜零点和中午十二点是他们两班弟兄交接的时刻。
不错,是放四点响。
这就是说,他们在六月的烈日下曝晒了三四个钟头!这就是说,一场徒劳无益的意志战快要结束了,是的,看光景要结束了。
刘子平排长一厢情愿地想。
王绍恒斜长的身影被牢牢压在脚下的土地上动弹不得。四点钟的太阳依然像个脾气暴烈的老鳏夫,挥舞着用炽热的阳光织成的钢鞭在王绍恒和他的弟兄们头顶上啸旋。阳光开始发出嗡嗡吟吟的声响,王绍恒觉着自己挺不住了,脑门上一阵阵发凉,眼前朦朦胧胧升起旋转飞舞的金星。
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高桥躺在竹凉椅上吃第三茶缸刨冰,他干瘦而白皙的脸上依然没有一丝汗迹,几个日本兵将三八大盖斜挎在肩上,悠然自得地抽着烟。南面一至五号通屋里的弟兄已发出阵阵鼾声。
这一切强烈地刺激了他,他一次次想到:这不合理!这太不合理!他不该在这六月的烈日下罚站!出事的时候,他不在现场嘛!日本人不该这么不讲道理!他感到冤枉,感到委屈,真想好好哭一场。
高桥是条没有人性的狼,是个该千刀万剐的混蛋,如果有支枪,他不惜搭上一条性命,也要一枪把这混蛋崩了。
其实,他早就知道高桥不讲道理,早就知道这电网、高墙围住的世界里不存在什么道理,可他总还固执地按照高墙外那个自由世界的习惯思维方式进行思维,还固执地希望高墙外的道理能在这片狭小的天地里继续通行。狼狗高桥的思维方式和战俘营里的野蛮秩序,他都无法适应。他不断地和他们发生冲突,又不断地碰得头破血流,每当碰得头破血流时,他就变得像落入陷阱中的狼一样,绝望而烦躁,恨不得猛然扑向谁,痛痛快快咬上几口。
只有这疯狂的一瞬,他才是个男子汉。然而,这一瞬来得快,退得也快,往往没等他把疯狂的念头变成行动,涌上脑门的热血就化成了冰冷的水,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怯弱的娘儿们。
他时常为自己的怯弱感到羞惭,高桥站到他身边时,他怕得不行,两眼瞅着自己的脚背,不知咕咕噜噜说了些什么。仿佛鼻子下的那张嘴不是他自己的,仿佛他的大脑已丧失了指挥功能。高桥的拳头落到他脸上,把他打倒在地了,他才意识到:他并没讲什么对弟兄们不利的话,才感到一阵欣慰。
他不能出卖弟兄们,不能把逃亡的计划讲出来!他出卖了别人,也就等于出卖了自己!逃亡计划流产,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生命的希望,自由的希望是和那个逃亡计划连在一起的。
他却无法保证自己不讲出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到阳光下,已是三四个钟头了。这三四个钟头里,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他挺不住了!挺不住了!他两条干瘦的腿发木、发麻,青紫的嘴唇裂开了血口,体内的水分似乎已被太阳的热力蒸发干净。被高桥打倒在地时,他真不想再爬起了,他真希望就这样睡着,直到高墙外的战争结束……
恍惚之中,两团旋转的黄光扑到了他身边,两只从半空中伸下来的铁钳般的手抓住他肩头,抓住他胳膊,将他竖了起来,他听到了高桥野蛮无理的叫喊:
“晒死你们!饿死你们!困死你们!”
不!他不死!决不死!活着,是件美好的事!再艰难,再屈辱的活也比任何光荣的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活着,便拥有一个世界,拥有许多许多美好的希望和幻想,而死了,这一切便消失了。
他要活到战争结束的那天。
面前的金花越滚越多,像倾下了一天繁星,高墙、房屋和凉椅上的狼狗高桥都他妈腾云驾雾似的晃动起来。耳鸣加剧了,仿佛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同时飞动起来,嗡嗡嗜嘈的声音响成一片……
眼前骤然一黑,维系着生命和意志的绳索终于崩断了,他“扑通”一声,再一次栽倒在被阳光晒热了的地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扑来了两个日本兵。
他们试图把他重新竖起来。
却没有成功。
“抽!用鞭子抽!装死的不行!”
高桥吼。
两条贪婪噬血的黑蛇一次次扑到了他的脊背上,他不知道。昏迷,像一把结实可靠的大锁,锁住了他心中的一切秘密。
他挺住了。
后来,从昏睡中醒来,他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他竟熬过了这顿毒打,竟做了一回硬铮铮的男子汉。
他感动得哭了……
最终下令结束这场意志战的,是阎王堂最高长官龙泽寿大佐。
龙泽寿大佐是在王绍恒排长被拖到六号通屋台阶下的时候,出现在弟兄们面前的。他显然刚从外面的什么地方回来,刻板而威严的脸膛上挂着汗珠,皮靴上沾着一层浮土,军衣的后背被汗水浸透了,一只空荡荡的袖子随着他走动的身体,前后飘荡着。
他走到高桥面前时,高桥笔直地立起,靴跟响亮地一碰,向他鞠了一个躬。
他咕噜了一句鬼子话。
高桥咕噜了一串鬼子话。
孟新泽听不懂鬼子话,可能猜出高桥和龙泽寿在讲什么。他脑子突然浮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拼着自己吃一顿皮肉之苦,立即把面前的一切结束掉。
不能再这么拼下去了,再拼下去,他们的逃亡计划真有可能在烈日下晒得烟消云散!这僵持着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潜浮着可能爆发的危险。
他要向龙泽寿大佐喝一声:“够了!阴谋是莫须有的!逃亡是莫须有的,大佐,该让你的部下住手了!”
在整个阎王堂里,孟新泽只承认龙泽寿是真正的军人,龙泽寿不像管他们的高桥那么多疑、狡诈,又不像管七号到十二号的山本那么阴险、毒辣。龙泽寿喜欢用军人的方式处理问题。有一桩事情给孟新泽的印象极深:去年五月间,龙泽寿刚调到阎王堂时,有一次和孙连仲集团军某营营长章德龙谈高墙外的战争。谈到后来,双方都动了真情,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章德龙竟毫无顾忌地把龙泽寿和帝国皇军痛骂了一通。龙泽寿火了,冷冷抛过一把军刀,要和章德龙决斗。决斗就是在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进行的,弟兄们都扒着铁栅门向外看。章德龙是条汉子,军刀操在手里,马上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他挥着刀,扑向龙泽寿,头一刀就划破了龙泽寿的独臂,龙泽寿凶猛反扑,终于在一阵奋力的拼杀之后,将章德龙砍死。后来,龙泽寿在高墙内为章德龙举行了葬礼,他对着那些日本兵士,也对着站成一片的战俘们说了一通话:
“他不是俘虏!不是!他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死于战争!献身战争,是一切军人的最终归宿!”
龙泽寿大佐脱下帽子向章德龙营长的遗体鞠了躬。
那些日本士兵也鞠了躬。
孟新泽从那开始?认识了龙泽寿。他恨他,却又对他不无敬佩。龙泽寿敢于把军刀抛给章德龙,让章德龙重新投入战争,便足以说明他的胆识、勇气和军人气质!其实,他完全可以用高桥的手法,像掐死蚂蚁似的将章德龙掐死,他没有这样做。
高桥还在那里用鬼子话啰嗦。
龙泽寿的眉头皱了起来,极不耐烦地听。一边听,一边在高桥面前来回踱步,间或,也用鬼子话问两句什么。
后来,事情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没等孟新泽从人群中站出来,高桥绷着铁青的脸走到了弟兄们面前,很不情愿地喊道:
“通通的回去睡觉!以后,哪个再想逃跑,通通的枪毙!回去!回去睡觉!”
直到这时候,孟新泽才长长吐了口气,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放到了实处,他不无自豪地想:他和他的弟兄们又胜利了。
回到屋中,见到了耗子老祁。老祁血肉模糊的屁股已不能着铺了,他像条被打个半死的狗,屈腿趴在地铺的破席上,身上叮满了苍蝇。
孟新泽俯到老祁面前,老祁费力地昂起了脑袋,昂了一下,又沉沉地落下了。
老祁显然有话要说。
孟新泽嘱咐弟兄们看住大门,把耳朵凑到了老祁的嘴边:
“老祁,你要说啥?”
老祁低声问:
“和……和外面联系上了么?”
孟新泽摇了摇头。
“得……得抓紧联系!不能再……再拖下去了!咱们中间有鬼!”
孟新泽悄悄说:
“鬼抓到了,被弟兄们送到阴曹地府去了!”
“是谁?”
“张麻子!”
老祁点点头,又说:
“今日下窑,再派个弟兄到……到上巷看一下,我估摸那个露出的洞子能……能走通!我……我进去了,摸了几十米,感觉有风哩!”
“老祁,你吃苦了,弟兄们谢你了!”
老祁脸上的皮肉抽动了一下,说不上是笑还是哭:
“这些话都甭说了!没……没意思!”
这时,守在门口的弟兄大叫起来:
“饭来了!饭来了!弟兄们,吃饭了!”
老祁和孟新泽都住了口。
送饭的老高头将一筐头高粱面饼子和一铁桶剩菜汤提进了屋,弟兄们围成一团,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咬着铁硬的高粱饼子,喝着发酸的剩菜汤,弟兄们都在想着那条洞子……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洞子?它的准确位置在什么地方?它能把井下和地面沟通么?”
躺在地铺上的刘子平排长一遍又一遍问着自己。他凭着两年来在地层下得到的全部知识和经验,竭力想象着那洞子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洞子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耗子老祁已道出了一个秘密:洞口在上巷。然而,上巷有五六个支支叉叉的老洞子,究竟哪个洞口能通向自由?这是急待搞清的。另一个急待搞清的问题是:这条有风的洞子,是否真的通向地面?倘或它只是沟通了别的巷道,老祁的努力就毫无意义了……
兴奋和欣喜是不言而喻的,被囚禁着的生命在这突然挤进来的一线光明面前变得躁动不安了。他怎么也睡不着,睁着眼睛看灰蒙蒙的屋顶。
屋顶亮亮的。夏日的太阳把黄昏拉得很长,已是六点多钟的样子了,挂在西天的残阳还把失却了热力的光硬塞到这间青石砌就的长通屋里来。屋顶是一根根挤在一起的大圆木拼起来的,圆木上抹着洋灰、盖着瓦,整个屋子从里看,从外看,都像一个坚固的城堡。黄昏的阳光为这座城堡投入了一线生机,给刘子平排长带来了许多美好的联想。他想起了二十几年前做木材生意的父亲带他在长白山原始森林里看到的一个湿漉漉的早晨。做了俘虏,进了这间活棺材,那个早晨的景象他时常忆起。那日,他和父亲从伐木厂的木板屋中钻出来,整个大森林浸泡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突然间,太阳出来了,仿佛一只调皮的兔子,一下子跃到了半空中,银剑似的光芒透过参天大树间的缝隙,齐刷刷地照到了远方那一片密密麻麻、城墙般的树干上。他惊奇地叫了起来,仿佛第一次看到太阳!
那是永远属于他的自由的太阳!
升起那轮太阳的地方,如今叫满洲国了。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作为一个有血气的男子汉,他在国民**最高统帅部的指令下,在众多长官的指令下,也在自己良心的指令下,参加了这场由“满洲国”漫延到中国腹地的战争。随整个军团开赴台儿庄会战前线时,他从未想过会做俘虏,更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向日本人告密。在台儿庄会战中,他和他所在的队伍没打什么硬仗,但,台儿庄的大捷却极大地鼓舞了他,他认定他和他的民族必将赢得这场正义的战争。
然而,接踵而来的,是灾难的五月十九日。那日半夜,徐州西关大溃乱的情景,给了他永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日夜。一切都清楚了,可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日军业已完成对徐州的大包围。徐州外围的宿县、黄口、肖县全部失守。丰县方面的日军攻势猛烈。津浦、陇海东西南北四面铁路被日军切断。最高统帅部下令撤退……五十余万国军相继夺路突围,溃不成军,徐州陷入了空前混乱之中。堆积如山的弹药、粮秣在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中熊熊燃烧,火光映得大地如同白昼。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狂轰滥炸,一颗**落下,弟兄们倒下一片。突然而来的打击,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各部的建制全被打乱了,连找不到营,营找不到团,团找不到师。从深夜到拂晓,崩溃的国军组成了一片人的海洋,一股脑向城外涌……
他也随着人的海洋向城外涌。长官们找不到了,手下的弟兄们找不到了,他糊里糊涂出了城,糊里糊涂成了俘虏。
他被俘的地方在九里山。那是徐州城郊外的一个小地方,据说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和他同时被俘的,还有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一百余名弟兄。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是他的精神信念大崩溃的日子。从这一日开始,战争对他来讲已不存在什么实际意义了,求生的欲念将他从一个军人变成了一条狼。
他要活下去,活得好一些,就得做条狼。
五月十九日夜间,当那个和他一起奔逃了几个小时的大个子连长被飞起的弹片削掉半个脑袋时,他就突然悟到了点什么,他要做一条狼的念头,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萌发的。谁知道呢?反正他忘不了那个被削掉半个脑袋的苍白如纸的面孔。那时,他一下子明白了: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只能是他自己!他决不能去指望那个喧闹叫嚣的世界!那个被许多**词藻装饰起来的世界上,充满了生命的陷阱。
为了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管是做一条狼还是做一只狗,都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这是一条世人之间彼此心照不宣的密约和真理。
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一串固执的问号:
“那条洞子走得通么?它是不是通向一个早年采过的老井?老井有没有出口?”
是的,要迅速弄清楚,要好好想一想。告密并不是目的,告密只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最大值,如果不告密也能得到这个最大值,他是不愿去告密的!他并不是坏人,他决不愿有意害人,他只是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些东西。
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像潮水一样,渐渐退去了。漫长的黄昏被夜幕包裹起来,扔进了深渊。高墙电网上的长明灯和探照灯的灯光照了进来,屋子里依然不太黑。
他翻了个身,将脸转向了大门。
他看到了一个日本看守的高大背影。
这背影使他很不舒服,他又将身子平放在地铺上,呆呆地看圆木排成的屋顶。他还想寻到那个混漉漉的布满自由阳光的早晨。
却没寻到。
在靠墙角的两根圆木中间,他看到了一个圆圆的蜘蛛网,蜘蛛网上布满了灰,中间的一片软软地垂了下来,要坠破似的。挂落下来的部分,像个凸起的乌龟壳。他又很有兴致地寻找那只造成了这个乌龟壳的蜘蛛,寻了半天,也未寻着。
几乎失去希望的时候,却在蜘蛛网下面发现了那只蜘蛛,它吊在一根蛛丝上,一上一下的浮动着,仿佛在做什么游戏。
他脑子里突然飞出一个念头:
“蜘蛛是怎么干那事的?”
没来由地想起了女人,饥渴的心中燃起了一片暴烈的大火,许多女人的面孔像云一样在眼前涌,一种发泄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纷杂的念头……
他将手伸到了那个需要发泄的地方,整个身子陶醉在一片美妙的幻想之中。他仿佛不是睡在散发着霉臭味的破席上,而是睡在自家的老式木床上。那木床正发出有节奏的摇晃声,身下那个属于他的女人正呻**吟地哼着。
手上湿了一片。
没有人发现。
将手上沾乎乎的东西往洋灰地上抹的时候,他无意中看到,靠墙角的铺位上,两个挤在一起的身影在动。遮在他们身上的破毯子悄无声息地滑落到脚下,半个**的臀在黑暗中急速地移来移去。
他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他只当没看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睡着了。他在梦中看到了耗子老祁说的那个洞子,那个洞子是通向广阔原野的,他独自一人穿过漫长的洞子,走到了原野上,走到了自由的阳光下,他又看到了二十几年前长白山里的那个湿漉漉的早晨。
被尖厉的哨音唤醒的时候,他依然沉浸在幸福的梦境中,身边的项福广轻轻踢了他一脚,低声提醒了他一句:
“老刘,该你值日!”
他这才想起了:在出工之前,他得把尿桶倒掉。
他忙不迭地趿上鞋,走到了两墙角的尿桶边,和田德胜一人一头,提起了半人高的木尿桶。
倒完桶里的尿,田德胜照例先走了。
他到水池边刷尿桶。
就在他刷尿桶的时候,狼狗高桥踱着方步从北岗楼走了过来,仿佛鬼使神差似的,告密的念头又猛然浮了出来,他大声咳了一声。
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一串固执的问号:
“那条洞子走得通么?它是不是通向一个早年采过的老井?老井有没有出口?”
是的,要迅速弄清楚,要好好想一想。告密并不是目的,告密只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最大值,如果不告密也能得到这个最大值,他是不愿去告密的!他并不是坏人,他决不愿有意害人,他只是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些东西。
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像潮水一样,渐渐退去了。漫长的黄昏被夜幕包裹起来,扔进了深渊。高墙电网上的长明灯和探照灯的灯光照了进来,屋子里依然不太黑。
他翻了个身,将脸转向了大门。
他看到了一个日本看守的高大背影。
这背影使他很不舒服,他又将身子平放在地铺上,呆呆地看圆木排成的屋顶。他还想寻到那个混漉漉的布满自由阳光的早晨。
却没寻到。
在靠墙角的两根圆木中间,他看到了一个圆圆的蜘蛛网,蜘蛛网上布满了灰,中间的一片软软地垂了下来,要坠破似的。挂落下来的部分,像个凸起的乌龟壳。他又很有兴致地寻找那只造成了这个乌龟壳的蜘蛛,寻了半天,也未寻着。
几乎失去希望的时候,却在蜘蛛网下面发现了那只蜘蛛,它吊在一根蛛丝上,一上一下的浮动着,仿佛在做什么游戏。
他脑子里突然飞出一个念头:
“蜘蛛是怎么干那事的?”
没来由地想起了女人,饥渴的心中燃起了一片暴烈的大火,许多女人的面孔像云一样在眼前涌,一种发泄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纷杂的念头……
他将手伸到了那个需要发泄的地方,整个身子陶醉在一片美妙的幻想之中。他仿佛不是睡在散发着霉臭味的破席上,而是睡在自家的老式木床上,那木床正发出有节奏的摇晃声,身下那个属于他的女人正呻**吟地哼着。
手上湿了一片。
没有人发现。
将手上沾乎乎的东西往洋灰地上抹的时候,他无意中看到,靠墙角的铺位上,两个挤在一起的身影在动。遮在他们身上的破毯子悄无声息地滑落到脚下,半个**的臀在黑暗中急速地移来移去。
他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他只当没看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睡着了。他在梦中看到了耗子老祁说的那个洞子,那个洞子是通向广阔原野的,他独自一人穿过漫长的洞子,走到了原野上,走到了自由的阳光下,他又看到了二十几年前长白山里的那个湿漉漉的早晨。
被尖厉的哨音唤醒的时候,他依然沉浸在幸福的梦境中,身边的项福广轻轻踢了他一脚,低声提醒了他一句:
“老刘,该你值日!”
他这才想起了:在出工之前,他得把尿桶倒掉。
他忙不迭地趿上鞋,走到了两墙角的尿桶边,和田德胜一人一头,提起了半人高的木尿桶。
倒完桶里的尿,田德胜照例先走了。
他到水池边刷尿桶。
就在他刷尿桶的时候,狼狗高桥踱着方步从北岗楼走了过来,仿佛鬼使神差似的,告密的念头又猛然浮了出来,他大声咳了一声。
高桥在他身边站住了,定定地看他。
他几乎未加思索,便低声叫道:
“太君,高桥太君……”
正要说话时,三号的两个弟兄抬着尿桶远远过来了。他忙把要说的话咽到了肚里。
高桥产生了疑惑:
“嗯,你要说什么?”
那两个弟兄已经走近了。
没有退路了。他做出失手的样子,猛然将湿淋淋的尿桶摔到了高桥面前。
“八格呀噜!”
高桥一个耳光极利索地劈了过来。
显然,高桥已悟出了些什么,打完之后,又叫道:
“你的良心的坏了坏了的!我的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高桥将他带进了北岗楼。
一进北岗楼,他跪下了:
“太君,高桥太君!我的,我的有事情要向你报告!”
高桥笑了:
“明白!明白!你的说!说!”
他想了想,却不知该怎么说,一瞬间,他觉着很惶惑。他是怎么了?他原来并没想到要告密,怎么一下子竞主动找了高桥,他该讲些什么呢?那个洞子他是不能说的,那个洞子是属于别人,也是属于他的,别人的东西,他可以拿来送给日本人,他的东西,却是不能送给日本人的。他要说的,应该是与他无关的事——与他无关,而又能使他获得好处的事!一时间,这种事却又想不出来。说弟兄们要逃跑?怎么逃?有什么证据?
他无疑犯了一个聪明的错误。他一直寻求一种稳妥的告密方式,却忘了自己在逃亡的弟兄身上押下的赌注。
他有些后悔。
“嗯!你的说,快说!”
“太君!太君!他……他们……他们要逃!我知道,我听到了他们的议论。”
他含含糊糊地说。
高桥很高兴,搓着手,踱着步。
“说,说下去!”
“具体情况,我……我、我还没弄清楚,只是听他们议论过,说……说是要和外面的游击队联系,在……在通往井口工房的路上逃!”
他编了一个逃亡的方案。
“哦?谁在和游击队联系?”
“不……不……知道!”
高桥端着瘦削的下巴,想了一下:
“好!你的大大的好!你的回去,弄清楚,向我报告!嗯,明白?”
“明白!明白!太君!”
他站起来,正要向高桥鞠躬的时候,高桥一脚将他踢到了门外……
捂着被踢疼的肚子,站在出工的队伍中,他不再后悔了,他兴奋地想:今日这突然而来的机会,他利用得不错,他没暴露逃亡的真正秘密,为自己留下了一条退路,又向日本人讨了好,如果那条洞子走不通,他就甩开手做这笔大买卖。
院子中,月光很好。
高桥太君照例在月光下的高台阶上训话。
一切全和往常一样……
身陷囹圄,我却老是想着二十七年五月间徐州战场上的事,做梦也尽做这样的梦,有一次,在井下依着煤帮打了个盹,一个噩梦就跳出来了。我梦见日本飞机扔的**把我炸飞了,脑袋像红气球一样在空中呼噜噜地飘。我吓醒了……
人呀,落魄到那种地步,真没个人模样了。要说不怕,那是瞎话!要说没有点别的想法,那也是瞎话!那工夫,有的人真当不了自己的家哩!脑瓜要混蛋不知哪一会儿。日本人越是发狠,弟兄们就越想逃,可能不能逃出去,都挺犯嘀咕的。逃不成怎么办,半道送了命怎么办?命可只有一条哇!有人想告密,想讨好日本人,也是自然的。
这时候,弟兄们都听说了那条洞子的事,都一口咬定那洞子是通向地面的,那个洞子给弟兄们带来了多少热辣辣的希望哟,可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