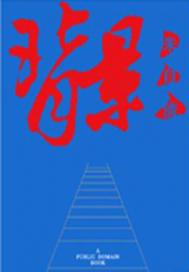中途在阿候家的一个小寨子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再起程时山势就逐渐平缓了。古旺元根据太阳方位,问阿候拉什这是不是向西昌方向靠近。阿候拉什说:“是的,原来我们在西昌西北,现在绕到西昌北面偏东了。离西昌有百多里路,如果不隔着罗洪家,就可以直接把你送到西昌去。这一带是暴动的武装没有来过的。”
话还没完,正前方有两人骑马飞奔而来。来人虽然也披着擦尔瓦,但看得出里边却是旧军服。阿候拉什眼尖,立刻叫人马停住,并特别嘱咐人给古旺元找件擦尔瓦披上,隐蔽到树丛后休息。他和阿芳两人迎着来人策马前进。
远远地看到两边四人都下了马。把马交给来人中之一,牵到一旁等候。阿候兄妹与其坐到树下,紧张地交谈。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两个来人骑上马顺原路跑回去了。阿候兄妹等他们走远,这才拉着马边说边走,慢慢走了回来。两人脸上都有些焦急与气恼。
回到队前,阿候集合人马严肃的讲话,阿芳把古旺元拉到一边说:“从现在起,你要换上彝装!”
古旺元问:“出了什么事吗?”
阿芳说:“我们被包围了,看样子要打一场恶战。”
事情来得突然,古旺元毫无准备,惊得话也说不出来。阿芳叫人给他拿来阿候拉什的一套旧衣,要他换上。换好衣服他才问道:“我们被谁包围?消息可靠吗?”
阿芳说:“来的那两个人是**救国军吴大头派来的,其中一个就是卖你的那个沙喉咙。他们的队伍就在我们左侧山后。”
古旺元说:“他们来打你们?”
阿芳说:“不,他们是来送信的。他们侦察到罗洪家的人正向我们家支打来。罗洪家是政府干部,跟他们誓不两立。进了我们地界就等于站到了他们**救国军的家门口。他问我们打不打?我们不打,他们就向我们借道,开过山去向罗洪开火;如果我们打,他们愿意作后盾。就是说我们不打,吴大头就要进来;我们打,就犯了政府不许打冤家的条例,而且打的是政府干部罗洪家。左右为难,我们给推到死夹道里了。”
古旺元问:“你们决定怎么办?”
阿芳说:“打!宁肯冒打冤家的罪名,也不要吴大头插手!”
古旺元望着阿芳的眼睛说:“也许还没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吧,罗赤中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能再派人去谈谈吗?”
阿芳说:“要是他哥哥带队,或许还可以谈判。若是他那个黑嫂嫂,就没有回转余地。他哥哥怕老婆,他是个软骨头!”
古旺元说:“如果是这样,我愿意替你们去说合。”
阿候拉什说:“到了前边看看情况再说。”
中午时分,阿候指指面前不太高的一座山说:“翻过这道山有个小寨子。这块地方是我报复罗洪家抢我的娃子,从他手夺过来的。不产粮食,就为了赌口气。我不在这里住,只有几家曲诺。他们也是投保了罗洪家一个小支头作名投主子,才敢住在这里放羊子。”
古旺元问什么叫名投主子?阿候告诉他,我的白彝住在这边放羊种地,怕罗洪家来打他,我离着远保护不到,他们就找附近罗洪家的小头人,给他银子,为他家种“节伙”,(为主人服劳役种的地)那一家便成为他的名投主子,保护他不受本家人杀掠。阿候并说:“这事是我首肯的。我说了并不想在此地捞钱,就为出一口气,名义上归我就行。”
走在前边的彝人停住了马,向后边摇手,大家又停下。从山坡上跑下一个人来。满头大汗来到阿候马前,结结巴巴地连说带比划。阿候兄妹听完脸色顿显紧张。没等古旺元问,阿候阿芳就对古旺元说:“什么民族政策、政府号召!什么要讲团结,求进步!再没人信你的鬼话。你们的人领着罗洪家打冤家来了!”
古旺元看她脸色气得煞白,知道是动了真气,满心狐疑却不敢再问,只把眼睛询问地望着阿候拉什。
阿候拉什脸色也很难看,但没说话,把头一摆,策马上山。
阿芳在古旺元身后,有点担心地望着他背影,一步不离左右。
来到山头,看到对面山上有人走动,执枪携炮,不下百余人。
阿候拉什作手势,要后边的人不要上山,留下几个瞭望哨。他领着众人退到山背后,在树木前下马,把刚才报信的彝人叫到跟前,从头仔细地盘问。
那人说,罗洪家的人昨晚到达山对面。他的名投主子叫他离开这里躲一躲,一两天内他们就要过山来抢占地盘,还说队伍里有十多个公家人。
阿候拉什对古旺元说:“我见过王队长,看样子是个诚实人,他怎么会言而无信!”便又问那人:“罗洪家是谁带队伍?”
那彝人说:“是罗洪英豪的老婆和罗赤中!”
阿候阿芳一听蓦的从地上跳了起来说:“你问清楚了?确实是罗赤中?”
那彝人说:“确实有罗赤中,听说他是和公家人在一起,他嫂子带队伍。”
阿候拉什自语说:“那么是他负责传递公家人的命令,黑玫瑰指挥打仗!”
阿候阿芳气恼地说:“我要把他杀了!”回头看见古旺元在用奇怪的眼神看她,就又加了一句:“把你也杀了,把他抓来两个一起杀。”
阿候拉什说:“你要杀就杀罗赤中。古先生是我的朋友,由不得你。我要留着他作个见证,证明这场冤家是谁打起来的!你倒要替我看好他,别叫他出意外。你杀罗赤中的时候我不拦阻就是!”
说完阿候拉什立刻把随从中几个得力的人叫来,一边斫下几根木棍,一边点火烧红一把刺刀,在木棍上烙出横竖交插的符号,挑出四匹快马,几个人跨上快马,连打几鞭,向四个不同方向飞奔而去。
这两人说的是彝语,古旺元一句也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