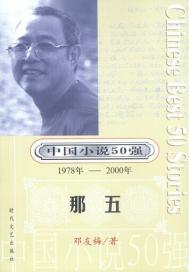芦花中学家属区一共有三个小院。最西北角的小院里住着四户人家。每家都是两间搭一个简单的小厨房。四间向阳的房里:左边住着林老师一家,右边住着团委书记张清家,靠左的边房里住着教务员郑明智一家,靠右的边房住着数学教研组长牛磊家。
四家四个女人,搭邻居已有几个年头。
人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屁股大的小院却住了四个女人,真真是,一台戏用不了,还有看戏的哩!
这四个女人还都有雅号呢!
林老师的夫人——尤萍香,大伙尊称“香油瓶”。
张书记的娘子——唐古露,人称“糖葫芦”。
郑明智的婆娘——常金秀,绰号“长舌头”。
牛老师的“娇妻”——五大三粗的马菊花,通称“马大炮”。
一开始住进这个小院时,四个女人中,就数着唐葫芦身价最高。她是城里人,下放农村后,又推荐去上了一年“五·七”大学。毕业后分配下来教外语,加之她又有个“精明强悍”的丈夫(在那乱世出英雄的年代里,他眼尖手快,小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毕业不管任课,就换了个书记干)据推算,完全中学的团委书记是科局级的干部哩!再配上农村稀少的外语教师糖葫芦那可真是锦上添花啦!
次之要数香油瓶,她在镇上供销社开化肥票,这是个特别吃香的玩艺儿,那些教书种田双管齐下的农村教师,哪个不围着她打转转哟,只要她点点头,赏个笑脸,总归是能落到些许好处的。
三等的公民就是长舌头和马大炮了。她们俩没有正式工作,都在学校办的家属药厂里刷瓶子。
四个女人一个小院,总免不了有些小磨擦,尤其有个马大炮在这儿,随时都有开火的可能。
女人眼皮浅,马大炮一看到香油瓶家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心里就不是滋味,“哼,香油瓶就是吃香,可实际上有什么能耐,不是男人有个当局长的表舅,还不照样在街上摆茶摊”。
这马大炮不光嘴里说,还时常摔摔打打的,有时还站在门前大声哼两声。大炮心里有,嘴里就搁不住,一放出来不要紧,长舌头就有事儿做了,她先跑到靠近自己的香油瓶家。
“喂,尤大姐,你还不知道呢!今天,那马大炮又骂了半晌,说谁谁谁又来拍你的马屁……”
香油瓶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她赶忙接过话茬说:“哦,小常,你搞错了,不会的,她怎么会骂我们的,她家的牛老师正要求加入组织,我家老林还是介绍人呢!老牛和小张有点那个,大炮说不定是冲着唐古露的哩!”
香油瓶话音刚落,长舌头恍然大悟:“哦,对、对对!也许是我听错了。”
长舌头的身影闪进糖葫芦的门缝,香油瓶撇了撇嘴角,“啪”地一声关上了门。
糖葫芦三十有五,城里人着意修整自己,虽然生了两个孩子,但丝毫不见衰老,甚至那丰满的额头还是十分光鲜发亮的。孩子都送进了城里,男人又被抽去县里搞外调,就一个人在家,每日里闲得无聊,只得把录音机放得大大的,屋里布置得也十分舒适宜人,各种高级奶糖,终日不断。加上一副天然的笑脸,搅得那些年轻的或单身的男同胞心里痒痒的,有事没事总是出一屋进一屋的,总归是精神加餐呗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不少人嘴嚼着可口的香糖,听着迷人的音乐,都一致称赞糖葫芦的温柔,娇顺,羡慕张清取上这位妻子,可真是搬座花暖房。糖葫芦看不上眼常金秀这样的女人,但生活中总是需要陪衬的,越是这样的女人多,越是显得糖葫芦高贵哩!
长舌头传来的信息恼坏了糖葫芦,嗬!连马大炮这样的贼女人也敢和自己挑事了,和张书记结婚以来,自己受过谁的委屈!她要找校领导告马大炮,她要找男人整马大炮,不能再叫这个女人做家属工了。这个可恶的女人,一定是眼红自己那铮光瓦亮的家具,眼红自己那落地式的录音机,嘿!癞蛤蟆也想和天鹅比翼飞!
马大炮受了男人一顿训斥,窝了一肚子火,在药厂里刷着瓶子就忍不住地咕噜起来了:“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我啥时候找过糖葫芦的事,糖葫芦也去告我。我也不想到她那个破葫芦里掏糖吃,我也不受这份气。”越说越气,火气攻心,一时大意,瓶子烂了,手被剐了个口子,正在一边刷瓶子的长舌头起忙掏出口袋里的手帕给大炮包扎,并连连叹气说:“忍了吧马大姐,省一事,少一事,唉,四家人,不就咱俩家不行吗?要不,咱们也不会住偏房!千不怪,万不怪,就怪咱俩的男人没本事。这年头男人当官,女人升天,男人上城,女人成龙,咱们的男人是狗熊,咱们只能刷瓶子”。
马大炮心里更窝火了,“住偏房咋样,心宽体胖,她们住正房,整天病讶讶的,她们是龙是什么龙!她们是虫,整天刷锅洗碗洗衣服倒尿盆都让男人干,自己搽呀,抹呀的,都甩掉男人,瞧谁能吃上饭!”大炮的声音高起来,顾不上伤口的疼痛,狠命地刷起了地板。
马大炮下班回家,想想长舌头的话,心里真够委屈。为什么男人一“走红”,女人就光彩了呢?大炮说什么也服不了这口气,这光彩不是自己挣来的,小秃跟着月亮走,有啥意思!大炮心里这么想,可是牛老师放学回来吃饭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地啰嗦起来。
“亏你还是本科毕业呢!有什么能耐,整天就会教书,也不替我想想,还能叫我刷一辈子瓶子?”马大炮的眼泪从来都是最金贵的,可在丈夫面前,今天却破天荒地掉了下来。
“瞧你,菊花,又想不开了,我教书,你刷瓶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不是好得很吗?”牛老师不紧不慢地说。
“刷瓶子,刷一辈子,也还是这么长,有什么长进,还能刷出个***来?”马大炮不耐烦了。
“菊花,你说得对,刷瓶子是不能刷出个***来,可你知道那***是哪一个人就放出来的吗?那必须有许许多多人配合工作才行!我教书,站在讲台上,可我也要吃饭,穿衣,没有人给我安排好这些,我能安心教书吗?再说,你不愿意刷瓶子,他也不愿意刷瓶子,可这瓶子到底得有人刷。”
牛老师到底是知识分子,几句话就把大炮给说闷了。晚间,牛老师为了安慰妻子,竟领着大炮到镇电影院去看电影去了。
马大炮一家生气拌嘴,小院准会都知道。因为大炮不会说悄悄话。这晚大炮的门刚落锁,小院里的脚步声一消失,三个女人不约而同的从门缝里伸出脑袋。
糖葫芦端出上海精制的奶糖,热情地招待两位女同胞。
还是长舌头嘴快,“你们瞧见了吧,老牛带着大炮去看电影啦,真稀罕!”
“她看懂个屁,今晚放的是《奇迹会发生》。那都是大作家大记者的私生活,她有那个欣赏能力吗?”糖葫芦吸着奶糖水,按下了录音键。小屋子里响起了轻快的音乐。
“嗬,你说她不懂,她还贬低你们呢?今天她在药厂刷瓶子时就说你们是寄生虫,能干什么,刷锅洗碗,倒尿盆都叫男人干?”常舌头连说带比划,唾沫迸了香油瓶一脸。香油瓶白了常舌头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是不做家务,我们当然没有她做得多,不过她干什么去呢!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只配干粗活的料!”
“是呀,她那‘高头大马’生成出苦力的模样,老牛和她不知怎么会有共同语言!”糖葫芦又朝嘴里放了一颗香糖。
“哼,你们没看到老牛这一阵也疼惜她啦,前天还给她买了一件好料子的上装,听说二十五元哩!”长舌头仿佛什么都知道。
“再好的料子到她身上该怎么样,牛屎包到鲜花里也还是牛屎”糖葫芦拽了拽自己合身笔挺的西装。
“那可不是吗?要有你们俩这样的身材,她马大炮更‘盛’哩!”长舌头甜甜地咂了咂嘴。长舌头话音刚落,糖葫芦得意地翘起了二郎腿。
“谈这些干什么。美不美主要在心里!”香油瓶不满地瞥了长舌头一眼,按了按自己肥厚的肚皮,那腰围早已超过裤长了。
小院里的人照常生活着。香油瓶糖葫芦照常上班下班,马大炮,长舌头还是刷瓶子。
生活就像平静的湖面,一粒小石子也会激起一圈涟漪。有一天,糖葫芦的男人回来了,糖葫芦出出进进,满面春风,原来男人调进城里工作,糖葫芦也要跟着进城了。幸运的人儿总是爱交好运的,糖葫芦的身价也随着男人的地位而提高了。临走的那天,小屋几乎挤炸了,男女同胞,恭喜寒暄,拍照话别,好不热火,直喜得糖葫芦满面红光,直忙得糖葫芦汗流浃背。男同胞们留恋她的温柔,女同胞们留恋她的糖甜。可马大炮却溜进药厂刷了一整天的瓶子。
晚上糖葫芦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正想和男人温存,香油瓶却悄悄地走进来了,不必说自然是一番亲热,亲热得异常,异常得少见。“唐小妹子,咱隔邻居多少年了,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你帮我,我帮你,胜过亲姐妹,你要调走了,咱俩再见面都不容易了。这些年大姐我有啥对不住你的,你就直说,我是个直肠子驴,从来不会使个小心眼。你走了,我也没啥给你,咱姐妹也是处一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话毕,从腋下拿出一个纸包,揭开外面的白纸,里面竟是一块上好的全毛料子。
这种事儿,糖葫芦不知干过多少次,如今,总算有了回头子,真是锯响就有末哇!男人,这时糖葫芦才真正理解了男人的价值……
晚上,劳累了一天的马大炮正想上床睡觉,牛老师训斥开了,“你真是不顾一点大局,小唐一家明天就搬走了,学校里老师都去送行,咱们好歹还住在一个院子里,你也该去坐坐,这是礼节呀!”
马大炮虽然是个粗人,可对男人的话总是听的,她觉得男人有知识,也有头脑,说的话也很在理,于是就换上了那件好料子的上装,理了理蓬乱的头发,又破天荒地搓了些发油,免得人家看不起。她刚到糖葫芦门口,听到里面有声音,就停下了脚步。她和糖葫芦有过磨擦,她怕人家讥笑她向糖葫芦“投降”,她刚立下,就听里面传出话语声。
“尤大姐,你的情我领了,可这么贵的东西我不拿钱怎么行呢?”
“瞧你说什么外话,咱姐妹俩还分什么你我,这是店里刚进的货,我一件,你一件,以后走远了,飞高了,莫忘了我就行了!”
马大炮明白了,是“香油瓶”给糖葫芦送礼,大炮立刻火气攻心了,“唉、女人,下贱货,难怪世上人瞧不起戴手巾的长头发!”
小院走了一家,只剩下三个女人了。
三个女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生活,上班,下班,刷瓶子。没有多久,林老师提拔为芦花中学的主任了,不用说,“香油瓶”比以前更香了,除去那些农村教师买化肥外,城里来的教师,那些双职工也上门了,排课的多少,轻重,检查作业的好坏,考勤记录……林主任的手里有许多好处哇!当今“枕头风”是人所共知的,最起作用。老师们心里都有数,只要过了“娘子关”,就算稳操胜券了。
不用说,长舌头不仅嘴勤,腿也更勤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谁能比她离香油瓶更近呢?
特别是近两天,她更忙了。听说学校要安排糖葫芦那两间向阳的房子,她施展开了全身的解数,可香油瓶却守口如瓶,不肯漏一滴香味。急得她抓耳挠腮,坐卧不安。自己的房子该换一下了,冬天西北风冻死人,夏天西晒太阳热死人。虽然马大炮跟自己住房条件相同,但自己总归比马大炮多长个心眼吧!
马大炮也听说了要安排“糖葫芦”的房子的事。
她也在心里打着算盘,“最好能安排来一家平头教师,老婆也是家属工,要不然就来一个有知识学问的女人,像她家老牛那样的。”
这两天大炮受凉了,身体格外不舒服,发烧,头疼,一天半都没去刷瓶子了。她躺在床上,心里直着急。小院里的人走光了。大人、孩子、上班的、上学的。没有人声,没有鸟鸣,很寂静。大炮撑着下了床,蹒跚来到门口,才发现天阴得很重,一会儿雷声隆隆,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就掉了下来,她突然发现香油瓶家门口晒着一大片蜂窝煤球。她来不及想什么了,只觉得邻居就得互相照应,她踉踉跄跄走出门,用灰搓子一趟一趟又一趟,一直搬完了那三百多快煤球,“香油瓶”家铁将军把门,她只好把煤球全搬进自家的屋中,大炮全身淋透了。雨越下越大,马大炮在床上哆嗦成了一团。
香油瓶冒雨跑回小院,发现煤球全搬光了。本以为是林主任回来收的,可是开门一看,屋里空空的,一时很纳闷。林主任也回来了。一问,才知道是马大炮帮的忙。香油瓶一时感到很惭愧。觉得马大炮虽然粗俗,可是心眼儿还是不错的。一天晚上,她悄悄地向林主任建议,“该给老牛调一下房子才对,他住的那两间房子光线太暗,再说他还是教研组的骨干,眼下还准备考讲师呢!将来说不定是条大鱼,知识分子吃香着咧。”
林主任笑了笑说:“不要你操心,领导早有考虑,只是没有正式宣布。”
路上说话,草棵里有人,两口子的议论被长舌头听了个精光。原来长舌头正准备去找香油瓶谈房子,恰巧到门口碰上了林家两口子在议论此事。长舌头像喝了一瓶子醋,什么?马大炮住向阳的房子,我常金秀住偏房!呸!叫你住!住!
马大炮的感冒还没有好,浇了这一场大雨更厉害了。她躺在床上,浑身火烧火燎地难受。可她生成的闲不住,还是坚持烧饭,做菜,她不忍心看老牛那笨手笨脚的样子,老牛正在研究高深的学问,她不能让老牛分心。
这天,马大炮正在吃药,长舌头来了,还顺手捎来了二斤红糖,这是马大炮开天辟地第一次受供,她哪有这份福气哟,这不是折磨人吗?她再三诅咒不要。长舌头不高兴了,“马大姐,你怎么这样怪呢?你几天不上班,我可急死了,你病着,我也不好受,小院几个女人,不就咱俩命苦吗?咱俩不一心,还给谁一心。你是个好心肠人,可如今兴不得好人哩,你冒雨收煤球,人家还说你是拍马屁哩!”
“什么?什么!”长舌头没说完,大炮蹦下了床,“这个臭油罐,我想拍马屁,我才不会像她那样给人送衣料,我想拍驴屁来,我求她个啥?”大炮血红着眼睛,坐在床沿上捶起了脑后勺。“唉!我也是个混人,事到临头,忘记了她是个当官的婆娘,早知这样,别说去收、就是看一眼,我都不是姓马的!”
香油瓶下班了。她走进小院,就想朝右拐,她想看看马大炮病轻些了没有,可她一抬头,正碰上大炮叉着腰,凶神一般地盯着她。
“天哪!这是咋啦?”香油瓶心中暗暗吃惊。
“拍马屁!呸,送布料的才是拍马屁!”马大炮又是吐,又是跺脚。
香油瓶脸儿红了,她知道大炮是在奚落她。
长舌头又来了,她劝香油瓶不要给马大炮一般见识,大炮是想住北房急骚了才发的火。香油瓶也恍然大悟了,难怪马大炮冒雨收煤球,原来施的是“苦肉计”。
不几天,长舌头家就搬进了糖葫芦的那两间向阳的房子里。
一切又归于平静了,小院还是原来的小院,人们一如既往地生活,三个女人还是上班,下班,刷瓶子。
有一天,长舌头也满面春风了,从来没有人光顾过的家里也开始喧闹起来。原来长舌头的男人郑明智也要“出口”了,他调到区委大院当文书。长舌头自然也随着丈夫的“出口”而光彩了。这年头,女人的身价总是随着丈夫的身价而增减的。长舌头,香油瓶,糖葫芦都是如此!因此,长舌头显得很坦然,她自豪地告诉人们,她不刷瓶子了,男人给她安排好了,到区委办公室看电话。长舌头显得很忙,她大声地给人们让坐。话音里掩饰不住春风得意,连额头上都显得光闪闪的。送走了客人,她就开始整理东西,明天上午就要搬出这个小院,她要去做区委大院里的人了。她想起了那电话机,哪头是说话的,哪头放耳朵上呢?真是!干吗想那么多,男人一定知道怎么使用电话机,反正有了男人就有了靠山。这时,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男人的价值。
收拾停当之后,她想香油瓶一定会来的。她左等右等,可是香油瓶没有来,一直也没有来,马大炮却来坐了一会儿,又走了。
一大早,老牛一家都在饭桌上吃饭,收音机里的乐曲刚停,播音员那甜美圆润的声音就响起来了。“下面摘要播送省教育厅通知……”
老牛屏心静气地听完了之后,高兴地打了个饱嗝,“哈,菊花,听到了吧,享受讲师待遇的五级教师可以解决家属、子女的户口和工作,这一下,你可以不去刷瓶子了。你为我付出的劳动还是有价值的吧!”
播出的内容,马大炮都听到了,她先是激动了一会儿,可是很快就平静了。她也会像长舌头那样随着丈夫的“出口”而不要刷瓶子了吧?她也会像糖葫芦那样跟男人屁股后头上城吗?不!她不,决不,她是马菊花,她身强力壮,五大三粗,她足有能耐自食其力,她享不得清福,享清福就丢去了理直气壮做人的权力,她必须首先做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女人也是人,不能是男人裤腰带上的小铃铛……
“菊花,愣想什么?你快解放了!”老牛快活得满面红光,轻轻地推了马菊花一把。
“不,我还是要刷瓶子,你看我这粗胳膊粗腿,闲的力气干啥去,”大炮朗声朗气地说,其实还咽下了一句话“靠男人大腿搓绳算不上一个好女人!”
长舌头要搬家了,正巧碰上糖葫芦从县里坐早班车来芦花中学统计五级教师名单,摸底排队。如今各行各业工作效率都高了,瞧,刚广播就行动起来了。出于礼节,香油瓶也来为长舌头送行。正好糖葫芦也到了,三个交了好运的女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说不完的神气话,笑声差一点冲飞了屋顶。
马大炮洗刷完毕,招呼老牛锁好门,她决定今天要比往常多刷二十只瓶子,并且不要报酬,力气是浮财,去了还会来!她甩了甩胳膊觉得力气大着呢!
三个女人从花格窗子里瞧见了马大炮招呼老牛锁门,就知道她马上要上班了。长舌头不知怎么竟生了恻隐之心,她不无惋惜地说:“这个女人有点差心眼,当初要不得罪咱们三人,如今你小唐在县上,我男人在区里,学校有尤大姐,说什么也给她找个合心的工作干!”
“老林说了,五级教师有安排,人家老牛拿的是响当当的本科毕业生工资哩”香油瓶像个东道主一样俨然地说。
“那可不是绝对的,我家小张在县里更清楚,这要酌情处理”。糖葫芦理壮气粗,此以前更有气派了。
“对哩,对哩,我家小郑今天早晨还给区委写报告,其中就有一句‘马列主义灵活运用’。”长舌头的话还没落音,糖葫芦的红唇嚼起来了,“嘘”。
原来是马大炮昂首挺胸地走过来了。
还是长舌头重情分,她甜甜地招呼道:
“马大姐,还去刷瓶子呀?”
“对,刷瓶子!”马大炮声音宏亮、吐字清楚,并且迈开了军人式的步伐,像斗胜了的公鸡,又像凯旋的勇士,咚咚咚地留下了一串响亮而有力的脚步声。
三个女人的兴致一下低落了,望着马大炮那远去的背影,她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