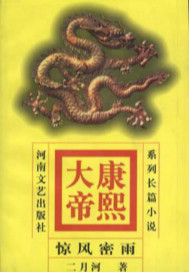军区还是那个军区,人还是那些人,一切似乎都没有变,一切似乎又都变了。
柳秋莎走在军区总院的一个角落里,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是当年的样子,只不过是人变了。院长很年轻,是当年的崔助理,柳秋莎当年一口一个小崔地喊着,如今的小崔已经是崔院长了,章梅也已经是副院长了。当年医院里那些老人都还记得柳秋莎,他们见了柳秋莎不知如何称呼,迟疑片刻,才热情地打招呼:老领导回来了!然后敬礼,握手。
柳秋莎走在医院的每一个科室里,情形大体都差不多。还有那些年轻的医生护士已经不认识她了,那些年轻人就问那些老人:这是谁呀?知道的便答:咱们的老副院长,柳秋莎。问的人便说:哦,是她呀。
柳秋莎被明确下来的职务是医院的顾问,她的办公室和崔院长的办公室是对门,门上就添了一块牌子,上面用红笔醒目地写着:顾问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摆设和崔院长办公室的摆设竟也分毫不差,有电话有沙发,还有两盆君子兰摆在窗台上。
她的门是打开的,崔院长办公室的门也是打开的。崔院长办公室里很忙乱,电话不断,来人不断,来的人大都是请示汇报工作的,然后送上呈文或报表,崔院长就在上面写上这样或那样的批示。崔院长最后总是关照那些人说:请柳顾问过一下目。
那些人便笑容满面地从崔院长办公室走过来,很谦逊地说:柳顾问,崔院长请你过目。说完,便把批件呈上去。
刚开始,她还认真地看那些批件,一页一页的,那样子比崔院长看得还仔细。来人就自然不耐烦的样子,在屋里踱了两步,后来索性坐在了招待客人的沙发上,点上支烟,轻轻淡淡地吸。柳秋莎闻到烟味,就下意识地拧紧眉头,来人注意到了,把吸了半截的烟掐掉了。
柳秋莎再去看崔院长的批示,崔院长的批示写得龙飞凤舞,她只能猜着认。按说,批件送到你这里了,按规定也是要写上自己意见的,这些柳秋莎懂,提起笔来,想了一会,又想了一会,就写了几个字:同意崔院长的意见。便把批件还给来的人,来的人便拿着批件走了。
渐渐地,柳秋莎对这种工作厌倦了,不就是看看批件嘛,她知道,看也是同意,不看也是同意,难道她还不同意崔院长的意见?时间长了,她就有了自己是个闲人的感觉。她这样的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既然这样,那还回来干什么?还不如她在靠山屯,每日出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在靠山屯的日子,她是踏实的,回到医院的日子她是个闲人。不行,绝不能过这种闲人的日子,她这么想过了,便锁上办公室的门,来到了军区胡参谋长办公室。
胡参谋长办事说话依旧,他正冲电话里喊:这事是军区党委定的,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你要是办不好,我就把你的师长撤了。
说完呱嗒一声放下电话。抬起头来,才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柳秋莎,他不认识似的看了一眼柳秋莎,然后才惊呼一声:小柳原来是你,快进来,快进来。
柳秋莎坐在招待客人的沙发上,胡参谋长一屁股也坐了过来,亮着嗓子说:你回来我还没去看你,你倒来看我了。
柳秋莎就公事公办地说:胡参谋长,我要工作。
胡一百就吃惊地问:你不是有工作了吗?
柳秋莎:就那个顾问?!
胡一百:小崔年轻,你要给他当好这个顾问,你是老同志了,你要帮助小崔。
柳秋莎又问:我的工作是谁定的?
胡一百就说:军区党委呀。
柳秋莎就又说:那要是我不当这个顾问呢?
胡一百终于明白柳秋莎来的目的了,便说:小柳哇,你年纪也不小了,党委考虑你离开岗位这么多年,让你担任顾问,先熟悉熟悉情况,以后再说。
柳秋莎心凉了,她知道自己工作的路快走到头了,自己哪儿还有以后,再以后就该退休了。想到这儿,她不说什么了,站起身来对胡一百说:看来组织是想让我吃闲饭了。
胡一百就说:小柳,你误会了,这是组织对你的关心。
柳秋莎就走了,顺着长长的楼道往前走着。
胡一百在后面喊:小柳,生活上有啥困难提出来,组织一定给你解决。
柳秋莎没有回头,一直走到军区办公楼外,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眼泪哗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她流泪、伤心,不是为了自己的得失,而是为了自己是个闲人,她为自己终于成了一个闲人而感到悲哀。
后来章梅找到了她,两个女人有了如下的对话。
章梅说:柳呀,我今年都快五十四了,到了五十五就该退休了,你呢,今年也有五十多了吧,再有几年就该退了,顾问就顾问吧。
柳秋莎就说:那以后我们就都吃闲饭了?
章梅说:这是客观规律,强求不得。
柳秋莎又说:那男人为啥能干到六十,我们咋就不能?
章梅道:这是国家的规定,国家有国家的道理,就是干到六十,最后不也得退休?话说回来了,谁让咱们是女人来着。
柳秋莎就说:下辈子说啥我也不再当女人了。
章梅笑了,她望着柳秋莎说:柳哇,你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从那以后,柳秋莎似乎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再有人来请示报告时,她不那么费劲巴拉地一页页地看了,而是在崔院长的批示下面写上:知道了。就算完成自己的工作了,后来,她连这三个字也不写了,她学会了画圈,于是,她就开始画圈了。
这样一来,大家都很满意的样子,来的人再也不用坐在沙发上等,或点支烟什么的了,而是匆匆地来,把批件往她前面一放,她很干脆、麻利地画了一个圈,写上一个柳字,工作就顺利地完成了。
来人就谦恭地对她点着头说:谢谢顾问。
她冲着远去的背影,显得一脸茫然和困惑。然后拍拍桌子,冲着窗外发呆。
邱云飞的境况和柳秋莎的处境大相径庭,他整天到晚忙得很。他现在已经是学院的一个负责人了,正领着一帮专家、老师,筹备恢复军队院校招生。学院已经十多年没有招生了,而是变成了轮训队,师资力量大批流失,一切都要从头再来。邱云飞是学院的老工作者了,于是,邱云飞便成了新一届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被任命为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
邱云飞已经不是以前的邱云飞了,整天从早到晚的忙。一大早,便有专车停在楼下,他一边嚼着饭,一边夹着包往外走。晚上回到家后,仍忙得很,一边看文件一边批示,还不停地打电话联系工作。
那一阵子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刚开始柳秋莎还赶忙地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都是找邱副院长的。从那以后,柳秋莎不再接电话了,而是一有电话铃响她便喊:邱云飞,邱副院长,电话——
邱云飞就急三火四地从书房里跑过来,冲电话里这样那样地指示一气说上一气,然后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还没忘了指示柳秋莎两句:以后有电话你就接,别大呼小叫的,这样不好。
说完便走回书房。柳秋莎来气了,她尾随着邱云飞走进了书房,指着邱云飞的鼻子说:你把话说清楚,我哪样不好了?
邱云飞就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没工夫和你磨牙。
说完便伏案继续看自己的文件去了。
柳秋莎一摔门,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赌着气道:就是当个破副院长吗,有啥了不起的?哼,看把你美的。
柳秋莎只能独自生闷气了。
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她刚想大声喊邱云飞,想了想又停下了,电话铃声在响,她干脆用手把耳朵堵上了,做出一副耳不听心不烦的样子。
邱云飞接完电话,看了她了一眼,哼一声走了。
没过两天,家里来了一个通讯班的战士,把家里的电话干脆扯进了邱云飞的书房里。
那些日子,柳秋莎的心空落得很,闲来愁肠瞌睡多。有时晚上,柳秋莎都睡醒一觉了,见身边的位置仍然空着,抬起头来,见书房的灯仍然亮着。她悄悄地起床,走到书房门口,看见邱云飞还在那里写写画画的,她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神,最后还是走了回来,躺在床上,望着黑夜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