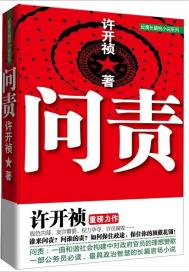一连两天,布达佩斯市像个失恋的少女样阴着面容,不时一阵濛濛细雨,淅淅沥沥,似烟似雾,如泣如诉。雨小而风轻,宛如天使般的清洁女士用抹布勤勉地将市区红绿相间的高大建筑物擦拭得异常洁净,在银灰的天幕下,绿得鲜亮而火得耀眼,辉映得这座极具欧洲风格的古老都市像个浓妆艳抹的老妪不乏妖媚风韵。
当曹仁义在华娜娜的陪同下走出布达佩斯这座教会办的医院,依恋地回头打量医院大门上端耸立的十字架,庆幸地双手合十:“阿门!”
华娜娜清楚曹仁义的心情。他这次遭人暗算,庆幸地是在他正向右面转身时子弹在其左肩胛处穿了进去。据医生讲,如果行凶者迟一秒钟开枪或者他转身的速度稍快一点,那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子弹将直接射进他的心脏,那么他将一动不动地在原地呜呼哀哉。他被送到这所教会医院后,医生没有任何的种族偏见,也没有考虑他经济上能否负担得起昂贵的手术费,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立刻给他做了开刀手术,将埋在肩胛处的子弹取了出来。从取出来的子弹头看,行凶者使用的是94式俄罗斯造袖珍****。这种手枪口径小,杀伤力不大。如果换了一些华人手中的其它任何一种手枪,那造成的伤害会大得多。而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慈悲为怀的上帝庇护的结果吗?华娜娜见状,以揶揄的口吻说:“仁义,你脖子上是不是刚挂了个十字架?”
曹仁义解嘲地一笑:“娜娜,你觉得我这次遭暗算是挺幸运的吧?”
华娜娜神色一沉,答:“我倒觉得,除了这家教会医院具有高尚的医德外,那就是行凶者手段的高超了。”
曹仁义听罢脸一白:“你是说那打我黑枪的家伙不想要我的命?”
华娜娜一点头:“是,但应该这样说才更确切,是他们此刻不愿惹出人命案来。”
曹仁义听后脸色由白变黄:“看来,这人是个超级杀手呀?!”
华娜娜又“嗯”一声,接着告之:“你没听说,在来匈牙利的中国人中,有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射击运动员吗?并且还拿过奖牌!”
“莫非打我的就是他?”曹仁义一脸惊讶。
华娜娜一摇头:“那我可说不准。”
华娜娜讲说不准,是指具体到哪一个人说不准,其实她心里已经料到,对曹仁义打黑枪的是周大海的人干的。
华娜娜的判断没有错。
这个对曹仁义打黑枪的不是别人,是被周大海唤做老四的那个光头小伙子。
老四出国前的确当过省里的射击运动员,并且在全国运动会上拿过名次。由于他生性鲁莽,在一次朋友与别人的斗殴中拔刀相助,结果误伤了人命。他感到杀人要偿命,自己将罪不可赦,便越境逃到了俄罗斯。他到了俄罗斯后,一没有学识,二不会经商,身上带的几个钱没多久就踢腾光了。就在他穷困潦倒时,遇到了周大海。周大海听说他曾是个射击运动员,会一手好枪法,日后用得着,便招致麾下,并拜了把兄弟。周大海年长他三岁,便成了大哥,从此他与周大海形影不离,成了名符其实的周大海的保镖与打手。前两天,周大海派**到“四虎市场”去教训曹仁义,又怕**莽撞而闹出人命来,立刻派他和老五去协助落实赵岩的意图,即对曹仁义只给他点颜色而对其他华商起到隔山震虎的作用就行了。当他和老五紧追慢赶地来到“四虎市场”,发现**正潜伏在购货的人群中要向曹仁义射击。他一看觉得大势不好,因为他知道**的枪法不准,要么会把曹仁义打死,要么就会误伤别人,便急中生智,掏出袖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打了曹仁义的左肩胛一枪,才防止**酿成大祸,同时也保全了曹仁义的性命。
曹仁义见华娜娜有些搪塞的样子,忧急地问道:“娜娜,你说这次对我行凶是不是周大海指使的?”
华娜娜见曹仁义面露惊慌,知道他内心里有点怕周大海。休看曹仁义为保护华娜娜口头上敢豁出去与周大海一决雌雄,并且在对旅游鞋统一限价的市场督察中也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其实他是属于胆小怕事的人。一次,毗邻华娜娜摊位的一名女华商无辜遭到市场保安人员的刁难,这名女华商不服,便据理力争,那个市场保安人员恼羞成怒,野蛮地对女华商拳打脚踢。华娜娜和目睹现状的华商们见自己的同胞受辱,对那个市场保安来了个群起而攻之。尽管那个市场保安人员手持电警棍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但见被激怒的华商们同仇敌忾,急忙用报话机报警求救。不多时,“四虎市场”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大批保安警察得到那个市场保安人员的报案后气势汹汹地赶来了。在这危急时刻,曹仁义吓得神色慌张地劝华娜娜赶紧收拾摊位躲开,免得遭到保安警察的逮捕。华娜娜瞪了曹仁义一眼:“怕什么?保安警察也得讲理!”事态的发展果然像华娜娜说的一样,虽然当时保安警察由于不明真相和语言障碍抓走了两名华商,但经过“华联会”和华商代表的抗议与交涉,保安警察便把两名华商放了回来,并公开向那个遭到市场保安人员欺辱的女华商道歉,“四虎市场”的老板为平息华商的愤怒还开除了那个保安人员。华娜娜通过这件事,看清了曹仁义性格上怯懦的严重缺陷。
“勇敢,不是男人的专利。懦弱的男人比女人还胆小。”华娜娜为此心里升发了感慨。
于是,华娜娜告诉曹仁义:“是不是周大海指使的,我还没有真凭实据。不过,你以后要处处谨慎些。但是,也不必由此就什么事情都缩手缩脚不敢做了。那些犯罪分子,就像蚍蜉,只能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他们是怕见阳光的。”
曹仁义知道华娜娜是在鼓励他,便点头表示听从。
这时,华娜娜的手机响了。
“喂,您好。”华娜娜将手机贴在耳畔。
“娜娜吗?我是杜仲坤,现在曹仁义的枪伤怎么样啦?”
华娜娜猜出杜仲坤打电话的目的不单是寻问曹仁义的身体状况,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忙答:“没事了,现在他已经出院了。还有什么事吗?”
“那曹仁义现在在哪里?”
“就在我身边。我们正要开车回家。”
“你能不能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就我一个人?”
“噢,要是曹仁义身体可以,你们两个一块儿来更好。”
“那好,我们俩马上就到。”华娜娜关上手机,紧走几步,打开一辆伏尔加轿车的后车门,招呼曹仁义,“上车吧。”
这辆半新不旧的伏尔加轿车是华娜娜前几天买的二手车,只合一万来元人民币。在匈牙利,买这种车是相当便宜的,而且布达佩斯大部分是这种价位的汽车。因为匈牙利人的经济收入不高,一般平民百姓月收入平均也就是二三百美元,所以绝大多数家庭买不起好车。
“杜仲坤这么急找你去有什么事?”曹仁义关切地问。
“具体什么事儿他没说。”华娜娜话语很淡。
“你想想,可能会是什么事儿呢?”曹仁义又说。
“你急什么,马上到了不就知道了!”华娜娜一边开着车,头也不回地说道,话出口很冷。
曹仁义像喝了顶头风,嗓子被噎着似的梗住了,把再想说的话闷了回去。
不大工夫,华娜娜和曹仁义来到杜仲坤的公司总部。
华娜娜一进杜仲坤的董事长办公室就觉得有一种临战的氛围。在杜仲坤的办公室里除了司马小媛,还有“华联会”派来的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华娜娜认识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华联会”的骨干力量,不仅热心于“华联会”的公益事业,而且还精明强干。特别是其中一个叫蒲昭合和一个叫严振东的人,更是身怀绝技,膂力过人。蒲昭合过去是相扑运动员,身大力沉,站起来俨若北京觉生寺内那口重达46.5吨的永乐大钟。这名叫严振东的,虽然身材不像蒲昭合那样魁梧,却从小习武,后得名师真传,刀枪棍棒无所不精,出拳踢腿碎石断柱,一般情况下,五六个人一齐动手休想伤他一根毫毛。他们到匈牙利来,完全是经商,但出于维护广大华商的利益,特别是在一些面临安危的事情上,他们两个总是自报奋勇,不计得失,颇具侠肝义胆。他们和杜仲坤都算行武出身,又似同出师门,彼此相当亲睦。论年龄,杜仲坤长他们几岁,因此他们对杜仲坤以大哥相称。
“老曹,伤口怎么样?”杜仲坤见曹仁义走进来,立刻关切地问道。
曹仁义感激地一笑:“受点小伤,已经没关系了。”
杜仲坤戏笑地看一眼华娜娜,对曹仁义说:“你这点小伤不要紧,可把我们娜娜累坏了,一连两天守候在你床边,瞧,眼圈都发乌了,说明为你担忧得睡不着觉。”
“董事长,您……”华娜娜话没说完已经腮落红霞。
杜仲坤向华娜娜一摆手:“娜娜,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而是告诉老曹,要记住感情是需要付出才能培育的。老曹,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对。”曹仁义用力一点头。
“好了,现在咱们言归正传。”杜仲坤叫大家都坐下,神色立刻凝固一般严峻,“先给你们通报一个情况,周大海回国以后已被当地司法部门拘留。至于为什么,有的同志知道,有的同志不知道,我再说一下,那就是他长期拖欠银行的巨额贷款,还有就是赖着不还几家公司和厂家的货款。”杜仲坤虽然来匈牙利已经好几年,但说话中常常不经意地使用“同志”等这种具有国内特色的字眼儿。
“他罪有应得。”华娜娜听罢愤恨地搭话。
杜仲坤发现,除了华娜娜和曹仁义一个是怒一个是惊以外,其他人的表情似水,居然连司马小媛都似乎觉得顺理成章,便立刻转人要说的主要话题:“刚才我说的只是个开场白,下面要讲主要话题了。”他说到这里,目光如雷达荧光屏扫描仪一样注视着大家的表情,话出口也凝重了许多,“根据‘华联会’的决定,将由我们去执行一项任务,去查封属于周大海的那个名叫匈牙利昆仑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货库!”
“什么?查封周大海的仓库?!”这愕然的惊诧,不是司马小媛的呼喊,而是她内心的震响。瞬时,杜仲坤的办公室内阒然无声,静溢得似乎地上掉根针都能振聋发職。
理解大家心思的杜仲坤明白,在座的之所以没有明确表示可否,是等候他讲这次查封周大海货库的合法依据。于是,他接着说道:“昨天,‘华联会’的武汀轩会长接到辽宁省沈阳市某法院发来的传真,委托‘华联会’查封周大海在布达佩斯的仓库。理由是向周大海贷款的那家银行和几个棉纺织品公司同时向法院起诉,告周大海拖欠公款不还。同时,这几个起诉周大海的棉纺织品公司联络几家周大海都有欠款的厂家,联名给‘华联会’也发来传真,讲周大海仓库的货物是国家的财产,不是周大海私人的,也委托‘华联会’进行查封。过后,他们再派人带上相关合同类的材料来对仓库里的货物进行处理。因此,武会长召集‘华联会’负责人开会研究决定,委托我和大家一起完成对周大海仓库的查封任务。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
华娜娜听了杜仲坤的介绍,虽然觉得对于查封周大海的库房的合法性没有什么置疑,但又觉得这种做法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匈牙利,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所在国的法律,便从国家的角度问道:“这事跟我们的大使馆说了吗?”
“已经以‘华联会’的名义给大使馆报告了。不仅如此,沈阳的那个法院也给大使馆发了传真。”
“大使馆也同意我们的这种做法?”
“对。”杜仲坤看着华娜娜,那特有的目光夸奖她成熟了,变得善于思考问题了。
这时,司马小媛却如坐针毡,心里很乱。她也认为查封周大海的仓库属天经地义,但她最大的恐惧是知道目前周大海仓库中的货物可能有她秘密存置在“苏联市场”北侧那两个被盗仓库里的服装鞋帽,而这些服装鞋帽恰恰又是杜仲坤从国内亲自定的货,一旦打开周大海的仓库,杜仲坤一看,岂不彻底暴露无疑?杜仲坤肯定要察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怎样回答呢?是一口咬定不知道,或者推说这些货物就是当初华娜娜当经销部经理时被盗的那两个仓库的东西?但对于人生经验很是丰富和目光异常锐利的杜仲坤骗得了初一骗得过十五吗?再说,当时她采取嫁祸于华娜娜的手段,不是还有几个她的亲信吗,谁又担保她这几个亲信就永远不会背叛她呢?比如其中的春子,虽然她是她的表妹,可杜仲坤对春子也不薄。有一回她试探性地问春子崇拜谁,春子开口便说崇拜杜仲坤。她问为什么,春子说杜仲坤酷毙了。她听了起初没明白“酷毙了”是什么意思,春子叫一声“哇塞”,说“酷毙了”就是冷峻刚毅,是“帅呆了”。她听罢佯装生气地要春子说“普通话”,对“帅呆了”她也听不懂,春子嘻嘻一乐,告诉她“帅呆了”就是英俊之极,帅气之极。你想,杜仲坤已经成了春子崇拜的偶像,他要是凭着在国内当兵时练就的做思想工作的经验找春子调查了解,怎么能担保春子不说出实情呢?为此,她越想越感到可怕。要做到不使这件不光彩的事情败露,惟一的办法是造成查封周大海仓库的行动流产。而这又能做得到吗?做不到就等于坐以待毙!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她与杜仲坤的爱情,总不能难以所为而不为呀!司马小媛在这种巨大利害关系的拉动下,便鼓足勇气说:“杜总,不知‘华联会’想到一个问题没有,周大海有个合伙人叫赵岩,周大海的仓库虽然不是赵岩的,但他们两个在对旅游鞋统一限价上却是狼狈为奸,赵岩找了个匈牙利女人,那女人的舅舅在匈牙利警察局工作,听说还是个什么头头。‘华联会’要查封周大海的仓库,赵岩会不会动员他匈牙利的妻子搬来她舅舅强行干涉呢?”
杜仲坤听了不由得一怔。是呀,司马小媛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仅“华联会”的武会长忽略了,自己也忽略了,并且参加“华联会”商讨要查封周大海仓库的“华联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忽略了。而这个被忽略的问题,又是在这次查封周大海仓库中极可能发生的。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去年,有个华商的货物被抢,这个被抢货物的华商,组织一些人到他认定是一个华商抢了他的货物的仓库去抢回属于他的货物,就遭到了布达佩斯市当地警察人员的干涉,反而把这个被人抢了货物的华商以抢劫罪拘留,后经“华联会”担保,关了七八天才被释放,并处以两千美元的罚金。当然,这次查封周大海的库房与那个货物被抢的华商情况有别,不能同日而语,但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也许会是惊人的相似。这一重要的环节,怎么大家都忽略了呢?多亏司马小媛提出来呀!女人思考问题就是心细。杜仲坤以赞赏的目光看着司马小媛:“谢谢你,你说的这个问题至关重妻,我们确实是忽略了。”他说着眉宇微蹙,显然是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
“董事长,是不是给‘华联会’的武会长通个电话,讲明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你们开会再商定一下,可否先摸清赵岩的举动,再做出查封周大海仓库的决定。”刻意观察杜仲坤神色变化的司马小媛立刻提出建议,目的是使用缓兵之计。对周大海仓库晚查封一天,他们的存货就可能多卖出去一些,尤其是旅游鞋他们天天大量批发,他们盗窃的“苏联市场”北侧的那两个仓库的旅游鞋就可能全部卖光。再说,那两个仓库的旅游鞋本来就数量不大。这样做虽然对于臾挽回国内的损失以及对旅游鞋统一限价不利,但在与自己须叟不可剥离的利害面前只能是将天平往自己这方倾斜了。
没想到,杜仲坤果断地说:“不必了。我们要是拖延一天,就可能为周大海的人赢得做手脚的机会。再说,周大海虽然在国内被拘留,但是根据他的能量和现在国内司法部门的特殊情况,很可能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这个周大海,可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呀!我们现在就立即行动,到时要是出现特殊情况,我们再做特殊处理!”
“我们既然意识到可能出现特殊情况,就应该认真研究对待,要是这样匆匆忙忙地去,会不会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呢?”司马小媛在说到“要是这样匆匆忙忙地去”的时候本来想使用“莽撞”的字眼儿,但又怕刺伤杜仲坤,所以使用了“匆匆忙忙”,但意思也表达出来了,语调也显得平和。这就显示了司马小媛的应变力和乖巧程度。
“时间就是胜利。延误战机就会导致失败。”杜仲坤军人风度不减,使用的语言也兵味儿十足。他蓦地站起来,犀利的眸子寒光如剑,话出口俨若战鼓:“除了老曹留下,所有的人都跟着我出发!”说完,拎起一个老板箱,拔脚出门。
华娜娜一听杜仲坤要把曹仁义留下,立刻给曹仁义使了个赶忙要求一起去的眼神儿。
曹仁义本来就不愿意去,听了杜仲坤不让他去的话就更心安理得的不想去了,但他看到华娜娜那带有愠怒的目光,不敢怠慢地急忙说:“杜董事长,我、我也去吧?”
杜仲坤闻听止住脚步,转身看着曹仁义:“你刚出院,伤口还没有痊愈,还是不要去了吧?我们这么多人去,足够了。”曹仁义听完杜仲坤的话,扭头见华娜娜冷鼻子冷脸,知道她对于自己的退缩已经生气了,一迭声地表示:“杜、杜董事长,我的伤口已经不、不碍事了,真的,您看,这不连绷带都拆了,还是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他几次说话带出口吃,足见他是出于华娜娜的胁迫。
“董事长,他坚决请求参加,就叫他去吧,多个人不就多份力量吗?媛媛大姐,您说是吧?”华娜娜不但在杜仲坤面前为曹仁义请缨,还对司马小媛使用了一个“大姐”的亲昵称呼,旨在求得司马小媛的援助。她主张叫曹仁义参加的目的,倒不是完全像她说的多个人多份力量,而是想以此锻炼一下曹仁义的胆魄,同时也使他养成关心他人和公益事业的美德。
司马小媛见华娜娜求到她了,在这种场合是不能显得无动于衷的,便顺口说:“董事长,曹先生想去,娜娜又想叫他去,你何必不……”
“好,”杜仲坤没等司马小媛说完,立刻拍板同意,“但是,老曹哇,咱有言再先,不管到时候,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不要冲锋在前,伤口要是犯了病可就更痛苦了。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曹仁义一伸脖子,这声回答很响亮。
周大海的仓库在布达佩斯第二区的榆树街。这里是居民区。街道既不如安德拉什大街气派漂亮,也不像瓦茨大街那样繁华喧闹,更没有城堡山下的主街古老典雅,显得极普通又极静谧。街道两旁虽然不乏停放着各种轿车,但极少看到行人,甚至在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之间也很少有汽车通过,使人怀疑这里是不是无人使用的搭建的影视拍摄景地。
上午十时正,杜仲坤一行来到周大海租赁的临街的库房前面的停车场上。
杜仲坤下得车来,身材魁梧的蒲昭合指给他一扇灰色的木门:“这就是周大海的仓库。”
“库房这么大!”杜仲坤一看不禁有些惊讶。
“里面可以放十来个货柜的货物。”卫士般站在杜仲坤另一侧的严振东说。
杜仲坤一挥手:“把封条贴上!”
“那大门上的锁呢?”蒲昭合走到灰色木门前,看了看木门上的铁锁,扭头问杜仲坤。
杜仲坤明白蒲昭合问话的意思,光贴封条不行,木门上的锁不换掉,周大海的人照样可以把仓库里的货物拉走。
杜仲坤回答:“我们不是带来了锁吗?再加上一把!”
“锁谁拿着哪?”蒲昭合话出口似山炮样响。
“我拿着哪!”华娜娜答。
“给我吧,我来锁。”严振东麻利快捷地从华娜娜手里拿过锁,走到木门前抬手就要锁。
这时,从严振东身后酷似拉响了一枚手**:“干什么的?!”
严振东和所有来的人蓦地听到一声喝斥,急忙转身一看,见周大海的十来个人一字排开地站着,脸上的表情除了嘲弄就是不以为然。其中叫得上名字来的有赵岩、**、老四、老五,还有被周大海唤做咪咪的卡拉菲莉亚,另外的几个壮男则平时没有见过。这些人从什么方向来的,怎么到的他们身后,杜仲坤他们一点都没有察觉。而且从他们的表情看,显然是已经得知杜仲坤就在这个时刻带人要查封周大海仓库的,所以他们显得从容不迫。
“哟,赵总,”杜仲坤暗暗吁了口气,神色坦然地走到赵岩近前,“我们来例行公事,你们几位——”
赵岩微微一笑:“我们也来例行公事。”
杜仲坤觉得赵岩很有城府,从他笑里藏刀的神态和含而不露的讥诮中可以看出非同等闲之辈。杜仲坤最讨厌这种笑面虎和阴阳怪气的人,所以直言相告:“我们代表‘华联会’,来查封周大海的货库。”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赵岩依然不动声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明人不做暗事。原因是,因为周大海被国内司法部门拘留,法院和他所欠款的几家公司及厂家委托‘华联会’对周大海的仓库实行封存,以追回一部分国家财产。”
“且不讲你们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如何,仅请教一个问题,你们怎么知道这就是周大海的仓库呢?”赵岩脸上依然笑靥不减。
“当然我们是经过调查弄明确的。”
“请问,谁调查的?又是哪一个弄明确的?”
“我!”蒲昭合冲前两步横在赵岩面前,那嗓音像撞响一口大钟。
赵岩抬眼见面前似戳着一堵墙,后退一步:“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蒲昭合。”
“噢,你就是像熊瞎子摔跤一样玩过相扑的蒲昭合?怪不得这么一身肉。请问,你是什么时候调查的?”赵岩的话语不像与杜仲坤说话时那样彬彬有礼,而是变得极为刻薄和尖损,目的是要把蒲昭合激怒。
“你先说话客气点!”蒲昭合果然吼开了,脑门上青筋直暴,“至于我什么时候调查到的,对于你更是无可奉告!”
“那我就可以说,你这种所谓的调查完全是弥天大谎和信口雌黄。”赵岩的话语依然辛辣嘲讽。
“你!你才是信口雌黄哪!”蒲昭合像头公牛似的眼珠子圆睁,脖子上的青筋似蚕样蠕动。从脖子到头顶宛如一块烧红的钢锭,他那蒲扇大的手掌几次欲抬,仿佛要给赵岩一个响亮的耳光。他怒冲冲几步来到灰色木门前,一拍门上的大锁,“姓赵的,你要有种,就打开仓库,看里面有没有在传真中说的一些品牌的货物?!”
“放下你那熊爪子,你要再敢动门上的锁,我们就对你不客气!”老四和老五见蒲昭合冲到仓库门前,如饿狼扑食般“呼”地跃到蒲昭合身旁,一左一右似铁钳般把他挟持在中间,那挽袖攥拳的架势,似乎一场拳脚大战即将爆发。
“你们两个退下!”赵岩沉着脸把老四和老五喝止住,使本来想以拳脚回击的蒲昭合孤零零地站在木门旁,像头拧着脖子想用利角奋力顶撞而却失去攻击对象的莽牛。
这就是赵岩优于杜仲坤之处。老四和老五唱白脸,他就立刻唱红脸,刚柔相济,进退有余。可是杜仲坤呢,蒲昭合被赵岩刺激得像只狂怒的猛狮,他心里也已是义愤填膺的,还怎么劝说蒲昭合要冷静呢?其实,无论是大千世界的演化还是芸芸众生的繁衍,无不是阴阳的交会。天与地,昼与夜,阴与晴,雄与雌,强与弱,不都是有机地排列组合吗?反之,两刚相并而易折,两柔相加而必弱。农村有句俗话,叫做一个槽里栓不住两条叫驴,就极通俗又极形象地道出了这一哲理。
“杜老板,还是我来请教您吧。您或许不会不知道,如果明目张胆地要封别人的仓库,那可是与明火执仗的抢劫是同等性质的问题。”赵岩说这番话时两个嘴角吊起,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在微笑莫如说是嘲弄。
血气方刚的杜仲坤早已被赵岩皮笑肉不笑的神态刺激得气撞脑门子,听了他的诘问,厉声回答:“赵老板,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承担法律责任,既然我们的话已经说到这一步,我们再在周大海库门上加把锁,你们不会挡横儿了吧?”他见赵岩嘴努动了一下没表态,立刻向蒲昭合和严振东一挥手,“把这个仓库锁上!”
“不许!”像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就在这个当口,卡拉菲莉亚大喊一声,跑到仓库大门前,双臂左右一横,用背靠在大门铁锁处,一反往常的麻木,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急扯白脸地喊道,“周老板不在,你们这是趁火打劫!”
这样一来,杜仲坤一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了。他过去曾听说周大海从俄罗斯带来的一个漂亮姑娘,在周大海面前像个木头人似的很少言语,更很少动容,今天却为了维护周大海的利益不仅声撕力竭,而且简直是要誓死捍卫了。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年轻而姣好的俄罗斯女人,她挡在门前,总不能叫蒲昭合和严振东两个大男人把她扯开吧?但不把她扯开,查封周大海仓库的任务就无法进行。怎么办?当他求助似的看华娜娜和司马小媛一眼,见华娜娜正虎着一双杏眼瞪着卡拉菲莉亚,心里顿时一亮,立刻一指卡拉菲莉亚:“娜娜,上前给我把她扯开!”
华娜娜早已憋了口恶气。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死心塌地地忍受周大海的作践。周大海是个什么好东西吗?一个恶狼样的性虐狂,一个穷凶极恶的骗子,一个枭匪般的抢劫犯!他本来是拿你当玩物,可你不但不趁他被国内的法院拘留的机会逃出他的魔爪,反而今天还充当他的帮凶,为他做挡箭牌。不知好歹的贱货!华娜娜心里骂完,便大喝一声:“你算干什么的?闪开!”
卡拉菲莉亚见华娜娜像个斗红了眼的母鸡一样扑将过来,她知道华娜娜与周大海的夫妻名分,吓得慌乱地喊道:“你,你要干什么?!”
“你说我要干什么?论名分,我与周大海还没有离婚,可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华娜娜气咻咻地指着卡拉菲莉亚的鼻子尖,“闪开!”
卡拉菲莉亚听了华娜娜的质问的确无言以对。是呀,自己算什么东西呢?说得好听一点是情妇,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在俄罗斯叫鸽子,与妓女没什么两样。她正感到为难时,忽然看到赵岩给她传递过来的特有眼神,立刻大喊:“来人哪,有人要抢劫我们的仓库啦!”
“□——□——!”卡拉菲莉亚报警般的喊声未落,四周顿时响起尖厉刺耳的警哨声,随之洪峰似的涌过来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一个个冒着瘆人寒光的乌黑枪口对准了杜仲坤、蒲昭合、严振东和华娜娜等人。在这些武装警察中,充当指挥官的是安丽娜的舅舅亚·隆·尤瑟夫。
这个尤瑟夫不像一般匈牙利男子那样人高马大,而是五短身材,身高充其量也就一米六八,加之大头颅大臀部大脚板,长与宽几乎失去比例。休看他又矮又胖,但却似《水浒传》中的王矮虎一样身手灵活。他雪球般滚到杜仲坤面前,肥硕的两腮上乌黑的胡茬子像两畦刚割过不久的韭菜地,一双豹眼怒目圆睁:“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胆敢抢劫?!”
杜仲坤明了这是赵岩设的圈套。他知道在匈牙利武装保安警察面前不能对抗,否则他们会立刻逮捕你,只能是说明情况,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于是,他递上自己的名片,微笑着解释:“正因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才不会胆敢抢劫。”他说完拿出“华联会”收到的国内法院和有关棉纺织品公司的委托书,以流利的匈牙利语详细说明查封周大海仓库的正当理由。
尤瑟夫听罢向赵岩掷过质问的目光,仿佛感到赵岩有“谎报军情”之意。
赵岩见状,脸上的温文尔雅不见了,代之是对杜仲坤的愤懑:“杜老板,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周大海的仓库,那好,当着保安警察的面儿,你说说里面都是些什么货物?”
杜仲坤又是一亮手上的传真件:“有什么货物,这上面写得一清二楚。”
“如果仓库里没有这些货物呢?”赵岩的目光突然变得似猛涮一般,凶恶阴毒。
杜仲坤顿时哑了,脖子上的硕大喉结提升了几次,也没有把淤结在嗓子里的字眼儿拉动起来。是呀,该怎么回答赵岩鞭梢一样严酷的质问呢?说如果仓库里没有这些货物甘愿以讹诈罪论处,要是真没有这些货物岂不是自我罗织罪名?虽然蒲昭合与严振东对侦察周大海的仓库花费了许多心血,甚至昨天还做了观察,再三保证不会有误,但毕竟不是还有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然而,倘若不敢凛然地回答赵岩要挟般的质问,不仅要落个无端滋事,而且也会极大地伤害蒲昭合与严振东的感情。于是,他冷冷一笑:“仓库里要是没有这些货物,你不是已经搬来了这么多武装保安警察吗?”
“好,杜老板,是条汉子!”赵岩以戏谑的目光蜇在杜仲坤的脸上,转身向老四一抬手,“把库房的钥匙交给警察!”尤瑟夫一伸手:“把钥匙给我!”
老四紧跑几步将钥匙放在尤瑟夫发面饼一样的手掌上。
“杜先生,请!”尤瑟夫向杜仲坤做了个友好的手势,但脸色如冰。
“您先请!”杜仲坤礼貌地一躬身。
此刻,要说心里最紧张的恐怕莫过于司马小媛了。虽然杜仲坤、蒲昭合和华娜娜等也心跳如鼓,但毕竟坚信感充溢于胸,并且还有一种敢于身入虎穴的豪迈,可是,司马小媛却觉得心里构筑的堤坝轰的一声坍塌了。只要周大海的仓库门一打开,杜仲坤原来从国内定购的旅游鞋和服装便昭然若揭!太可怕了呀!她虽说跟在华娜娜身后,距杜仲坤之间还隔着两三个人,却依然觉得杜仲坤会听到她“咚咚”的心跳声。她感到地在颤,又觉得脚下如履薄冰,身子在向寒冷贬骨的河水里沉没。每迈动一步,都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惶恐,那么的艰难。这不是在一步步走向毁灭,一步步走向自殄吗?
随着“嘎啦啦”一声响,灰色的木门敞开了胸膛。
明晃晃的阳光直泻在库房的水泥地上,亮得刺眼,又箭镞般射向四壁。
杜仲坤刹那间两条腿木桩子似的戳在原地不动了。
蒲昭合一双大眼瞪得失去了动感。
严振东惊诧得嘴变成了一个黑洞。
华娜娜忍不住叫出了声:“空的!怎么库房里什么货物都没有呀?!”
司马小媛身子一软,要不是急忙扶住门口的墙壁,会瘫坐在地上。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呀!仓库里没有货物,她最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了,这种一惊一喜的心理落差冲击得她浑身发软,似乎筋骨被泡酥了,被风化了,变成了齑粉,成不了团儿,没有了支撑力。
“杜先生,库房里哪是你们要查封的货物,认得出来吗?!”尤瑟夫悻悻地怒视着杜仲坤,那目光告诉他他已经犯了讹诈与扰乱社会治安的罪行。
杜仲坤虽然知道赵岩做了手脚,但抑制不住迁怒地向蒲昭合投过冷冷的一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姓赵的,你们昨天夜里一定把这里面的货物偷偷地运走了!你说,你他妈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蒲昭合与严振东一看库房里空荡荡地没有一件货物,一种被欺骗被作弄的愤懑使他们失去了理智,像两条疯牛一般扑向赵岩。
“抓起来!”尤瑟夫向几个武装保安警察发出了逮捕的指令。
尽管蒲昭合与严振东具有一身武功,但在荷枪实弹的武装保安警察面前还是被抓了起来,乖乖地被带上了手铐。
“慢!”杜仲坤急忙向尤瑟夫解释,“不要带他们两个走,要是我们这次行动有过失,该负责任的是我。要带,就带我走吧,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说完,双手向前一伸,一副自愿受罚的姿态。
赵岩觉得不能叫武装保安警察把杜仲坤带走,这样惊动面会太大。因为杜仲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分华商的旗帜,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也器重他。要把他抓到警察局,“华联会”和大使馆会立刻出面交涉和保释,自己也会因此在广大华商心目中成为周大海的帮凶,被暴露,被孤立。所以,他慌忙走到尤瑟夫面前耳语了几句。
尤瑟夫听了赵岩的话一点头,向武装保安警察一挥手:“把他们两个带走!”
顿时,蒲昭合与严振东被塞进一辆警车。
“杜先生,再见!”尤瑟夫向杜仲坤一握手,转身命令武装保安警察上了警车,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恍若做了场噩梦般的杜仲坤,有一种被奚落、被羞辱的感觉在胸中炽烤,他虽然极力抑制住冲动,话出口却依然显得很冷:“赵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说完向华娜娜和曹仁义及司马小媛一挥手,“走,回去!”
一脸得意的赵岩,看着昂首阔步走向奔驰轿车的杜仲坤,鼻孔里讥诮地喷出一股冷气:“哼!还是武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