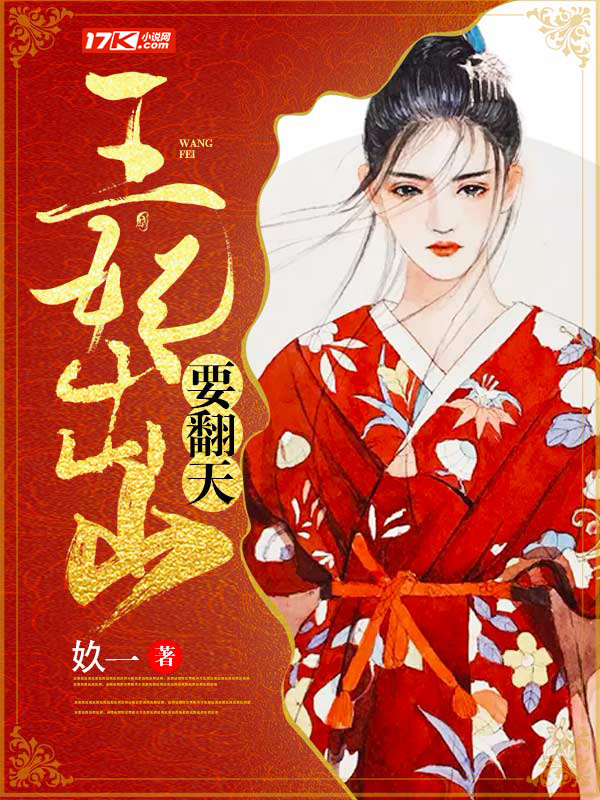妫翼跟随君绫北上至周地,这一路,妫翼时时刻刻都在提心吊胆。
月恒在君绫的怀中哭得撕心裂肺,可她越是哭闹,君绫越是不肯放手。
终于在抵达宛城时,月恒病了。
妫翼再忍不住,从她怀中夺下月恒,寻医官而去。
如今整个宛城冷冷清清,城中本就寥寥无几的医馆却都关着门。
走投无路时,她忽而想到,秦上元曾与她提到过的宛城驻军医局。
她凭着记忆向宛城驻军营飞奔,见驻军守营兵不过二三,且未成队。
未表明来意,妫翼直接闯入挂有“病”字旗的营帐之中,掀开大帐放眼望去,内中空旷且整洁,亦无伤兵,只有一群年岁不等的稚童与少年。
他们围坐在一处有模有样地分拣着草药,见妫翼闯入,皆向帐中磨药的妇人身前躲去。
妇人转过身时,紧追在妫翼身后的守营兵也冲了进来,作势便要打杀妫翼。
此时月恒颇为即时地嚎啕大哭起来,这哭声使守营兵停了手,连同妇人也穿过簇拥着她的稚童,向妫翼走了过来。
“她这是怎么了?”妇人开口问着。
妫翼眼眶发热,哽咽着声音道:“许是路途颠簸,加之受了惊吓所致。”
“这个时候,怎还带着个幼子到处赶路?”妇人紧皱着眉头嗔道。
她自妫翼怀中小心翼翼地接过月恒,一边埋怨着妫翼的粗心大意,一边细细地检查着月恒。
妫翼任凭妇人数落,也不开口反驳,站在旁边一位年岁稍大些的俊朗少年见妫翼眼中浸着少许泪水,故而上前扯了扯她的衣袖,细声道:“我阿娘最近太过劳累,脾气有些暴躁,虽然她是半路才学的医典,可多少有些用处,夫人莫急,我阿娘定能将妹妹医好。”
妫翼见少年眉眼有些相熟,可就是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她细声地与少年道了一声谢。
妇人检查完月恒后,又将她抱在怀中,轻轻地摇晃,嘴里哼着悦耳的童谣。
不刻,月恒止住了哭声,在妇人怀中渐渐睡去。
随后,妇人打发少年带着帐内的稚童去其他营帐内,并嘱咐他们,再不要靠近这所营帐。
“是风痧。”支开帐内所有的稚童,妇人开口道。
妫翼心中咯噔一下。
“不过算你走运,我刚刚炮制许多可用的药材,几服药下去,也就痊愈了。”妇人将月恒放在软塌上。
“只不过你的孩子尚幼,饮这种苦涩的汤药颇有难度,我建议你饮下汤药,再通过乳汁喂养。”妇人铺了几张油纸,开始为月恒配药。
妫翼垂眸望着月恒,随后笔直地跪在妇人身前。
妇人吓了一跳,连忙去扶。
“我与女娘有因缘羁绊,还请女娘代我照看她。”这妇人的相貌与莘娇阳有七分相像,又能在宛城军营随意去留,想必是嫁给宋家的莘氏女,同莘娇阳是亲姐妹。
如今妫翼被君绫痴缠,若君绫再拖着月恒,怕是到了安阳,月恒也没命了。
迫不得已,妫翼才想将月恒托付给她。
“我如何代你照看这乳娃娃,她这般幼小,你忍心扔下她就走?”妇人挑着眉梢,不可置信地看着妫翼。
“我有不得不走的理由。”妫翼哽咽道。
妫翼望着月恒的眼神带着心碎与不舍,妇人从她的眼眸中读懂,又想到她说的那句因缘羁绊,终是叹了口气,道:“何时回来?”
妫翼微怔,她总是没想到妇人能这么快就妥协。
她跪拜后起身,从怀中摸出一条冰玉的火纹长生锁,这是月恒满月时,妘缨送给她的礼物,此前被君绫嫌弃碍眼,扯下仍在路旁。
妫翼将长生锁重新挂在月恒身上:“若我一直未能回来,还劳烦女娘,将她送去宋国,出示这冰玉的长生锁,便会有人收留她。”
妇人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不知你要去做什么,想来也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抛下这乳娃娃,只是我相信若非到性命攸关,一个母亲总不会抛下自己的孩子。”
“周地动荡,阿妹小心些,我和孩子一起等着你回来。”
莘氏女总能察觉到人的内心身处,良善又不失锋利,体贴又恰到好处。
妫翼点了点头,心中盛满感激地再次拜别妇人。
此时,帐外传来稚童们阵阵惊呼,妫翼与妇人相视一眼,先后冲出了营帐。
帐外,君绫正提着一惊慌失措的稚童,神色玩味地逗弄着。
她身上的华服血迹斑斑,腰腹之间有一处浓厚的血印,似是那处受了重伤。
余下稚童皆战战兢兢地躲在年岁稍大的俊朗少年身后,而大营中的守卫皆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口鼻渗血,气息奄奄。
君绫看见妫翼现身,缓缓将手松了开。
眼看稚童欲坠向地面,那位俊朗少年猛冲向前,稳稳地接住了稚童。
站在妫翼身后的妇人松了一口气,她气势汹汹地向前一步,质问君绫何故与孩子过不去。
妫翼默默捏了一把冷汗,上前握住了妇人的手臂,示意她不要再开口。
君绫见妫翼与妇人相熟,冷冷地开口道:“你将阿九托付给她了,是不是?”
妫翼定了定心神,行过妇人的身旁,道:“你我二人此去安阳,不便带着她,不如暂且先将她留在这儿,这营中稚童皆受这位女娘照拂,荒时暴月能有如此良善行德之人,你也不必担心她会亏待了阿九。”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一路,我亏待了阿九?”君绫横眉立目,眸中火色妖瞳忽隐忽现。
妇人听得出来,孩子的母亲正是受面前这位不速之客的胁迫,才不得不托付骨肉予她。
“她得了风痧。”妇人道。
“阿九得了风痧,若不留在这里接受治疗,再继续前行,路途颠簸会有性命之危。”妇人故意将月恒的病说得严重。
君绫眼神犀利地望着妇人,妇人并未躲闪,行之坦荡地与她对视。
少时,君绫冷笑一声:“原是宋将军的良妻。”
妇人一怔,眼神忽而变得凶猛。
“你将我家将军如何了?”妇人紧握着双拳怒吼道。
妫翼颇为不解,妇人是如何仅凭一句话,便知晓君绫见过宋尔延将军的?
君绫摇了摇头,不屑一顾地道:“我也不清楚,许是死了吧?”
妇人闻此,近乎崩溃,她身形恍惚,若不是妫翼扶了她一把,怕是她已经栽倒在地。
君绫阴霾的眼中,闪过一丝透亮,她随后又道:“进了死城,也不一定会死,也可能还活着,被秦上元用汤药吊着命。”
妇人忽而扑向君绫,跪倒在她脚边,一边啜泣,一边求道:“我求求你,救救他,别让他死,至少别让我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妫翼不动声色,细细地观察着君绫,她眼眸中的火色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寂的墨色。
“他知道前去安阳支援必是凶险万分,所以随身带着你的小像,因为你的小像,我已经饶了他一次,可他却不知感恩,反而刺穿了我的心窝。”君绫平静地说道。
妫翼也是最近才察觉,疫病发散可能源自于君绫的血。
越是疯狂砍杀她的人,越容易被侵染疫病,甚至触碰到她的血迹,便会即刻死亡。
只是妫翼尚且不清楚,那些没有被染上疫病的人,是如何规避的。
便是方才君绫提着那个稚童的脸上,也被溅到君绫的血迹,可为何那稚童却毫发无损?
“愣着做什么,不走吗?”君绫喝道。
妫翼回神,将妇人扶了起来,并安慰她,待到了安阳,定会确认宋尔延将军的情况,而后书信与她知晓。
妇人不言不语,只是不住地在抽泣。
妫翼见无法慰藉妇人的悲痛,便叫来那少年搀扶妇人,随后与君绫缓缓离开。
还未行满十步,身后便传来动静。
妫翼回眸望去,见那妇人手持长簪,向君绫背后刺去。
妫翼甚怕妇人被君绫的血迹飞溅,而染疫身亡,故而挡在了君绫身前,为她承受了那一簪的袭击。
妇人未修武道,身姿轻盈柔弱,那一簪子虽然见血,可终究未伤及太深。
妫翼趁机伏在妇人肩膀,轻声道了一句:“护好自己,才能守护孩子们。”
妇人闻讯,身形一晃,眼中积泪登时崩落于面颊,而后长叹一声瘫坐在地上。
妫翼将簪子拔出,还给妇人,随后自中衣内侧撕下一段薄布,按压在伤口处止血。
她转过身,却发现君绫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她后背冒出虚汗,有些后怕君绫看穿她为了保护妇人,所用的苦肉伎俩。
“为何替我挡下,你明知我就算被剁成肉泥,也不会死去。”这一路上,要杀君绫的人太多,多到每经过一处,君绫都会换掉沾满血污的衣衫。
妫翼不知她伤口如何愈合,只是但凡她受伤之地,方圆十余里的人,皆被不约而同地染上疫病。
“你是不会死,可你也会疼。”妫翼道。
“你骗我。”君绫眼中闪着许久不见的泪光。
“你定是怕我受伤后,发怒而伤害她,所以才会为我挡了这一下。”君绫道。
妫翼抿着嘴,越过她,继续向前走,道:“若你这么想,便如此吧。”
二人一前一后出了宛城大营,继续在春日的萧瑟中前行。
由于日夜不停地赶路,妫翼身上的那处伤口反复撕裂,创面难以愈合。
创痕引起了她的惊厥,猛然摔进了春夜的野花丛里。
陷入惊厥的恍惚之间,妫翼似是看到满天的萤火,聚集着向她飞了过来。
她心口滚烫,火炼般的刺痛钻心刻骨,随后便来阵阵暖意,由心口蔓延全身,直至四肢。
妫翼神智逐渐恢复,且再感受不到伤口的疼痛,眼前的萤火越来越旺盛,似是破天的火焰一样。
她动了动,想坐起身,却惊觉自己身体似是被什么东西禁锢在花丛中,动弹不得。
须臾,破天的火焰汇聚成了人形,落在妫翼的身前。
万千条裂痕般地脉络在人形之中突显出来,妫翼睁大双眼,仔细地观察着。
每一条裂痕,皆是一道伤疤。
刀伤,箭伤,刺伤,砍伤,剜伤。
在这些无数的伤痕之中,君绫的肉身显现出来。
犹如出浴的美人,初生的婴孩。
她在千疮百孔中死去,又在千疮百孔中重生。
炽热般的气息吹散开来,野花飞起再落下,如君绫一般,完成了一次新生。
她伏在妫翼的胸口,浓密的青丝包裹着娇嫩的身躯,墨色中的雪白,格外耀眼。
“替我受的这一下,我还你了。”君绫道。
妫翼这才知,原来君绫受的那些伤,都是经历浴火来完成愈合的。
仅仅她心口的那一处伤痕,方才就疼的死去活来,君绫那一身的伤痕,火炼般地刺穿全身,该多疼啊。
妫翼抬起手,环住君绫的腰身,将她牢牢抱在怀中。
“往后不要再受伤了。”妫翼轻声在她耳旁道。
“我会保护你,也请你爱惜你自己。”
君绫缓缓地向妫翼靠了靠:“好。”
“我就当你,真的是为我着想。”
她如此眷恋人间,可人间,却没有谁再眷恋她了。
妫翼竟成了她在人间唯一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