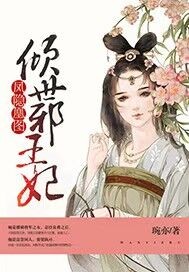不刻,白素面上忽然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随着他的闷声一哼,雅光侧身从马上落下。
木丝言见状飞身去接,二人一同落在两军对峙的中央空地上。
白素胸前铁甲的缝隙中有丝丝血迹流出,而他的胸膛上赫然地插着一支青玉簪。
“白武安,我不是你的东西,你听好,不惯昭儿答允了你什么,若是我不愿意,我就是死也不会死在你的怀里。”雅光俯身拾起方才落在地上的熊首弓道。
白素淡然一笑,而后将胸前的青玉簪拔出,摩挲了片刻后,放在怀中道:“雅光,你欠我三箭,加上这一道青玉簪,我记着,我都记着,你若不还,我就追到你下一世,你下一世若不还,我就追到你永生永世。”
雅光被白素气的浑身发抖,她才要拉满弓朝他射箭而去,可不知怎地,却又放了下来。
“白武安,你配吗?”
雅光轻蔑一笑。
白素并没有生气,彷如年少时二人吵嘴时地模样,他歪着头一脸欢愉地道;“当然,吾乃楚国将军,九州战神白素,与你自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此时,蔡侯的脸已呈现龟甲之色,他怕白素再说下去,就坐实了雅光同他有旧情的传言,况且在场的士兵如数百人,一人一口相传下去,他蔡侯的颜面可往哪里放?
他立即低声命令叔姜,趁所有人不备,前去夺回雅光。
叔姜才抬起脚,便被木丝言发觉,她侧身挡在雅光的身前,不让他有可乘之机。
蔡侯见状,便发动手持弓箭的侍卫,羽箭如落于一般地朝木丝言和雅光飞来。
木丝言立即以真气做盾,将雅光护住。
而雅光,也不甘只做为一个被保护者。她勇敢地上前,俯身拾起落在地上的羽箭,接二连三地朝着对面飞射去。
二人并肩作战,将包围着她们的队伍,打出了一个缺口。
“阿言,我们共乘一骑冲出去。”雅光射出手中最后一支羽箭道。
木丝言点了点头,护着雅光向后退去。
须臾,木丝言的双膝忽觉刺痛,待双腿不受控制地跪下时,迎面而来的一支羽箭就要射穿她的胸膛。
电石火光之间,雅光挡在了她面前。
“阿言,快逃。”
这是雅光扑倒在木丝言怀中说的最后一句话。
木丝言抱着雅光,拼了命地想要站立。
她想要带她离开,离开这些恨不得要分食她的人。
可她的双腿,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使不出半丝力气。
“入了绣衣阁,你还真以为你能活着逃走?”白素御马上前,他侧身下马,缓缓朝着木丝言走来。
木丝言将昏厥过去的雅光护在身后,拔出匕首指向白素。
在白素的身后,木丝言瞧见一个让她再熟悉不过的俏丽身影。
那人的脸上依旧被丑陋的面具所遮盖,修长而又丰盈的身姿在那些铁甲军之中显得格外孤立。
想必是那人发出的暗针,刺入了她腿上的某个大穴,才会导致她无法站立。
就像在绣衣阁刺入木丝言背后风门穴的那次一样。
“你的武功虽是所向披靡,可最终却是出于绣衣阁,我既然能让你天下无敌,自然也有办法让你一无是处。”白素俯身便要去拽雅光,却被木丝言的匕首割破了手臂。
“我就是跪着,也能杀你。”她不顾一切地逆行经脉,迫使双腿受力朝白素飞身而去,抬手便是一掌。
白素并未预料到木丝言会用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他来不及躲避,便只能硬生生地接下木丝言这一掌。
白素只觉胸口仿若被巨石砸穿了一般,他耐不住力道,后退了几步,身形一顿,猛地喷出一大口血来。
木丝言逆行了经脉,自然也不会好受。
她瘫倒在地上,随即也吐出一大口血来。
“你还在等什么,等她杀了我吗?”白素盘坐归息之余,朝不远处的那人喊道。
那人侧身下马,缓缓地朝木丝言走去了。
耳边传来了沙沙脚步声,木丝言抬头望去,见那人手持银针立于面前。
依旧是不动声色地将三支银针刺入木丝言的风门穴之中。
背后的刺痛席卷了木丝言的整个身体,她抽搐着昂起头,可双眼始终不屈。
“别,别让白素带走她。”木丝言死死地拉着那人的衣角隐忍地说道。
丑陋的面具后,本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却因木丝言的这一句话,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
那人俯身将昏死过去的木丝言抗在肩上,准备上马而去。
“我还未下令撤退,你胆敢私逃。”白素归息结束后,仍觉双腿发软。
毕竟方才那一掌,是木丝言拼尽了全力。
“我乃奉的是楚王之令,带木丝言回东楚复命,奉劝将军一句,收敛些,毕竟楚王答应了蔡侯,雅光公主是要同他归尔雅的,莫要为了一己之私,违抗王命才好。”她忽地开口道。
白素被气得面色发青,依旧踉跄地朝雅光走去。
料想蔡侯见到白素被打伤的几率,就犹如白日里见到星星一般。他自然不能放弃这个羞辱白素的机会,他欣喜若狂地命叔姜上前,将雅光带回。自己却抽出长刀对峙白素。
凭白素现在重伤的状态,随意一个小兵都可以将之重锤,更何况是有些身手的蔡侯。
两个男人同为了尊严展开了殊死搏斗,可最后谁都不是胜者,两败俱伤。
木丝言被带回了东楚,在楚王下令废了她身上的武功之后,被宫内的女官们收拾了一番,干干净净地送去了白家,成为了白尧的宠姬之一。
这是楚王答应白尧的,也是木丝言命里逃不过去的劫数。
她被软禁在一处白府的一处院子里,院子的名字叫莫梨轩,是仿照木丝言在木家所住的闺阁所建,院内还有三棵自木家移栽过来的棠梨树。
木丝言之所以认得那三棵棠梨树,只因那树是她和小姑姑亲手栽下的,树干上还刻着小姑姑的闺中小字,卿卿。
木丝言也曾想尽一切办法出逃,可白尧故意将莫梨轩建在白家花园最深处,四处皆是阵法,使木丝言困在其中,让她寸步难行。
她功力尽失,被废之时,伤了身上的筋脉,至今还浑身作痛。
她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砧板鱼,若不愿坐以待毙,只能拼了命地折腾。
她砸了莫梨轩内所有值钱的东西,玉器,陶瓷,青玉案,就连她夜夜所栖的,万金难求的息石床,也被她砸成了两半。
可白尧来莫梨轩见她时,却并未有责怪她,反而悠闲地捧着棋盘席地而坐,邀请她同自己对弈。
木丝言一气之下,接连赢了白尧三局。
可白尧依旧未生气,还拿出了一坛棠梨酒出来与木丝言对饮。
想来,白尧的棠梨酒同那三棵棠梨树一样,都是从木家夺来的。
木丝言喝了几爵,便精神恍惚了起来。
仿佛她又回到了木家,坐在棠梨树下,同阿翁和小姑姑对饮,谈天,华容郡主手持柳条出现,怒斥着木丝言年幼狂妄,胆敢背着她饮酒。
只不过,华容郡主的柳条,再也不能抽到她的身上罢了。
木丝言迷迷糊糊地哭着笑,笑着哭,醒来时,完好无损地睡在了白尧的卧房之中。
白尧也算是个君子,并未有在木丝言喝醉时趁机下手将她吞入腹中。
可木丝言知道,既被送来了白家,白尧对她下手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所以在被生吞活剥之前,她尽可能让白尧厌烦了她,她才有机会能逃。
于某日深夜,木丝言一把火将莫梨轩烧了干净。
火光冲天之时,她缓缓地坐在棠梨树下,望着夜空。
众人闻讯赶来,纷纷洒水救火。
少时,白尧衣衫不整地从主院跑来。他原本面目惊慌,在见到木丝言毫发无损时,先是松了一口气,而后猛地想到了什么,抬起手便掌掴了木丝言。
木丝言身子虚弱,被白尧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头昏眼花,跌倒在地上,竟无力站起。
“你就这般想死是吗?”白尧一把拉起木丝言,扯着她后脑的长发,目眦尽裂地怒道。
木丝言双手死死抠在地上,指甲深埋入土,双目通红地道:“我这样活着,同死并无区别。”
白尧神情一顿,随后松开了木丝言。
他直起身子,眼中隐藏了愤怒,转而一片漆黑。
“夫君,莫生气,想来阿言妹妹也是一时冲动,这夜里凉,她前些日子伤筋动骨,别又冻坏了身子。”前来劝说白尧的,正是他的正妻姚绾。
看来木丝言烧的这场大火,耽误了两人之间的夫妻秘事。
木丝言心里,不知为何,产生一种可耻的窃喜。
姚绾将身上的披风解了下来,裹在了木丝言的身上,并将她扶了起来。
如若不是少时的姚绾对木丝言不错,导致木丝言放下了戒心,她不会想到,今夜姚绾帮她,不过是在白尧面前作态,并且暗自酝酿着借刀杀人的计谋。
木丝言被姚绾带去了她住的浅绛院。
在浅绛院小住了些许时日的木丝言被姚绾照顾有加,闲来无事之时,尝试盘坐院内的河塘旁边归息。
归息时,她猛然发觉自己的体内尚有一丝真气游荡在丹田之内,只是被一股更霸道的真气禁锢了而已。
她尝试一连几次突破,累的浑身香汗淋漓,却也无济于事。
少时,她听到了脚步声,连忙停止调息,站起了身。
来者是白尧,他见木丝言浑身湿透了,神色略带惊异。他抬起手,想是触碰木丝言潮湿的额头,探看她是否生病。
可这手还未落下,却被木丝言一个侧身躲了开。
“方才,我是瞧河塘里的鱼儿肥,便想着抓一条烤来吃。”木丝言胡诌了一个理由,搪塞白尧。
白尧淡淡地笑了笑,随即拉过木丝言,伸手扯着她腰间的衣带。
木丝言花容失色,两只玉臂慌乱地捶打着白尧的前胸。
白尧猛地将她拉入怀中,在她耳边吹气道:“你不是一直想要逃吗,你与我生个孩子,我便放你走。”
木丝言身体僵硬,被白尧抱回到屋内,放在床榻上时,浑身上下战栗不止。
须臾,她觉得浑身一凉,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被褪去了。
内力尽失的木丝言,面对白尧,就像是已经烤好野味,根本没机会反抗,只要撕扯便能尝到。
不反抗,或许还能剩下一副骨架,反抗,可能连渣子都没了。
白尧观赏了木丝言的身子一阵,呼吸由轻变重,又由重变轻。
随后,他取下一块干净的布,将她身上的汗珠拭干,又转身寻了一身干爽的衣服,替她穿上了。
木丝言半悬着的心落地了,她坐起身,规整衣裳后侧目白尧。
敢情方才,白尧是在试探她?